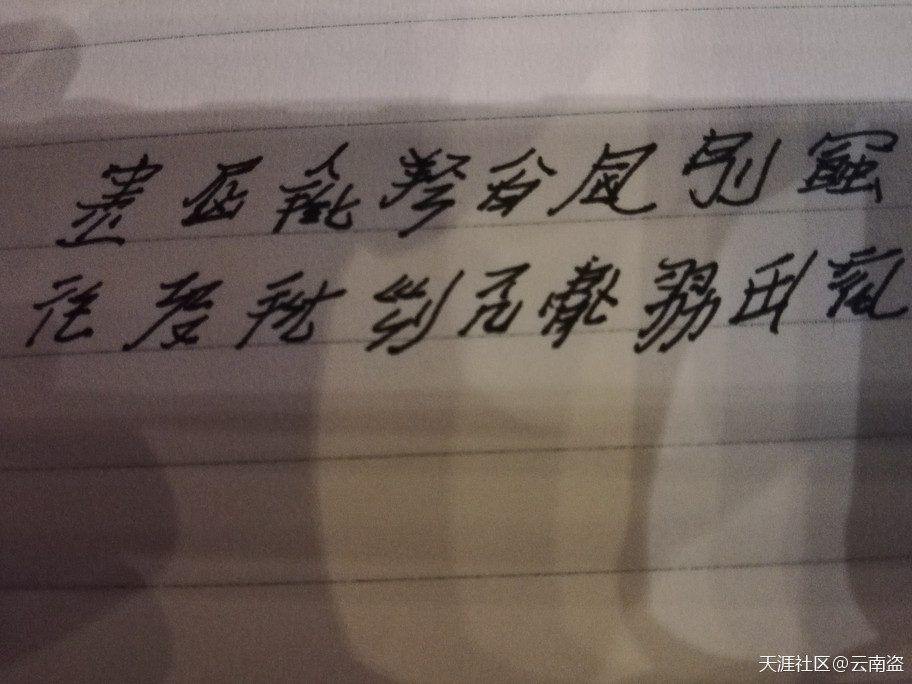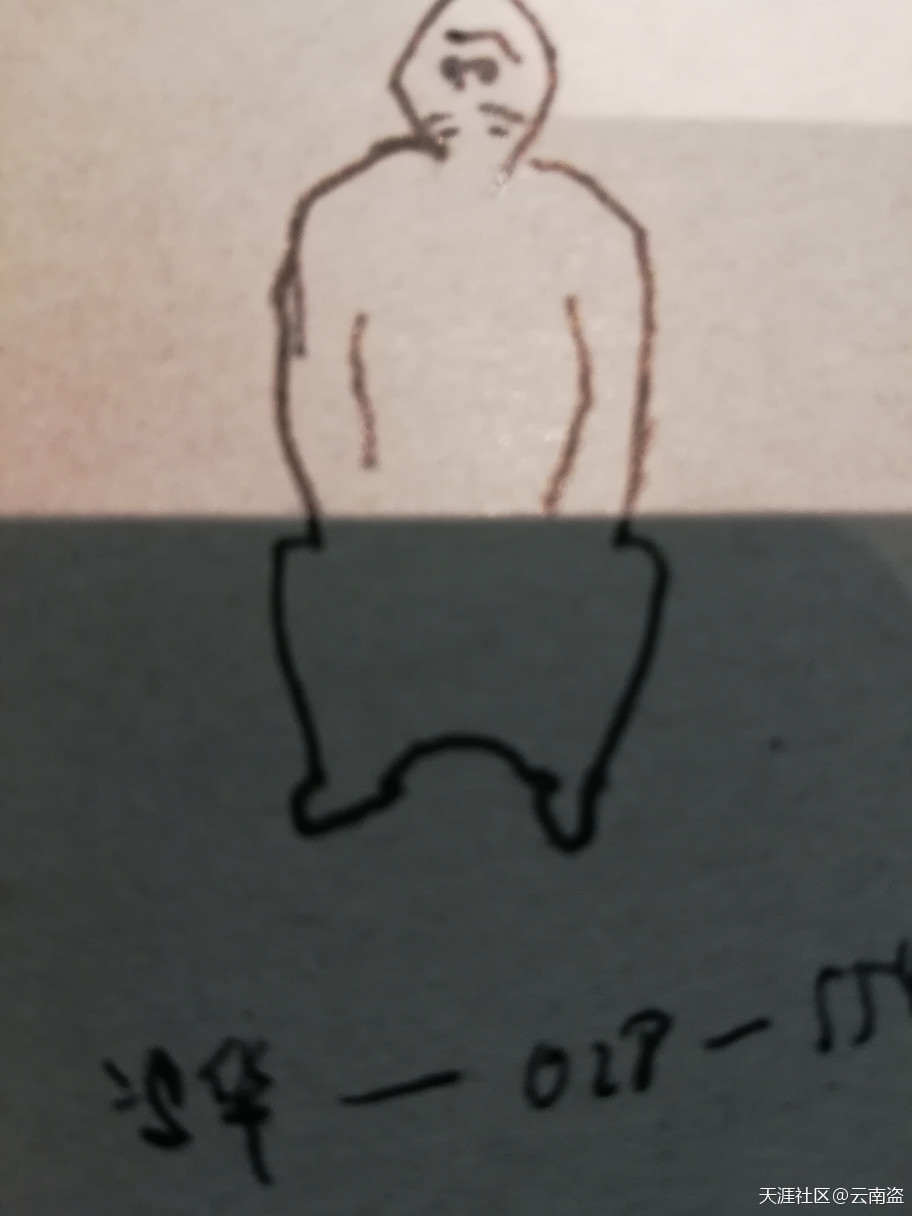“有文化个屁!”我抵了回去,心说我就是一个做活路的粗人,就因为打架才进监狱,不知道这小子从哪里看出我有文化的。
周结巴扶了扶眼镜,嘿嘿笑道:“现在没有以后有,来,给你看样东西。”
说完他伸手入包,一阵鼓捣,“叮咚”几声,掏出一个皱巴巴的黑色塑料口袋。
我这时心里升腾起一个疑问,不由问道:“等一下!我总觉得这人有问题!”
周结巴一愣:“怎么?”
我拿起那根短铲,来回看了看,铲子锈迹斑斑,前端出现很多冰口,明显铲过石头之类的硬物,我丢在一边,拿起电筒,是一把很普通的铁皮电筒,也锈得厉害,一摁开关,眼前一亮,竟然还有电。
我丢一边,又拿起那把砍刀,发现刀刃大了很多卷儿,前端有一层黑色的油状物,我凑近闻了闻,顿时闻到那种墨鱼的腥臭。
“太怪了。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包里装这些工具?”
“多半是个收货的。”
我一愣:“怎么说?”
周结巴回答:“我以前在小板桥认识好几个,古董旧货死人东西全部都在做,他们都随时背一个包包,吃饭喝茶拉屎拉尿都不离身,里面就是这些铲子啊电筒放大镜之类的东西,我看那个人多半也是做这行的。”
我指了指石俑:“这样子说,这东西说不定也是他从什么地方收来的。”
“嗯。”周结巴点头:“很有可能。”
我哼一声:“你也可以,人死在昆明,东西在攀枝花被你拿去卖钱!”
“嘿嘿嘿!”周结巴干笑两声:“说明他没这个缘分。”
我摇摇头,心中五味杂陈。
“算了算了。”周结巴这时开始打开那个塑料袋子:“现在说这些都是废话,来来来,你过来看一下,看认不认识这些字。”
里面是一卷黑色的纸,质地感觉比较柔软,周结巴小心展开,出乎我意料,竟然有两张报纸横着连起来这么大,一米来宽,上下30公分,在展开的同时,那种墨鱼腥臭味一下冒出来,明显来自于纸张本身。
我忽忽嗅了两下:“闻到没有?又是这种味道!”
“嗯。”周结巴点头:“是太臭了!我之前还以为这个皮包装过烂墨鱼,但现在看来不像,里面所有东西都有这股臭味,所以我感觉它之前是不是掉到了海里面。”
我一愣:“海?”
“是啊!肯定掉进去被浸泡了一段时间,搞得所有东西都有这种气味!”
我点点头,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怪光:“喂!你说——”
“什么?”周结巴抬起头。
“你说,这东西会不会从海里面捞起来的?”
周结巴一愣,指了指石俑:“你说这东西?”
我点头:“是啊!不然怎么全是海腥味!”
“这个我倒没想过!”周结巴一脸茫然:“海?X你大爷的怎么会从海里面?”
我也想不通,懒得想了,指了指那块黑色的纸:“你给我看什么?”
“哦!”周结巴回过神,小心一翻,翻到另外一面,只见黑纸中间赫然出现一排白色的东西,歪歪扭扭,像是一排文字。
我凑过去一看,果然是文字,而且第一感像繁体字,但仔细一看,那些文字虽说有“横竖撇捺折”,也有一些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但组合得极其怪异,明显不是汉字!
周结巴问:“什么字见过没有?”
我摇摇头:“没见过。怪眉怪眼的像是繁体字但是——”
“屁个繁体字!”周结巴很肯定:“繁体字我还不知道?我也收过几年古籍,肯定不是!”
“那你问我老屁!”我也懒得想。
“算了,这东西以后再说。”周结巴卷起黑纸,塞进塑料袋,又把报纸重新把石俑包住,小心翼翼放进皮包。
我站起来,看了看手表,已经半夜1点10分了。
周结巴把皮包拉链拉好,放进编织袋,也站起来。
“妈X的又是半夜了!”他看了窗外一眼,回头坏笑道:“走,下去再找那两个小妹放一炮,刚才没按摩爽!”
我打个哈欠:“你想去就去,我要睡觉。”
周结巴嘿嘿一笑:“也行。那你干脆就在这儿睡,我下去搞点节目,明天看那个老板来不来。”
第二天睡到10点半才起床,周结巴正抠着眼屎上来,说昨晚上“包了个夜”,累。
二人下楼在一家米粉店随便吃了点东西,周结巴说今天我们两个就不要到处跑,最好不要出这个家属区,出去万一被雷兵发现就不好办,到时候他找不到我们两个自然就会回昆明。
我问他身上没有手机那个黄老板如何联系你,他说他留了招待所的座机号,到时候人到了攀枝花就会联系。
于是就在家属区里面一家电子游戏厅玩,旁边还有一家台球室,一个录像厅,一直混到傍晚,我坐了几年牢,好久没玩了,也懒得多想,敞开了玩游戏。
晚上随便吃了点东西,又去看录像,是个通宵录像,20块钱一张票,一共放5部,各种类型都有,周结巴请客买了两张票,进去看到凌晨2点过,他打着哈欠说不好看,上楼睡觉去了。
当天无话。
第二天上午在房间睡觉,下午起床又下去打游戏,晚上吃米粉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电话来,周结巴摇摇头,有些失落的样子。
晚上我又去看录像,周结巴说去那家按摩店消费,说完溜了。
看到12点时候,刚看完第二部,周结巴摸黑跑进来,找到我,一脸兴奋说,走,人到了!
我也一下很兴奋,赶紧跟他上楼,把那尊石俑放进那个绿口袋,出门。
已经深夜,在路边喊了一辆出租车,周结巴说:“去木棉路。”
到了木棉路,找了一下,路边有一家高档茶楼,叫“金雁茶府”,周结巴说那个人就在楼上,一个小时前到的,看来也很急,连夜叫我们见面。
上到三楼,进入大厅,里面烟雾弥漫,已经12点过了竟然还有七八桌喝茶的,看衣着穿戴都像是有钱人。
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周结巴说,找个人,成都来的,姓黄,于是服务员带我们拐了个弯,走到一个包厢门口,打开门,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里面有两个男的,看见我们,其中一个站起来。
站起来那人60多岁,像个乡镇老师,坐着那人40来岁,衣着考究,戴一副茶色眼镜,神情沉稳。
“黄老板。”周结巴朝坐着那人点头哈腰。
“周学良,你好。”坐着那人点点头,声音沉稳不带任何情绪:“更正一下,我不姓黄,我姓邓。”
周结巴一愣:“哦邓老板。”接着朝“乡镇老师”一指:“那这位才是?”
“他也不是,他是老彭,你说的黄老板是我一个好朋友,是我委托他找那个东西的。”邓老板瞟我一眼:“这位是——”
“我兄弟,小关。”
邓老板点点头:“好,我也不废话了,东西带来没有?”
周结巴犹豫了一下,提起绿口袋,放茶座上,打开,露出包着的石俑,我注意到那二人同时深呼吸了一下,明显很紧张。
这时周结巴已经扯开报纸,整个石俑露出来,那张怪异的“倒脸”正正对着邓老板。
只见那二人四只眼睛全部死死钉在石俑脸上,邓老板因为带着茶色眼镜,看不见眼神,但老彭明显眼睛里露出一种恐惧神色,似乎很害怕眼前这东西。
我暗暗点头:他们居然这种眼神,看来这具石俑一定跟他二人有重大过节!
这时老彭伸出右手在石俑上摸了一把,缩回来,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又伸手敲了两下,石俑内部发出一种很木的声音。
“如何?”邓老板问。
老彭不回答,从内衣口袋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笔记本,翻开到某页,看了一眼,又抬头看了一眼石俑,又低头看本子,才点点头。
“如何?”邓老板又问。
老彭还是不答,伸出双手,抱住石俑,试了试,缓缓横放在茶桌上,然后做了一个古怪动作:低下头,把脸侧向石俑的脚部,两只眼睛上翻去看石俑的脸。
我暗暗点头:他在看石俑怪脸的正面!
看了几秒,老彭抬起头,把石俑翻上来放平。
“一模一样。”他道:“就这东西。”
邓老板呼口气,点点头,问周结巴:“东西哪儿搞来的?”
周结巴眨眨眼睛:“朋友的。”
邓老板一皱眉:“朋友?什么朋友?”
周结巴嘿嘿一笑:“这个,嘿嘿,他交代了要保密。”
邓老板点点头:“这么说,是他委托你来交易的?”
“对对对。”周结巴忙点头。
“从什么地方搞来的你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
“这个。嘿嘿嘿。”周结巴抠抠后脑勺:“我不能说。”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
“这个。嘿嘿,不能说。”
“那你朋友是哪儿的人,昆明还是攀枝花?”
“嘿嘿。不能说。”
“懂了。”邓老板点点头:“这样,东西我们要了,之前黄老板说的五千,我给你六千。”
“六千?”周结巴张大嘴巴,一脸喜色跟我对视一眼。
“对。钱我可以马上给你,但我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私人要求。”
“你说你说。”周结巴一脸喜色。
“这种石俑——”邓老板顿了一下:“你朋友那里还有没有?”
周结巴眨眨眼,道:“暂时——只有这么一个。”
“是么?”邓老板茶色眼镜后面露出冷森森的光:“你叫周学良是吧。”
周结巴一愣:“是啊?”
“好,周学良。”邓老板凑过来:“你记住我下面说的话,现在我不管你这东西是怎么搞到手的,是你朋友的还是怎么倒手来的,现在我都不管,我只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做成后我必重谢。”
周结巴看我一眼,怯生生道:“什么事?”
“我要你给我查出这东西的原始来历。”
“原始来历?”
“对!就是它最开始的发现地。”
“最开始的发现地?”周结巴喃喃重复。
“对。”
“就是最开始从哪儿发现的?”
“是。”
周结巴笑了一下:“那我也有一个问题,邓老板你为啥要查它发现地?”
“这个问题不该你问。”邓老板顿了顿:“如何,你接不接这个单?”
“嘿嘿。”周结巴看我一眼,讪笑道:“这个——钱怎么算?嘿嘿嘿。”
“这样,两万块钱,时限一个月,我先打五千块钱过来算前期车旅食宿费用,你看如何?”
“两万?嘿嘿。”周结巴瞟我一眼,蒙住嘴巴,露出笑意。
我脑子里已经一团浆糊:现在看来,这尊石俑不但收不回来,关键是这死结巴看来已经想跟这位邓老板合作去办事了,那昆明那头咋办?
我赶紧捅了周结巴后背一下,低声道:“要不出去商量一下?”
“商量个屁!”周结巴低声回骂一句,满脸笑容对邓老板道:“那行!我干!那要不要签个合同之类?”
“那倒不用。周福才好像是你亲戚吧?”
“对对。”周结巴忙点头:“他是我七哥子。”
“那就好。大家都是朋友,都在江湖上混饭吃,我相信你不会拿了这五千块钱就跑路吧。”
“不会。不会。”周结巴陪着笑脸。
邓老板没理他,朝老彭使了个眼色,老彭回身从一个旅行包里摸出厚厚一摞钱,点了点,递给邓老板,邓老板随手放桌上。
“这儿一万一,你点点。”
周结巴一把抓过,讪笑道:“不用不用不用。”
我心头一急,捅他一下:“喂!”
周结巴没反应,不停感谢:“谢了谢了。”
“那就这样。”邓老板站起来:“我们还有事要回成都,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利,我在成都等你们的好消息。”
旁边,老彭已经把那层报纸扯下来,丢在桌上,把石俑小心翼翼放进随身旅行包里,也站起来。
周结巴点头哈腰送那二人出去,我坐在沙发上,盯着那张烂报纸,一团乱麻,但这时我发现一点东西,于是拿起报纸,眉头上有四个大红字——《邢台日报》。
我正要看仔细,周结巴走回来,拍一下手,得意洋洋道:“搞定!”
我没好气:“你真要去?”
“定金都收了不去?”周结巴坐下来,抓住那摞钱,一边蘸口水一边数。
我盯着他数钱,心头也不由打鼓:这辈子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多钱,以前在宋建国的施工队每个月最多分八九百块钱,这邓老板也太大方了,一出手就是一万多,这都相当于我干整整一年了。
周结巴数完钱,塞进绿口袋,嘿嘿一乐:“看见没有?发财了!”
我恨着他:“你真要去查?”
“不是你,是你们。”周结巴用手背拍了拍口袋:“放心,我不会耍赖,这儿一半是你的,回去就给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我咬咬牙,这里头一万一,一半就是五千五,宋建国那儿准备给我600一月,相当于干9个月。
“昆明那边咋办?”我问。
“我是这样子想的。”周结巴扶住我肩膀,朝周围鬼祟瞟了几眼,压低声音:“那个人你说他是挖了自己眼珠然后死了是不是?”
“是啊?”
“你想过没有,他为啥要挖掉自己眼珠?”
我一凛:“宋建国说是他有精神病,你堂哥说是他中了什么邪。”
“哼哼。我觉得都不对。”
我一愣:“怎么说?”
“我觉得他是被谋杀。”
“谋杀?”
“对!凶手当时就在车上。”
我一惊:“你说什么?”
“嘘——小声点!”周结巴朝周围打望一眼:“我昨晚上又想了一下,总觉得有件事很奇怪,你看那个人,穿西服,还戴金丝眼镜,一看就是个有学问有身份的人,可是他的包里面放的东西却跟他身份严重不符,又是砍刀又是铲子,所以我就突然在想——”
“想啥?”
“我怀疑那个黑包,还有里面的东西包括那个石俑,也不是他的!”
我一愣:“不是他的?那谁的?”
周结巴摇摇头:“这个不好说。但我有个感觉,他被挖眼然后死,跟定跟那个包有关系,说不定也是巧取豪夺,最后被凶手杀了,而那个杀他的人不用说,当时也在车上,说不定就睡在你我旁边!”
我盯着周结巴,身上莫名起了一层鸡皮。
“所以这件命案跟我没关,跟你关哥也没关。”
我点点头:“你也许说得对。但现在关键,警察怀疑的是你。”
“妈X的就这点最麻烦!”周结巴啐了一口:“所以你我两个要抓紧,现在说都说好了,说好的事必须做,还有——”
周结巴凑过来:“我现在对那个石头怪人越来越有兴趣,原来我还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古董,那个黄老板也是普通的收购普通的收藏,但现在我感觉不对头,那东西绝对不简单,你看刚才那姓邓的还有那个老彭他们的表情,那个石俑背后绝对还有名堂!”
我点点头:“嗯。我也差不多看出来了,那姓邓的两个不是一般人,背后的水不是一般的深。”
“那走!”周结巴端起也不知道是谁的茶杯,猛灌几口:“回去研究一下,该从哪儿入手!”
回到招待所已经快凌晨2点了。
我跟周结巴开始密谋,先分析了一下邓老板要这种石俑的原因,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也许还不是石俑,而是石俑的“原始来历”,就是石俑的发现地!
这就非常奇怪,因为一般来说这些古玩商都是对古物有兴趣,而这个神秘的邓老板竟然对古物的“发现地”或者说“出土地”有兴趣,这里头就不简单。
周结巴最后判断,极有可能那个“出土地”里面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才是邓老板的终极目标!
我就问,那你估计那“另外一物”是什么?
周结巴摇头说不知道,这二人背后水够深的,竟然对我们完全隐瞒了这点,看来以后打交道还得防着他们。
接下来,我们开始商量正事,那就是下一步如何查找“原始来历”,发现几乎没有头绪。
现在能着手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这个黑皮包,再一个,就是那个死人。
死人当然就是那个“金丝眼镜”,他身上肯定有证件或者车票之类,能查出此人真实来历,但这些东西肯定都在警方手中,我们现在躲之唯恐不及,不可能去自投罗网。
那就只有从这个黑皮包入手,于是我们又打开皮包,一件一件摆出里面的所有东西,发现唯一能着手的,只有那张黑纸。
于是周结巴再次打开黑纸,他说感觉摸起来感觉类似一种油纸,就是用来做油纸伞或者包食品的那种。
打开黑色油纸,我们又盯着那两排白色“怪字”看,看了一阵,我突然有个发现,这两排“怪字”似乎不是写或者描上去的,而是印上去的,因为它明显有一种“漂浮”感。
周结巴也说有点像印上去的,但现在这个不是重点,关键是这两排文字是不是文字,有什么意思,跟倒脸石俑有没有关系。
我说,搞不懂。
边说边把那把短铁铲拿起来,问,说这种铁铲什么地方能买到?
周结巴打个哈欠,说卖旧货卖古玩的地方都能买到,查这个是查不出来的,现在唯一的线索就只有这张“黑油纸”,他认识一个人,在昆明“护国路古玩城”做仿冒古籍的生意,此人见多识广多半认识这种“怪字”,可惜没有此人电话,要不这样,我们二人马上冒险回一趟昆明,找到这个人看能不能破译那两排“怪字”的含义,说不定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原始来历”的一丝线索。
我愣住了,问,现在就回昆明?
周结巴把黑油纸一卷,说事不宜迟,明天一早走。
第二天早上5点半就起了床,之前找人打听了一下,攀枝花到昆明南客站没有车,只有到客运中心去坐,最早一班好像是7点半,要坐6个半小时。
收拾好,出门喊了个车,天才蒙蒙亮,开了一截,我发现路边一个宾馆正是之前我跟雷老二住的那家,二楼上有一扇窗户是黑的,正是我们那个房间,也不知道是他在睡觉还是已经里面没人,他已经回昆明了。
6点过到了客运中心,买了票,等了一阵上了车。
一路无话,下午2点左右到了昆明“南窑车站”。
出了站,喊了个车,朝“护国路”走,那条路在昆明市中心,我好像听说过那儿有个规模很大的古玩城,但一次没去过。
到了“护国路”,找到古玩城,果然是一家大型古玩市场,外面雕梁画柱古色古香,里面隔成大小不一的门面,走廊上密密麻麻全是地摊,玉器古玩字画卖什么的都有,人也不少,人声嘈杂。
周结巴明显对这里很熟,在前面东绕西绕,在一家小门面跟前停下,有三个人正坐在门口打牌,玩“锄大弟”。
辉哥!他招呼一声,一个白脸男子抬起头。
周结巴走上前低语几句,辉哥瞟我一眼,站起来走进门面里头。
果然是个卖古籍的,门面也就三个平方米,书架跟玻璃柜上重重叠叠全是古书,线装书油印书,一股油墨的香味。
“拿来瞧瞧。”辉哥手一伸。
周结巴从编织袋里摸出塑料袋,打开,小心翼翼把那张黑色油纸展开。
辉哥鼻子忽忽一嗅:“什么味道?”
这时油纸已经完全展开,辉哥看了几眼,摸了摸纸张,又盯着那两排“怪字”看半晌。
“奇怪。”他道。
周结巴一愣:“咋了?”
“这东西你知道是啥不?”
周结巴嘿嘿一笑:“知道还问你个屁?”
“这是拓本。”
“拓本?就是拓印的纸?”
“对。”辉哥瞪了周结巴一眼:“你收过古籍你居然不知道?”
周结巴嘿嘿一笑:“拓本我咋不知道,但好像不是这种纸啊。”
“就这点奇怪。”辉哥又摸了摸油纸:“据我所知拓本不管拓什么都是用宣纸,而且还是生宣纸,熟宣纸还不行,你看这种纸,感觉是一种油纸,有点像桐油纸,但桐油纸我还没见过这种全黑色的,反正是一种油纸,但还没听说过用油纸来拓东西。”
周结巴点头:“那说不定你看错了,就不是拓本。”
辉哥双眼一鼓:“看错?要是看错了我把这张纸吃了信不信?”
“嘿嘿。”周结巴嬉皮笑脸:“给我一万块钱,你随便吃。”
“给你一巴掌!”辉哥气呼呼道:“来,你们来摸,先摸字正面,再摸字背面,看有没有不一样!”
周结巴赶紧去摸了一下,点点头,朝我道:“来,你也摸一下。”
我伸出手,正反面一摸,果然,那些“怪字”正面明显有凸出感,而背面明显是凹陷感,果然是蒙在一件东西上面拓印下来的。
我点点头:“对!拓印。”
周结巴嘴里“咝”一声:“那就是说,这些字原先刻在一个硬东西上面。”
“废话!”辉哥道:“石碑,摩崖,或者一个铁器铜器,都有可能。”
周结巴跟我对望一眼,周结巴道:“来,最关键问题,这些是什么字你认得出来不?”
辉哥不语,低头来回细看,“嗯?”了一声。
周结巴一喜:“什么字?”
“好像是......”辉哥说了一半,抬头朝外面吼:“苏老师!进来看一下!”
一个60多岁戴眼镜老者走进来,刚才打牌三人中就有他,原来叫苏老师。
苏老师左看右看,笑道:“好热闹嘎。怎哪样?”
“你帮我看看这些字怎么回事?”
苏老师低下头,看了一眼,又取下眼镜,瞪着一对泡泡眼看。
“是不是一种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字?”辉哥问。
“不是民族,是国家。”苏老师抬起头:“是西夏文字。”
各位好。下面我上传两张图片,第一张是西夏文,第二张就是那种拓片文字,因为隔了这么多年,当年资料又全部被冯华焚毁,我是按照记忆写成,中间应该有误差。
西夏文?
我跟周结巴对望一眼,心里都很激动,居然这么快找到文字出处!
“你确定?”周结巴问。
苏老师又看了一眼:“应该是。跟那副书法一模一样。”
周结巴一愣:“什么书法?”
旁边辉哥解释:“苏老师给一个客户装裱过几幅书法,上面文字就是用西夏文写的,我看过两次,笔画都很像,肯定就是,没错!”
苏老师却没吭声,盯着那些字,皱起眉。
周结巴有些紧张:“怎么?有啥问题?”
“啧啧。”苏老师摇摇头:“第一眼看上去很像,但现在一看,啧啧,总觉得有些地方不一样。”
“什么地方?”
苏老师伸指点了点:“我也不太懂啊,但总感觉这两排字组合方式有点奇怪,跟我见过的那些西夏字总觉得不一样。”
“那你意思不是西夏字?”
“是应该还是。”苏老师犹豫道:“可能是一种变体,像那些西域国家,他们的文字据我所知经常出现变体,就是同一种文字,组合方式不一样,目的好像是为了不同用途。”
“对。变体。”辉哥点头附和。
周结巴嘿嘿笑道:“你们说的也太高深了,我们这些粗人搞逑不懂,那苏老师麻烦再看看这两排字大致什么意思,有没有你认识的?”
“这你就考到我了,呵呵。”苏老师笑道:“我只是个装裱匠,这些东西,低头可见素味平生啊。”
“嘿嘿嘿。”周结巴看我一眼:“这位苏老师文绉绉的听不懂啊。”
“要不这样。”苏老师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这东西他应该认识。”
周结巴一喜:“谁?”
“就我那位客户,我这儿有他电话。”
苏老师说完起身离开,说回铺子找此人电话号码。
周结巴收起油纸,旁边辉哥问了一句,说这东西哪里搞来的,周结巴含糊说是“得胜桥”旧货市场一个朋友的,他不知道从哪里收来的,因为上面文字很古怪,委托他来查一下,看到底是啥东西,大致值多少钱。
等了十多分钟,苏老师回来了,说联系上那个人了,此人是XX区文化局一位退休干部,姓赵,以前是个科长,电话里他大致说了一下,赵科长似乎没什么兴趣,只是嗯嗯几声,说有空过来看看。
周结巴问,说你没问他认不认识西夏文字?
苏老师回答,说问了,赵科长说他也是半吊子水瓶,之前用西夏文字制作书法作品,也是一时兴趣,也是画猫为虎。
我跟周结巴都有些失望,周结巴把我拉在一边,问,咋办?
我说现在已经确定这块黑油纸是一张拓片,至于上面那些“怪字”是不是西夏文字暂且不提,现在至少可以确定,它们是从一块硬物上面拓下来的,既然跟那尊“倒脸石俑”放在同一个包里,很有可能二者来自同一个地方。
周结巴道,这还用你说?关键是来自什么地方。
我说,如果这些字真是西夏文字,据我所知西夏国以前在甘肃青海那一带,会不会是从那个方向的某个地方拓印下来的?
周结巴啐了一口,说,你妈X的尽说废话,甘肃青海这么大,上哪儿去找。
我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既然那位“金丝眼镜”就在保山坐的车,说不定那地方就在保山。
周结巴骂了一句,说保山也不小,人海茫茫,就算回去,从哪里入手?
我摇摇头,说,说的也是,要不......这单生意就算了。
算个屁!周结巴拍了拍旅行包,说,你再打退堂鼓扰乱军心,小心我一毛钱不分给你。
一时我也无语。
僵持一阵,周结巴看了看表,已经快4点。
一时都没主意,回到辉哥铺子,看他们几个打牌,看到7点过,辉哥叫我们不要走了,就在这儿喝酒,几年没见,好生整几瓶。
我跟周结巴也老实不客气坐下来,四五个人包括苏老师一阵海喝。
喝到11点过,桌子上只剩下我,周结巴跟辉哥,眼看酒局就要结束,苏老师忽然匆匆走过来,身后还跟了两个人。
“二位,暂停一下。”他道。
我们三个都放下酒瓶,诧异抬头。
“来介绍一下。”苏老师指着身后一人:“这位就是赵科长。”
赵科长六七十岁,大腹便便,另外一人50多岁,瘦高个,一脸严峻。
“就他。”苏老师朝周结巴一指:“东西就在他身上。”
赵科长上下打量周结巴一眼,笑道:“听说你有个拓本想出手,我跟朋友过来看看,打扰各位酒兴,能否拿出来观摩一下?”
周结巴摇晃晃站起来,醉眼惺忪:“你不是说不感兴趣吗?”
赵科长尴尬一笑:“也是随口一说,好东西怎么能没兴趣,有兴趣有兴趣嗬嗬。”
旁边辉哥骂道:“你个死结巴还嘴臭!人家半夜三更跑起来你还在阴五阳五的,哪里有这样对客户的?”
“那行。”周结巴摇晃晃朝辉哥店面走:“东西在里头,要看就过来。”
苏老师三人赶紧跟上去,周结巴从包里又摸出那东西,在柜台上展开,那二人死死看了一阵,赵科长抬起头,问瘦高个:“如何?”
瘦高个抬头问周结巴:“这拓片小兄弟从哪里搞来的?”
“你管我从哪儿搞来?”周结巴借着酒劲道:“你就给老子说,这两排字写的啥意思?”
身后辉哥在骂:“他娘的周学良你还给鼻子上脸了是不是!”
旁边苏老师问:“这不是西夏字?”
高个子不置可否,低声对赵科长道:“是不是无关人员回避一下?”
赵科长点点头,朝苏老师笑道:“这样,我跟况教授想单独跟这位周兄弟交流一下,你们几位是不是——”
苏老师一愣,尴尬笑道:“行行行,我们先回避。”
赵科长看我一眼:“这位朋友——”
“他不用!”周结巴醉醺醺道:“他跟我一伙的。”
这时苏老师已经走出店门,走到酒桌那头坐下,兀自朝这边张望,一脸悻悻然。
“好。”高个子况教授道:“现在你能说说这东西的来历了吧。”
周结巴斜眼看他:“你先说这是啥东西,写的啥意思?”
况教授忽问:“你们是不是从贵阳来?”
“贵阳?”周结巴瞟我一眼:“不是。”
“这东西——”况教授一指:“跟贵阳有没有什么关系?”
“屁个关系!是从保——”周结巴一下停住:“你怎么老说贵阳,贵阳又怎么了?”
况教授面如寒冰,缓缓道:“这种文字居然又现世了,看来那个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并非虚言。”
赵科长点点头:“你是说那个《辽史补遗》?”
“对!”
旁边我跟周结巴都是一头雾水,周结巴抢先道:“喂喂你们在说什么,什么记载不记载?”
“两位朋友。”况教授冷森森看我一眼:“你们难道还没意识到,你们已经得到一件无价之宝?”
“啊?”周结巴跟我面面相觑,我实在忍不住:“啥?啥无价之宝?”
“这两排东西——”况教授伸手一指:“要是我判断没错,就是传说中的西夏死书。”
“西夏死书?”
周结巴跟我面面相觑:“什么东西?”
“也算一种西夏文字,但是——”赵科长似乎也不了解,看着况教授。
“1036年野利仁荣创造西夏文字。”况教授道:“这个基本历史二位搞古玩的应该知道吧。”
周结巴看我一眼,茫然点头:“好像——知道。嗯,知道。”
我心里暗骂:脸皮厚!
“根据史料,从1034年李元昊下令造字,到野利仁荣1036年功成,中间只有短短不到两年时间,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疑点,因为这完全不符合造字的规律,直到后来,具体什么时间我记不太清楚,有人发现了一条史料,内容是野利仁荣生前曾经提到他当年造字其实是根据党项族一位前辈族人留下的原始西夏文字,但很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条史料里没有记载那位前辈的身份姓名,处于什么时期,当然也没有所谓那种原始文字的任何信息,所以这么多年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条史料是后人伪造的,是野史,直到前年,1996年。”
“96年?怎么?”周结巴问。
“9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了一件文物,是一本古籍残卷,当时没有书名,作者也不详,拍卖方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辽史补遗》,《辽史》你们知道吧,是一本古籍,那本残卷就应该是对《辽史》进行了补充,所以取了那个名字,这本残卷我没看过,但是据说里面有一段记载,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诡异,居然提到了那种原始文字。”
“就那什么野利说的那种?”我问。
“野利仁荣。”况教授点点头:“对!因为我是搞古文字的,对那段话记忆深刻,我现在可以背给你们听——‘十四年,太祖命瞿宗寅制文,寅献铜书十二卷,字若斜鱼,非鬼神未识也’!”
“鬼神?”周结巴嘿嘿一笑:“啥东西?”
“我一个字一个字解释给你们听。”况教授道;“十四年,据我考证应该是统合一十四年,也就是996年,太祖应该是指西夏太祖李继迁,整段话意思是公元996年,李继迁命令一个叫瞿宗寅的人造字,中间隔了若干年,瞿宗寅献上铜书十二卷,上面应该是他造出的西夏文,这里面最重要就是后面两段话,说,字若斜鱼,应该是形容那种文字的形状,像倾斜的鱼。”
“等一下!”
周结巴突然打断他,接着低头,瞪大眼睛去看那两排“怪字”,我也突然有一种奇异感觉,赶紧也盯着看,看了数秒,心头不由一震。
“看出来了。”赵科长嗬嗬一笑。
“全是斜的!”周结巴抬起头,有些气喘:“从右上往左下斜!我靠太鸡X玄了!”
“对。西夏死书。”况教授点点头:“我私下取了个名字,叫斜鱼文字。”
“你意思这些字就是西夏死书——”周结巴顿了一下:“为啥叫死书?它死了?”
“这时我们业内一种叫法。”况教授解释:“其实这里面有个问题很奇怪,如果那本《辽史补遗》是真品,就是说它不是现代人做的假货,那就证明之前关于野利仁荣的那条记载是真是可信的,他制造西夏文字时候的确参考了一位前辈的原始文字,这就有个问题解释不通,那就是各大史料为何对这条信息没有记录。”
“是啊。为啥?”
“说不准。我的看法,是那位叫瞿宗寅的人当年确定是造出了文字,而且给西夏太祖李继迁的确献上了十二卷铜书,但这之后一定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故,导致文字被废除,而且事故多半涉及到西夏王朝的某种忌讳,所以之后任何信息被严密封锁,之后野利仁荣也许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信息,通过这十二卷铜书造出了通用的西夏文字,但是却被严格封口,严禁说出以上造字来源,这就是我的判断!”
“嘿嘿嘿。”周结巴看我一眼:“这——这也太鸡X玄了,简直在像听故事,嘿嘿。”
“听故事?”况教授脸若寒冰:“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写自己的故事,就看你想写的精彩还是平庸。”
“是是是。嘿嘿。”周结巴干笑道:“教授的话我们肯定相信,您是教授对不对,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两排字写的什么意思?”
况教授摇摇头:“抱歉,我无法解读。”
周结巴一愣:“你也不懂?”
“我这样给你说。”况教授森然道:“西夏文字一共5382个字,目前确定能破译的是1355个字,至于这种原始的死书,因为目前据我所知没有找到任何传世的实物,所以死书这两个字目前还停留在概念阶段,我只能说你们手头这东西,极有可能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至于你们想破译这两段文字,很简单,你们如果相信我,可以让我借阅一下,我慢慢研究,如果不相信,你们开个价。”
“对对。”旁边赵科长道:“开个价,一切好谈。”
周结巴道:“你们意思想买?”
“对。”况教授道。
周结巴看我一眼,我摇摇头。
“不卖。”周结巴道。
“不卖?”况教授一脸失望。
“我还没说完。”周结巴道:“暂时。”
“你意思暂时不卖?”况教授皱皱眉:“那什么时间能,能不能定?”
“嘿嘿。”周结巴干笑两声。
我赶紧道:“是这样二位,我们目前在查一件事,跟这东西有点关系,查完了多半可以考虑出手。”
“查什么?”况教授马上问。
“这个不方便说。”
赵科长道:“听小兄弟意思,是不是破译了这两段文字的意思,你们就能查出那件事?”
我看了周结巴一眼:“对。”
赵科长转头小声对况教授道:“干脆,贵阳那边——”
况教授不语。
“又是贵阳。”周结巴问道:“贵阳到底有什么事?怎么突然一棒子支那那儿去了?”
“好吧。”况教授点点头,明显想通了一件事:“那你们去一趟贵阳,去找一个人。”
我愣住:“去贵阳干啥?”
“有一个女人,据说,她能解读这种文字。”
我跟周结巴对望一眼:“女人?谁?”
“这样。”况教授道:“我先给那个人联系一下,你们直接过去,他会详细给你们说。”
“等等!”我有些懵:“你的意思,贵阳有个女的,能破译这种西夏死书?”
“嗯。”况教授干咳几声:“大概是。”
“什么叫大概是?”周结巴不满:“那女的是什么人,专家还是博士后,居然比你都厉害,她见过那些文字?”
况教授干咳一声:“她——能写。”
我完全懵了:“她能写?她怎么写?照着什么东西?你不是说现在还没有传世下来的实物文字吗?”
“这样。”况教授朝门外瞟了一眼:“其实这件事我不该给你们说,因为——怎么说呢,这里头涉及到贵阳当年发生的一起——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起灵异事件,我是无神论者,照理说,咳咳,不该牵涉进那件事,但是——算了,在这里实在不方便说,因为里头涉及的内容太复杂,又过了这么多年,有些东西根本无法解释,你们要不这样,我看二位也是急着办事,这样,你们去贵阳找我那个朋友,之后他会给你们提供方便,我也希望你们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但我有个要求希望二位满足。”
周结巴道:“啥?说?”
“就是你们办完事,如果确定要出售这块拓片,可否把我二人当做第一考虑对象?”
“就是说卖给你不卖给别人嘛。”周结巴不耐烦:“文绉绉的。行,没问题。”
@ty小小猫咪 2018-11-05 21:49:06
特喜欢看这种关于历史疑案的小说
-----------------------------
嗯。
送走赵科长二人,已经快12点。
古玩城的门早就关了,辉哥认识门卫,开了门放我们出去。
夜色深沉,我跟周结巴走到附近一座桥头,停下来望着盘龙江抽烟,边抽边商量下一步行动。
按照那位况教授所说,这两排“怪字”极有可能就是他说的“西夏死书”,按他说的,是公元996年被一个叫瞿宗寅的人创造,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废掉,但是在40年之后,被那个什么野利仁荣用来当做参考,造出了现有的西夏文字。
周结巴说,这里头有个问题小关你注意到没有,要是真像那况教授说的,那我们手头这块拓片,那就是目前唯一一块现世的记载了西夏死书的古董,那不知道有多值钱,那不就是几万几十万,至少也得上百万的价格,就这点他感觉太玄,况教授多半言过其实。
我点点头,说其实我也觉得没这么好的事儿,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线索,也只有相信他说的,这东西就是那什么“西夏死书”,调查也只能朝这个方向,除此之外别无他选,关键是去不去贵阳。
周结巴骂了一句,说最后说的贵阳的事也很玄,总觉得况教授之前一直口若悬河,但最后说到那个女的,突然有些迟疑,好像有什么事不敢说一样。
我叹口气,说是很玄,居然他说里头涉及到一起“灵异事件”,又不说清楚,看来里头大有文章,那贵阳去不去?
周结巴丢掉烟头,说管他妈X的,现在只有这条道,走,到南窑车站去。
我一愣,说干啥?
周结巴说,干啥?买火车票,去贵阳。
到“南窑”已经12点半过,午夜的昆明火车站依然人头攒动,周结巴说他去排队买票,我则在门口等。
等了一阵,想方便,于是朝厕所走,走的时候感觉后面似乎有人在跟踪我。
回头一看,到处都是人,没看见有谁异常。
我突然有些紧张,赶紧进了厕所,三两下拉完,刚出门,突然有人在背后拍我一下。
我吓一跳,一看,竟然是宋建国。
“果然是你!”他一把把我拽到墙角,低喝道:“关小峰你搞啥名堂!”
“嘘——”我左右张望一眼:“你咋来了?”
“我刚才在车站门口押货,看见有两个人下出租车,有一个很像你,就跟来了,你到底咋回事,跟你一起的是谁?”
我犹豫一下:“一个朋友。”
“朋友?你们买票去哪里?”
我抠抠脑袋:“去一个地方办事。你能不能不管。”
“不管?”宋建国瞪视我:“亏我把你们当朋友,一个打一万多个电话不回,一个失踪,找到了却叫我不管他,他娘的你们个个把我当欺头!”
我一愣,想起一人:“对了,雷老二呢,他回来没有?”
“回来个屁!在楚雄!”
“楚雄?在那儿干嘛?”
“鬼知道!”宋建国气呼呼:“鬼知道你们在高啥名堂!对了,周学良呢,找到没有?”
我一凛:看来他没见过周结巴。
于是低声回答:“不清楚。”
“不清楚?你们不是去楚雄找他了吗,后来咋样,你怎么单独回昆明了?还鬼鬼祟祟卖火车票,你要去哪里?”
我抠抠脑袋:“总之一言难尽。要不这样,等我回来再慢慢给你讲。”
“慢慢讲?哼!”宋建国冷冷道:“怕你来不及。”
我一愣:“啥意思?”
“警察来找你了。”
我一惊:“什么?”
“今天上午的事儿,公司来了两个警察,说是市局的,来问你的情况。”
“你咋回答?”
“我还能咋说?就说你的确回昆明了,之后走了,不知道去哪里。”
我有些气紧:“他们怎么找起来了?没说什么原因?”
“他们问你认不认识周学良。”
“啊!”我大惊:“你咋说的?”
“我说周学良是谁,我不知道。”
“后来呢?”
“后来没问出东西,就走了。”宋建国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你老实说,刚才跟你一起的那个人是谁,是不是周学良?”
我吞了吞口水:“这个,你还是别问了,宋哥我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哼!”宋建国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他们走之前突然说了一个地名你知不知道?”
“地名?什么?”
“是其中一个问的,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叫‘羊鬼沟沟’的地方。”
“羊鬼沟沟?在哪里?”
“我咋知道!是警察突然问起的,多半跟那件‘挖眼案’有关,你后来没听周学良说过?”
“没有——”我忽然止住,意识到失言了!
“哼哼!”宋建国很有深意的看我两眼,看表情已经知道那人就是周结巴了。
“那好。”他放开手:“你不想说我也不问了。”
我有些愧疚:“宋哥,有些事情——”
“算了。”他挥手打断我:“我先回了,你自己小心。”
说完他拍拍我肩膀,转身离开。
我愣愣站了一会儿,才回到售票厅,周结巴还在排队,我找了个墙角蹲下,摸出烟,狠狠抽了几口,脑子里一片浆糊。
这是昨晚上我翻出来的“倒脸石俑”图片,也不知道哪天画的。
其实石俑本身明显是一个古人,可惜本人画艺不精,画不出古风,各位将就看吧。
在候车厅窝了一夜,凌晨6点过上了火车,是一趟普快,2078次,要开11个小时。
一路无话,下午5点过到了贵阳。
下车后马上联系那个人,此人姓邱,是一家报社职工,电话里他叫我们到“文昌北路”,他单位在那儿。
到了报社门口,一个人匆匆跑出来,是个40多岁平头,他把我们拉进旁边一家馆子,喊了几个菜。
“况教授给我说了。”老邱道:“你们准备来查什么?”
周结巴道:“他说你们贵阳有个女的会破译那种西夏死书。”
“破译?”老邱摇摇头:“其实她写的那些东西是不是西夏死书还没定论。”
周结巴一愣:“怎么讲?”
“其实关于那女的,好多东西传得很恐怖很邪门,我个人是觉得是以讹传讹,但老况不这么看,他断定那女人写出的东西是西夏死书,他这个人,啧啧,对古文字过于痴迷,我也说不赢他,毕竟他是我老师,在昆明民族大学教过我三年,所以他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但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这次来如果真想破译什么西夏死书,我觉得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周结巴跟我对视一眼,笑道:“你说了半天,那个女人到底咋回事?”
“还是87年的事。”
“1987年?”
“对。说那个女的突然能预测。”
“预测?怎么回事?”
老邱摸出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了一眼:“这人叫余卫红,是贵阳国营新民农机厂一个女工,87年时候突然传出来此人会预测,我当时在报社还是个实习记者,我有个同事专门去那个厂做过采访,说当时她好像23岁,大致在4月份左右她突然开始写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字,我这儿有张照片你们来看一下。”
我跟周结巴赶紧凑过去,老邱翻了几下小本子,翻出一张黑白照片。
“就这个。”老邱放桌上。
我定睛一看,照片上是一整块灰白色的物体,也不知道是纸还是布,中间出现一排黑色文字,明显用笔写的,歪歪扭扭,不是很清晰,显得很阴森。
再仔细一看,不由一凛,那些字明显全部朝同一个方向倾斜,左上到右下,而形状笔画跟拓片上的字基本相同!
我跟周结巴对视一眼,我道:“这就是她写的?”
“对。”老邱道:“据说最开始没人注意,以为她是写着玩儿的,后来发现不对劲,她写出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地方也越发诡异,一开始在纸上写,后来在墙壁上,有时候一个人在厕所里头,写在门上,而且最吓人的人是发现她写这些字的时候神情不对头,就像一个精神病人的神情,后来有人就问她,说你到底在写什么,最开始好像她没说,后来也不知道是谁问出来,说余卫红有一次说,这些字是主动从她脑壳里头冒出来的。”
周结巴瞪大眼:“脑袋里头冒字?”
“对。她就说那些字是莫名其妙出现在脑袋里头,时间不定,有时候早上有时候白天有时候半夜,冒出来后就必须写出来,要不写,全身会非常难受,还会耳鸣。”
“耳鸣?”周结巴干笑一声:“这也太玄了!”
“是很不可思议,我记得我们报社是87年5月份去调查的,还拍了照片,当时还找人研究了一下那些字,发现不是已知的任何文字,当然研究的人学问也不是很高,所以不能肯定,我记得当时有人问那个女人,说你自己能不能认你写的那些字,她当时说不行,认不出,当时就采访了这些,回来后领导却不准发,说是封建迷信,说那个女的肯定得了精神病,所以当时这条消息就没发,后来,我记得很清楚,87年8月29号,当时我们报社去调查的那个记者收到一条消息,很吓人,说那个女人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突然能读出她写的那些文字的意思,最诡异的是,她居然提前预测了29号那天的一起恶性事件。”
“什么事?”周结巴赶紧问。
“说起来很吓人,是关于南朝鲜的一起集体自焚事件。”
“自焚?”周结巴问:“怎么回事?”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就是说当时大致一星期前余卫红突然读出了她之前写的一段文字的意思,后来发现竟然是一段预测的话,预测了8月29号那天在南朝鲜就是韩国发生的一起自焚事件。”
我赶紧问:“那段话怎么说?”
老邱摇摇头:“这个资料我没搞到,但是我搞到了另外一份,也很诡异,你们来看。”
老邱边说,边翻到一页:“来,你们看。”
我低头一看,本子上写了一段话,很古怪——“东胡寒地,火神,月亏月圆。”
“东胡寒地,火神,月亏月圆?”周结巴抬起头:“什么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老邱笑了笑:“这是我后来搞到手的,据说是余卫红87年4月底写的一段文字,当然写的是那种怪字,当时她还不能解释其含义,是后来好几个月以后,有人叫她翻译那段话,她就在纸上写出这三个词组。”
我问:“莫非这也是一段预测?”
“对。也是一段预测。而且很准确,准度得让人毛骨悚然。”
周结巴抢先问:“又预测了什么事?”
“87年5月6号。”老邱怪笑了一下:“中国出了一件大事你们不知道?”
“一件大事?”周结巴看我一眼:“啥事?”
我脑子里飞速一转,隐隐想起一件事。
“看来二位不太关心国事啊。”老邱道:“这样,我先不忙揭秘,我先解释一下这三个词组的意思,东胡寒地,东胡,是一个古代部落,很久以前在东北黑龙江一带,寒地,顾名思义,就是寒冷之地,火神不用说了,就是最后一个词有点难度,月亏月圆,就是说月亮亏到月亮圆,其实是代表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对。”周结巴茫然点头:“又怎样?”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顿时身上冒出一身冷汗:“对了!是不是大兴安岭——”
“对!”老邱打断我:“87年5月6号,大兴安岭发生大火,到6月3号扑灭,刚好烧了接近一个月!”
“我X他大爷!”周结巴叫道:“是有这件事!”
“最诡异的是那两个词语——”老邱道:“——寒地。”
“寒地?”
“对。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当时就出了一声冷汗,原来大兴安岭那‘兴安两个字,在蒙古语里面就是‘极寒之地’的意思!”
“我靠!”周结巴看我一眼:“真的假的,这也太黑人了!”
我也有些气紧,赶紧问:“那,那女的后来咋样,现在在不在贵阳?”
“应该还在贵阳。”老邱道:“但是当时,就是第二年就是1988年时候,听说她发疯了。”
“发疯?”
“对。”老邱点点头:“是这样,当时报社那个记者其实很想追踪报道此事,但因为领导不批准,也只有暗中进行,但是很奇怪,就是在她预测了南朝鲜那起自焚事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突然不写了。”
“不写?”
“对!就是说她突然就不再写那些怪异文字了,之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大家都以为她是不是病好了,因为当时虽说都觉得她这种预测能力很神,但私底下都判断她应该是脑子得了一种病,不然一个正常人哪里会写这些怪东西,当时就以为她是不是病好了,就没有继续追踪下去,结果到了第二年就是88年,具体时间我记不住了,大致在年初吧,传来个消息,说她突然疯了,被家人送到了贵阳第一精神病院。”
“后来呢?”周结巴问。
“是这样的。后来因为我掉到行政部门,也没再管这件事,直到96年吧,大致年底时候况书明——就是况教授来贵阳参加一个学术会,我请他吃饭,喝酒时候说了这件事,当时就是当做一个饭后奇谭说的,没想到教授竟然大有兴致,还叫我把相关资料给他看,后来我就把我掌握的一些东西交给他,包括这张照片,他当时神情我记得很清楚,嘴唇都在发抖,说这种字不是那女人乱写的,是一种消失的文字叫西夏死书。”
“嘿嘿。”周结巴朝我笑道:“96年,就是他看了那什么《辽史补遗》之后。”
我点点头,问老邱:“那后来呢,他肯定去找了那个女的。”
老邱点点头:“对,他第二天就去找了,但很快就回来了,脸色很难看,我就问他如何,他也没说,就叫我随时留意那个女的,有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那女的现在在哪儿?”周结巴急问。
“她据说病治好了,回厂宿舍区住了,至于在哪儿上班我就不太清楚,好像在外面哪家公司当保洁员。”
周结巴一喜:“哪个厂的宿舍区。”
“就她原单位,贵阳新民农机厂。”
吃完饭已经7点过了,老邱说他还有点事,就不作陪了,有什么要帮忙的就直接找他,老师的朋友他一定尽力。
告辞出来,在街边一个书报亭买了一张《贵阳市地图》,蹲在路边查了一下,发现“新民农机厂”在贵阳城南,“省劳改局”附近,已经属于城郊了。
于是喊了个车,直接往那儿走,天黑时候找到了那个厂宿舍。
在门口跟一个门卫交流了一下,此人姓魏,魏大爷,发了他一杆烟,他说余卫红家的确在里头,5栋1单元302,但是她很久没住这儿了,平时都是她老母亲在住,她父亲几年前死了,她还有个二姐,时不时过来一下。
我问,那余卫红现在住哪儿?
魏大爷说,住单位。
我问单位在哪儿。
魏大爷朝外头一指,说,“蓝港洗脚城”,就在那头,她在里头当保洁。
问明位置,我们步行朝那头走。
走了一公里多,远远看见右首边出现很多铁路线,停下来看了看地图册,发现这就是“贵昆线”,要去的那个地方叫“铁二厂”,属于贵阳南郊,周围有好几个大单位,有个货运南站,一个电厂,一个劳改局医院,还有个中铁X局贵阳二公司,那个“蓝港洗脚城”就是跟该公司合营的,原先是公司职工洗澡堂,92年时候改建,变成一个洗脚城,位置就在货运站南边,挨着一条河,地图上标注为“小车河”。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马路边出现一栋五层白色高楼,楼背面有一座黑色小山包,山包后是一条河,应该就是“小车河”了。
我们无声走过去,只见大楼门口有几个霓虹灯字在闪——“蓝港洗脚城”。
门口有两个穿制服的保安,我们上前,谎称我们是余卫红老家表哥,有急事找。
等了足足20分钟,我忽然感觉背脊骨有股恶寒,回头一看,一个穿制服女人正慢慢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