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不会被吞
【原创】愿你收获爱情❤️又名前妻前夫的搞笑爱情故事披着文艺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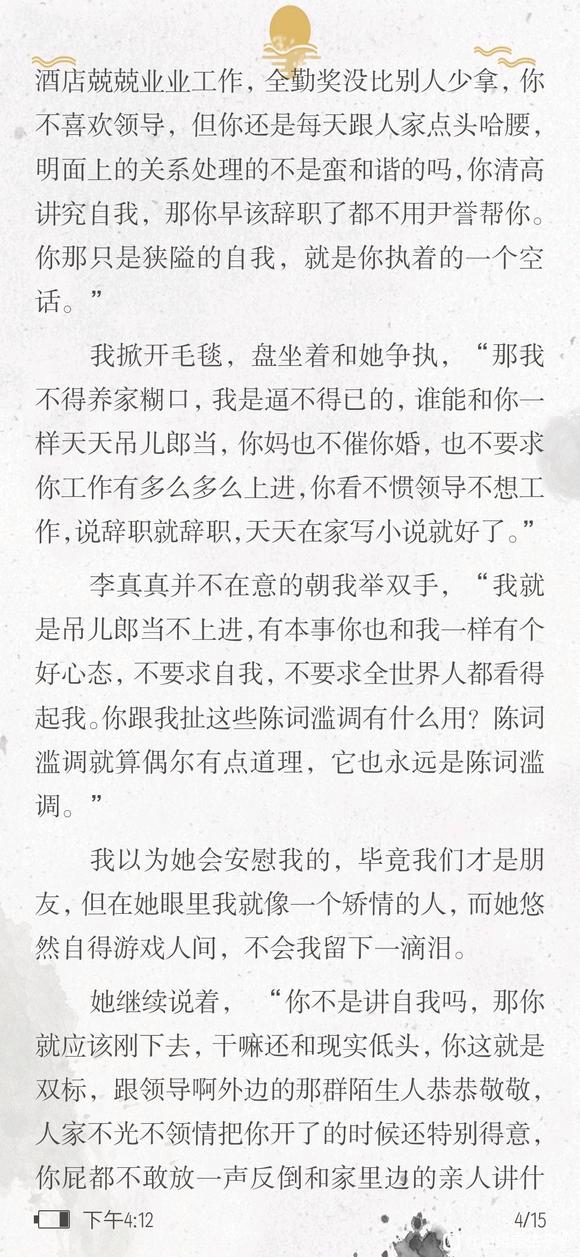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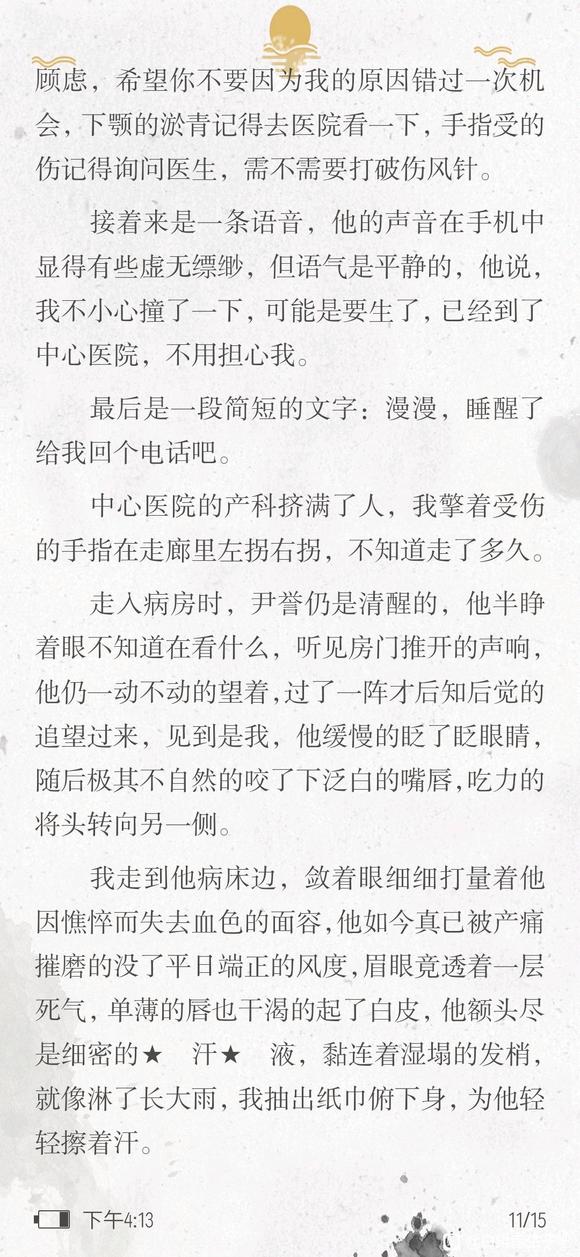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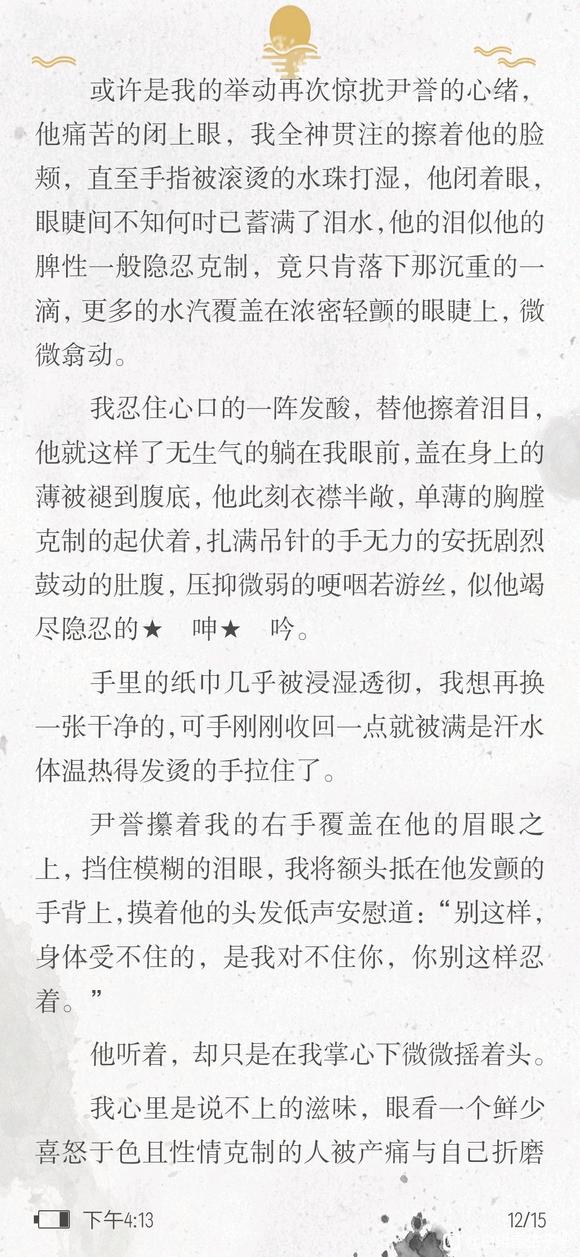
52
我敲开了李真真家大门,她正敷着面膜一脸见鬼的表情望着我。
她伸手戳了下我淤青的下颚,又碰了下我被医生缠成棒槌的食指,尖叫着,“陈以漫,你被家暴了!”
我迅速关上身后的防盗门,大声打断她的尖叫,“你才被家暴了!”
我缩在沙发上,小口啜吸着一杯热橙汁,李真真难得严肃的坐在我身边和我依偎在一起,缩在一张毛毯里,我歪着头枕在她的肩上,我们的头靠在一起,就这样安静的看着窗外的飘雪将世界装点成空虚的苍白色。
在女生懵懂的青春里的那些日子,我们就是这样亲密无间的相互依偎着慢慢度过的。
我眨着红肿的眼皮对她说着,“我吧觉得以前自己特别现实,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不是不知道职场不能交心的道理,但我就是想做一个被人喜欢的人,我想要被肯定,不像有人说对我失望。”
她贱兮兮的揽过我的肩膀,“很多人都喜欢你,从我认识你的时候起,你就比大多数人更容易被喜欢,你想听听我这个半吊子文学工作者的表白吗?”
我被她逗得忍不住笑了,伸手掐了她胳膊上的白肉,李真真也闹腾起来手总往一些奇怪的地方去摸,虽然这是女生间可以被接受的游戏,但我还是一脚把她踢下沙发。
她也不恼,笑着又迅速的爬上来和我挤在一起,我似乎是恢复了一些生气,表情也不像是刚进入这个屋子时一副被鬼缠身的样子。
我一边喝橙汁一边感慨,“其实我挺羡慕现在的生活的,起码我以前是羡慕的,人吧就是发贱,要钱、要面子、也要自尊自由,有些路吧,也知道是捷径,但有人逼着我去做,我就会难受,我有一种被爸妈限制但又不能顶嘴的感觉,感觉我离自己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远了。”
李真真回了句,“贱人就是矫情,你这活说的可真是矫情,但可以写在我的小说里。”接着又调侃我,“你既然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去试试新工作呢?陈以漫,我特别不喜欢人动不动就拿理想说事,你要记得你是个普通人。”
我反驳她,“古人不都是这样的嘛,讲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很重要,你有十分那么高的理想,往往最后你拼尽全力才能得到五六分现状的回报,你要是连个远大的理想都没有,你最后能混个三分就不错了。而且重点在于他不尊重我,这令我感觉很难受!好像是没有了自我。”
她坐起来凝望着我的眼睛说:“那你真心喜欢娱乐记者这份工作吗?这就是你的初衷吗?”
我欲言又止。
她却板下脸,“古人流行写诗,诗歌的特点就是浪漫,但浪漫讲多了就是空话。要我说,你今天冷静完了,该回哪就回哪去。辞了职,就去更好的新单位,别在这矫情。”
李真真冷淡的表情和窗外的冰冷的雪花融为一体,我有些愤怒,“但这不就算是放弃自我,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他的妻子不是孩子,他有想过他随手一按发送的辞职信可以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我被所有人指责,谁莫名其妙变成出卖公司的小人能不生气!”
她露出我很少能看见的带着嗤笑的眼神,这时候我甚至觉得李真真和吴桥是一类人,她说:“陈以漫,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想事情永远像个小孩一样,天天把自我挂在嘴上,可你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还真的讲究自我吗?你不喜欢当娱乐记者,但你依旧要每天蹲酒店兢兢业业工作,全勤奖没比别人少拿,你不喜欢领导,但你还是每天跟人家点头哈腰,明面上的关系处理的不是蛮和谐的吗,你清高讲究自我,那你早该辞职了都不用尹誉帮你。你那只是狭隘的自我,就是你执着的一个空话。”
我掀开毛毯,盘坐着和她争执,“那我不得养家糊口,我是逼不得已的,谁能和你一样天天吊儿郎当,你妈也不催你婚,也不要求你工作有多么多么上进,你看不惯领导不想工作,说辞职就辞职,天天在家写小说就好了。”
李真真并不在意的朝我举双手,“我就是吊儿郎当不上进,有本事你也和我一样有个好心态,不要求自我,不要求全世界人都看得起我。你跟我扯这些陈词滥调有什么用?陈词滥调就算偶尔有点道理,它也永远是陈词滥调。”
我以为她会安慰我的,毕竟我们才是朋友,但在她眼里我就像一个矫情的人,而她悠然自得游戏人间,不会我留下一滴泪。
她继续说着,“你不是讲自我吗,那你就应该刚下去,干嘛还和现实低头,你这就是双标,跟领导啊外边的那群陌生人恭恭敬敬,人家不光不领情把你开了的时候还特别得意,你屁都不敢放一声反倒和家里边的亲人讲什么自我,你是有病吧。”
我朝她扔枕头,“李真真你是我朋友,你怎么能在这时候这么和我说话呢!”
我敲开了李真真家大门,她正敷着面膜一脸见鬼的表情望着我。
她伸手戳了下我淤青的下颚,又碰了下我被医生缠成棒槌的食指,尖叫着,“陈以漫,你被家暴了!”
我迅速关上身后的防盗门,大声打断她的尖叫,“你才被家暴了!”
我缩在沙发上,小口啜吸着一杯热橙汁,李真真难得严肃的坐在我身边和我依偎在一起,缩在一张毛毯里,我歪着头枕在她的肩上,我们的头靠在一起,就这样安静的看着窗外的飘雪将世界装点成空虚的苍白色。
在女生懵懂的青春里的那些日子,我们就是这样亲密无间的相互依偎着慢慢度过的。
我眨着红肿的眼皮对她说着,“我吧觉得以前自己特别现实,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不是不知道职场不能交心的道理,但我就是想做一个被人喜欢的人,我想要被肯定,不像有人说对我失望。”
她贱兮兮的揽过我的肩膀,“很多人都喜欢你,从我认识你的时候起,你就比大多数人更容易被喜欢,你想听听我这个半吊子文学工作者的表白吗?”
我被她逗得忍不住笑了,伸手掐了她胳膊上的白肉,李真真也闹腾起来手总往一些奇怪的地方去摸,虽然这是女生间可以被接受的游戏,但我还是一脚把她踢下沙发。
她也不恼,笑着又迅速的爬上来和我挤在一起,我似乎是恢复了一些生气,表情也不像是刚进入这个屋子时一副被鬼缠身的样子。
我一边喝橙汁一边感慨,“其实我挺羡慕现在的生活的,起码我以前是羡慕的,人吧就是发贱,要钱、要面子、也要自尊自由,有些路吧,也知道是捷径,但有人逼着我去做,我就会难受,我有一种被爸妈限制但又不能顶嘴的感觉,感觉我离自己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远了。”
李真真回了句,“贱人就是矫情,你这活说的可真是矫情,但可以写在我的小说里。”接着又调侃我,“你既然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去试试新工作呢?陈以漫,我特别不喜欢人动不动就拿理想说事,你要记得你是个普通人。”
我反驳她,“古人不都是这样的嘛,讲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想很重要,你有十分那么高的理想,往往最后你拼尽全力才能得到五六分现状的回报,你要是连个远大的理想都没有,你最后能混个三分就不错了。而且重点在于他不尊重我,这令我感觉很难受!好像是没有了自我。”
她坐起来凝望着我的眼睛说:“那你真心喜欢娱乐记者这份工作吗?这就是你的初衷吗?”
我欲言又止。
她却板下脸,“古人流行写诗,诗歌的特点就是浪漫,但浪漫讲多了就是空话。要我说,你今天冷静完了,该回哪就回哪去。辞了职,就去更好的新单位,别在这矫情。”
李真真冷淡的表情和窗外的冰冷的雪花融为一体,我有些愤怒,“但这不就算是放弃自我,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他的妻子不是孩子,他有想过他随手一按发送的辞职信可以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我被所有人指责,谁莫名其妙变成出卖公司的小人能不生气!”
她露出我很少能看见的带着嗤笑的眼神,这时候我甚至觉得李真真和吴桥是一类人,她说:“陈以漫,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想事情永远像个小孩一样,天天把自我挂在嘴上,可你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还真的讲究自我吗?你不喜欢当娱乐记者,但你依旧要每天蹲酒店兢兢业业工作,全勤奖没比别人少拿,你不喜欢领导,但你还是每天跟人家点头哈腰,明面上的关系处理的不是蛮和谐的吗,你清高讲究自我,那你早该辞职了都不用尹誉帮你。你那只是狭隘的自我,就是你执着的一个空话。”
我掀开毛毯,盘坐着和她争执,“那我不得养家糊口,我是逼不得已的,谁能和你一样天天吊儿郎当,你妈也不催你婚,也不要求你工作有多么多么上进,你看不惯领导不想工作,说辞职就辞职,天天在家写小说就好了。”
李真真并不在意的朝我举双手,“我就是吊儿郎当不上进,有本事你也和我一样有个好心态,不要求自我,不要求全世界人都看得起我。你跟我扯这些陈词滥调有什么用?陈词滥调就算偶尔有点道理,它也永远是陈词滥调。”
我以为她会安慰我的,毕竟我们才是朋友,但在她眼里我就像一个矫情的人,而她悠然自得游戏人间,不会我留下一滴泪。
她继续说着,“你不是讲自我吗,那你就应该刚下去,干嘛还和现实低头,你这就是双标,跟领导啊外边的那群陌生人恭恭敬敬,人家不光不领情把你开了的时候还特别得意,你屁都不敢放一声反倒和家里边的亲人讲什么自我,你是有病吧。”
我朝她扔枕头,“李真真你是我朋友,你怎么能在这时候这么和我说话呢!”
李真真拿着手纸替我擦擦流出来的鼻涕,叹了口气,语气却格外真诚,“那我也告诉你,就因为我是你朋友,我把自己当成是你一辈子的朋友,我才得把话给你说明白了。我要不是真心当你朋友,我这时候就应该哄着你、依着你,鼓励你追求自我,女性要独立!女性要自由,让你赶紧去和尹誉离婚,谁叫他不尊重你,他怎么那么自私,怎么能把你那个没前途、搞关系、一门心思想压榨死你的破工作给辞了,怎么那么自私的托人找关系给你安排个好活?你就该离婚,听我的,离,咱们明天就离!”
我愁眉苦脸,“到也……没到离婚的地步吧。”
她说:“我告诉你陈以漫你现在不是个学生了,婚姻这个东西很复杂,周围那些听你一抱怨丈夫的不好就立马叫你离婚的,不是自己婚姻不幸,就是想方设法也让你不幸,婚是想离就离的吗?离了婚就能解决问题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也不看看你多大了,你是美得天下第一吗,家里有几亿资产吗,还是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才华?你再离婚了,可就快要三婚了,别说你现在还多一孩子,你以后上哪还能找想尹誉这么好的男人。”
李真真无比真诚的看着我,她告诉我,“陈以漫,你一直都是很好很好的家伙,不要因为别人而对自己失望,你要有自我,但同时也要现实,我们虽是个体,但都脱离不开这个社会,你的自我要用在对自己的肯定上,你的自尊心也要建立在对自己的信任上,没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但有相对的价值实现,你就是我心里最棒的记者!”
她的话我似乎听懂了,但有似乎没有完全听懂,但却给当时不断自我否定自己一个明亮的希望。
她继续分析,“而且,婚姻中的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尹誉出轨了,或者他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伤害你了,那你必须离,你不光要离,还得让他净身出户!该是你的,吐都得让他吐出来,想要女菩萨自己去庙里上香求去。我到时候去他学校替你撕烂他的嘴,这是原则问题!说明这男的人品有问题。”
我的眼前竟然真的浮现出她真的会冲进尹誉的课堂,扔臭鸡蛋,然后被保安无情的拖走的画面,有点好笑。我就真的笑出来了。
她被我笑得浑身发毛,强行把棒棒糖塞进我的嘴里,等我安静了她才继续说:“现在来分析你们现在的问题,他不经你的同意把你工作辞了,你觉得他不尊重你,没有替你考虑到你在公司危急时刻辞职别人会怎么看你对吧?”
我沉默着点头。
我愁眉苦脸,“到也……没到离婚的地步吧。”
她说:“我告诉你陈以漫你现在不是个学生了,婚姻这个东西很复杂,周围那些听你一抱怨丈夫的不好就立马叫你离婚的,不是自己婚姻不幸,就是想方设法也让你不幸,婚是想离就离的吗?离了婚就能解决问题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也不看看你多大了,你是美得天下第一吗,家里有几亿资产吗,还是有什么特别出众的才华?你再离婚了,可就快要三婚了,别说你现在还多一孩子,你以后上哪还能找想尹誉这么好的男人。”
李真真无比真诚的看着我,她告诉我,“陈以漫,你一直都是很好很好的家伙,不要因为别人而对自己失望,你要有自我,但同时也要现实,我们虽是个体,但都脱离不开这个社会,你的自我要用在对自己的肯定上,你的自尊心也要建立在对自己的信任上,没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但有相对的价值实现,你就是我心里最棒的记者!”
她的话我似乎听懂了,但有似乎没有完全听懂,但却给当时不断自我否定自己一个明亮的希望。
她继续分析,“而且,婚姻中的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如果尹誉出轨了,或者他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伤害你了,那你必须离,你不光要离,还得让他净身出户!该是你的,吐都得让他吐出来,想要女菩萨自己去庙里上香求去。我到时候去他学校替你撕烂他的嘴,这是原则问题!说明这男的人品有问题。”
我的眼前竟然真的浮现出她真的会冲进尹誉的课堂,扔臭鸡蛋,然后被保安无情的拖走的画面,有点好笑。我就真的笑出来了。
她被我笑得浑身发毛,强行把棒棒糖塞进我的嘴里,等我安静了她才继续说:“现在来分析你们现在的问题,他不经你的同意把你工作辞了,你觉得他不尊重你,没有替你考虑到你在公司危急时刻辞职别人会怎么看你对吧?”
我沉默着点头。
李真真轻拍着我的肩,“首先,于公,我觉得他做的不对,他应该事先和你商量,就这件事你必须和他严肃的说明,但不要在你正是气头上神志不清的时候聊,要点明如果再发生类似这种问题你绝对要他付出代价,至于效果如何,就取决于你调教男人的能力了。”
“但是于私吧,你看我是你朋友,我和尹誉没说过话,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是你告诉我的,可单就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尹誉不是一个自私不尊重人的家伙,他比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讲原则,甚至讲道理讲的都过了头,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发生的很诡异,就觉得不太像他能做出来的,要不你再问问他,最近受什么刺激了?”
“他能受什么刺激!”话刚说完,我又迟疑了,“也就是……撞见我带着前夫的戒指,还有……跟着江卓君跑了?”
她拍着我的脑袋,“陈以漫,你还是自我反思吧。”
“不是,为什么出了事情都要我反思。”但仔细一想,又勉为其难补了一句,“好吧,也有道理,这两件事我也反思。”
李真真点点头,“而且吧,我觉得这事他干的也不算特缺德,他把你那没什么前途的工作辞了,不是想把你扣在家里相夫教子当个家庭主妇,而是特地帮你实现梦想给你找了个更好的活,这么一想我觉得他很真挺像个光辉伟大的老父亲了。”
我把棒棒糖塞进她嘴里,“你闭嘴吧,我在家就天天当儿子了,结了婚又给他当儿子,我闲的我。”
她有些嫌弃的把糖丢尽垃圾桶,又迅速漱口,“关键是他管你和你讲道理,你听吗?”
我思索了片刻,“我……偶尔?”
她大手一挥,下了定论,“我觉得把你俩都没什么大错,夫妻俩闹矛盾很正常,而且你今天心里这么难受,很大原因是因为你今天遇上了太多倒霉事了,你正好把这些都赖尹誉一个人身上了。”
我说:“这就完了?”
她说:“完了,分析完了,要不你和我喝两杯,一会就忘了。”
我拒绝了她,一天的争吵早已令我分外疲惫,等世界安静下来,我感受着空调淡淡的暖风,眼皮愈来愈沉,在轻轻的抽泣中睡了过去。
“但是于私吧,你看我是你朋友,我和尹誉没说过话,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是你告诉我的,可单就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尹誉不是一个自私不尊重人的家伙,他比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讲原则,甚至讲道理讲的都过了头,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发生的很诡异,就觉得不太像他能做出来的,要不你再问问他,最近受什么刺激了?”
“他能受什么刺激!”话刚说完,我又迟疑了,“也就是……撞见我带着前夫的戒指,还有……跟着江卓君跑了?”
她拍着我的脑袋,“陈以漫,你还是自我反思吧。”
“不是,为什么出了事情都要我反思。”但仔细一想,又勉为其难补了一句,“好吧,也有道理,这两件事我也反思。”
李真真点点头,“而且吧,我觉得这事他干的也不算特缺德,他把你那没什么前途的工作辞了,不是想把你扣在家里相夫教子当个家庭主妇,而是特地帮你实现梦想给你找了个更好的活,这么一想我觉得他很真挺像个光辉伟大的老父亲了。”
我把棒棒糖塞进她嘴里,“你闭嘴吧,我在家就天天当儿子了,结了婚又给他当儿子,我闲的我。”
她有些嫌弃的把糖丢尽垃圾桶,又迅速漱口,“关键是他管你和你讲道理,你听吗?”
我思索了片刻,“我……偶尔?”
她大手一挥,下了定论,“我觉得把你俩都没什么大错,夫妻俩闹矛盾很正常,而且你今天心里这么难受,很大原因是因为你今天遇上了太多倒霉事了,你正好把这些都赖尹誉一个人身上了。”
我说:“这就完了?”
她说:“完了,分析完了,要不你和我喝两杯,一会就忘了。”
我拒绝了她,一天的争吵早已令我分外疲惫,等世界安静下来,我感受着空调淡淡的暖风,眼皮愈来愈沉,在轻轻的抽泣中睡了过去。
早上。
李真真的手机开始反复响起恶俗的手机铃声,我头痛欲裂的睁开眼,手在地板上摸索一阵,狠狠把手机拍到她身上。
李真真吃痛的叫了一声,勉强睁眼看了眼手机,又把手机拍到我身上,“***电话。”
我一手捂着宿醉后混乱的脑袋,另外一只手又把手机丢回到她身上,“我妈给你打电话,她找你的。”
她啧了几声,接通了电话,打开免提,“阿姨好,您有什么事情吗?”
我听见我妈温和的说着,“真真早上好啊,漫漫在不在你身边?”
她对着空气点头,“她在,她来接电话。”
我披头散发的爬到手机边,睡眼朦胧的问:“妈妈,什么事?”
随后便听见我妈怒吼:“陈以漫你死哪去了?打你电话你不接,人家尹誉电话都打我这了,你快给人家回电话!”
我说:“我电话……不在身边。”
我妈在那边都快要急疯了,“尹誉好像要生了,你赶紧给人家回电话,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想些什么玩意,赶快回电话,你别叫我妈!”她话音未落我就从地板上蹦起来,动作太大,还踢了李真真一脚。
我爬到副驾驶找手机,昨天手机掉进副驾驶以后就接连不断的接到电话,但我因为生气压根就没理会。
手机多了十几个未接来电,尹誉打了三个,其他的都是我妈打来的。
微信也满是红点,尹誉倒是发了不少信息但有七八条都撤回了。
最后剩下两段文字和一段语音。
较长的一段文字是:漫漫对不起,对于这件事情我承认都是我的责任,我不应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发送文件,没想到这件事会为你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不是想为自己辩解什么,但我知道你是有理想的记者,这几天我看你反反复复修改辞职信,我可以体会到你的顾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原因错过一次机会,下颚的淤青记得去医院看一下,手指受的伤记得询问医生,需不需要打破伤风针。
接着来是一条语音,他的声音在手机中显得有些虚无缥缈,但语气是平静的,他说,我不小心撞了一下,可能是要生了,已经到了中心医院,不用担心我。
最后是一段简短的文字:漫漫,睡醒了给我回个电话吧。
中心医院的产科挤满了人,我擎着受伤的手指在走廊里左拐右拐,不知道走了多久。
走入病房时,尹誉仍是清醒的,他半睁着眼不知道在看什么,听见房门推开的声响,他仍一动不动的望着,过了一阵才后知后觉的追望过来,见到是我,他缓慢的眨了眨眼睛,随后极其不自然的咬了下泛白的嘴唇,吃力的将头转向另一侧。
我走到他病床边,敛着眼细细打量着他因憔悴而失去血色的面容,他如今真已被产痛摧磨的没了平日端正的风度,眉眼竟透着一层死气,单薄的唇也干渴的起了白皮,他额头尽是细密的★汗★液,黏连着湿塌的发梢,就像淋了长大雨,我抽出纸巾俯下身,为他轻轻擦着汗。
或许是我的举动再次惊扰尹誉的心绪,他痛苦的闭上眼,我全神贯注的擦着他的脸颊,直至手指被滚烫的水珠打湿,他闭着眼,眼睫间不知何时已蓄满了泪水,他的泪似他的脾性一般隐忍克制,竟只肯落下那沉重的一滴,更多的水汽覆盖在浓密轻颤的眼睫上,微微翕动。
我忍住心口的一阵发酸,替他擦着泪目,他就这样了无生气的躺在我眼前,盖在身上的薄被褪到腹底,他此刻衣襟半敞,单薄的胸膛克制的起伏着,扎满吊针的手无力的安抚剧烈鼓动的肚腹,压抑微弱的哽★咽若游丝,似他竭尽隐忍的★shen★吟。
李真真的手机开始反复响起恶俗的手机铃声,我头痛欲裂的睁开眼,手在地板上摸索一阵,狠狠把手机拍到她身上。
李真真吃痛的叫了一声,勉强睁眼看了眼手机,又把手机拍到我身上,“***电话。”
我一手捂着宿醉后混乱的脑袋,另外一只手又把手机丢回到她身上,“我妈给你打电话,她找你的。”
她啧了几声,接通了电话,打开免提,“阿姨好,您有什么事情吗?”
我听见我妈温和的说着,“真真早上好啊,漫漫在不在你身边?”
她对着空气点头,“她在,她来接电话。”
我披头散发的爬到手机边,睡眼朦胧的问:“妈妈,什么事?”
随后便听见我妈怒吼:“陈以漫你死哪去了?打你电话你不接,人家尹誉电话都打我这了,你快给人家回电话!”
我说:“我电话……不在身边。”
我妈在那边都快要急疯了,“尹誉好像要生了,你赶紧给人家回电话,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想些什么玩意,赶快回电话,你别叫我妈!”她话音未落我就从地板上蹦起来,动作太大,还踢了李真真一脚。
我爬到副驾驶找手机,昨天手机掉进副驾驶以后就接连不断的接到电话,但我因为生气压根就没理会。
手机多了十几个未接来电,尹誉打了三个,其他的都是我妈打来的。
微信也满是红点,尹誉倒是发了不少信息但有七八条都撤回了。
最后剩下两段文字和一段语音。
较长的一段文字是:漫漫对不起,对于这件事情我承认都是我的责任,我不应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发送文件,没想到这件事会为你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不是想为自己辩解什么,但我知道你是有理想的记者,这几天我看你反反复复修改辞职信,我可以体会到你的顾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原因错过一次机会,下颚的淤青记得去医院看一下,手指受的伤记得询问医生,需不需要打破伤风针。
接着来是一条语音,他的声音在手机中显得有些虚无缥缈,但语气是平静的,他说,我不小心撞了一下,可能是要生了,已经到了中心医院,不用担心我。
最后是一段简短的文字:漫漫,睡醒了给我回个电话吧。
中心医院的产科挤满了人,我擎着受伤的手指在走廊里左拐右拐,不知道走了多久。
走入病房时,尹誉仍是清醒的,他半睁着眼不知道在看什么,听见房门推开的声响,他仍一动不动的望着,过了一阵才后知后觉的追望过来,见到是我,他缓慢的眨了眨眼睛,随后极其不自然的咬了下泛白的嘴唇,吃力的将头转向另一侧。
我走到他病床边,敛着眼细细打量着他因憔悴而失去血色的面容,他如今真已被产痛摧磨的没了平日端正的风度,眉眼竟透着一层死气,单薄的唇也干渴的起了白皮,他额头尽是细密的★汗★液,黏连着湿塌的发梢,就像淋了长大雨,我抽出纸巾俯下身,为他轻轻擦着汗。
或许是我的举动再次惊扰尹誉的心绪,他痛苦的闭上眼,我全神贯注的擦着他的脸颊,直至手指被滚烫的水珠打湿,他闭着眼,眼睫间不知何时已蓄满了泪水,他的泪似他的脾性一般隐忍克制,竟只肯落下那沉重的一滴,更多的水汽覆盖在浓密轻颤的眼睫上,微微翕动。
我忍住心口的一阵发酸,替他擦着泪目,他就这样了无生气的躺在我眼前,盖在身上的薄被褪到腹底,他此刻衣襟半敞,单薄的胸膛克制的起伏着,扎满吊针的手无力的安抚剧烈鼓动的肚腹,压抑微弱的哽★咽若游丝,似他竭尽隐忍的★shen★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