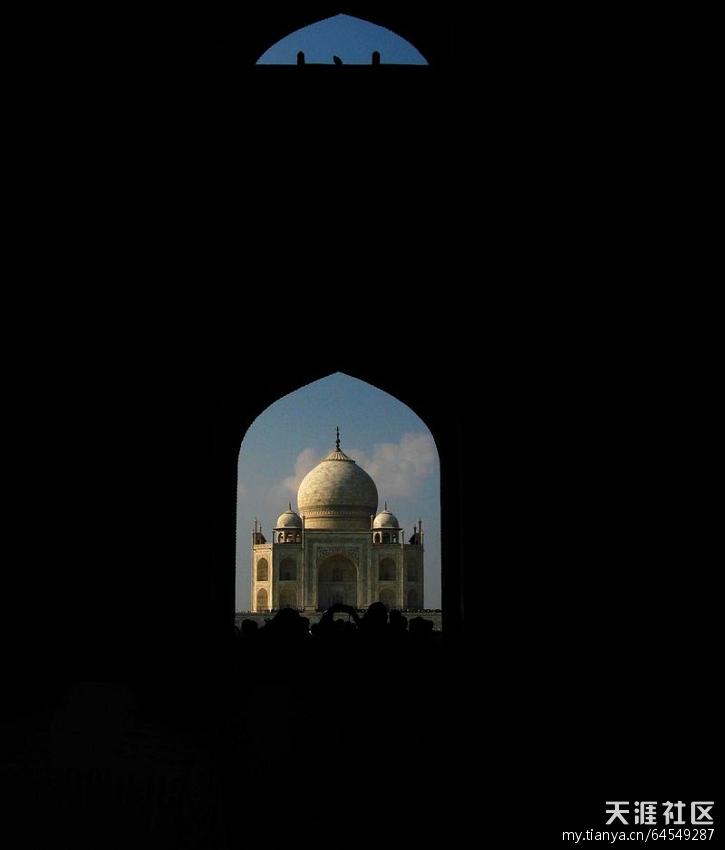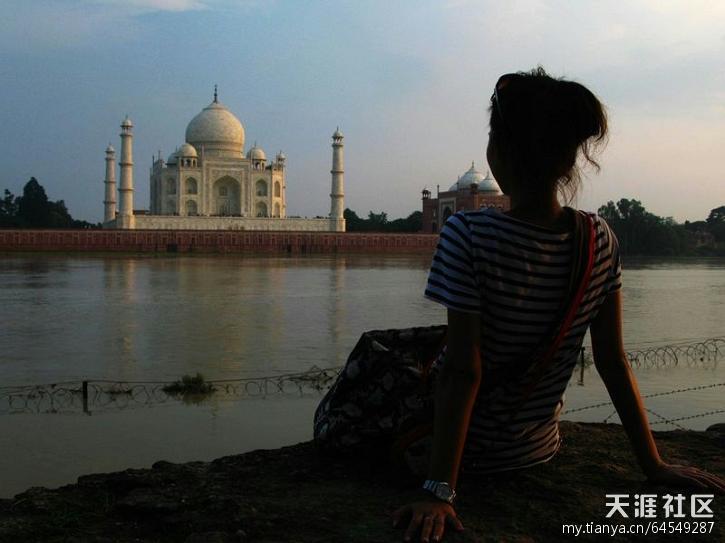在印度,八成的人民信奉印度教(Hinduism)。印度作家亚文德?雅迪加(Aravind Adiga)的畅销书《白虎》(White Tiger)中提到,印度教供奉三亿三千万零三个神祗。最大的三个神简称G.O.D.——负责生(Generation)的梵天,负责住(Operation)的毗湿奴和负责灭(Destruction)的湿婆,而这三个神又有无数的化身。
每当我稍微表现出一点对神的兴趣时,当地人便会兴致勃勃口沫横飞地告诉我谁的化身是谁,谁的配偶又是谁,配偶又有多少个化身,个别神如克利须那(Krishna)有16,000个情人,情人们又分别掌管什么,生下的孩子又是谁……
连象鼻神甘尼许(Ganesh)为什么长着大象脸都是有典故的!其中一个版本是:甘尼许出世时他的父亲湿婆已经远行,不知有这么个儿子。母亲帕瓦蒂(Pavarti)有一天在洗澡,嘱咐甘尼许看家,不要让陌生人进来。刚巧这天湿婆从远方回来,父子两人互不相识,湿婆非要进门,甘尼许非不让他进,湿婆一怒之下就把儿子的头砍了下来。等帕瓦蒂出来一看已经晚了,迁怒于丈夫。湿婆于是出门,把遇见的第一只动物,也就是一只断了一只牙的老象头带了回来,装在了儿子的身上。所以现在看到的甘尼许神像都有一只残缺的象牙。
以我个人的经验,这么多的神肯定是分不清楚的,记住几条特征就可以了:梵天只有在拉贾斯坦邦的布什格尔镇(Pushkar)被祭拜,平时是见不到的;克利须那是黑色长发吹笛子的,穿金戴银;湿婆是美型男,但脾气很爆,吸食大麻,手持三叉戟,爱跳舞;甘尼许是头大象,喜欢吃一种很甜的面球;而哈努曼就是我们的孙悟空。
路上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旅行者来到德里只去一个地方(Go one place),我忙问:“哪里?”
“他们只是离开! (They just go away)”德里人自嘲。
其实没有这么糟,排除所有的混乱和嘈杂,德里的街景很有看头。五花八门的店铺间穿梭着各“色”人种,他们通过服饰鲜明的表达自己:头上点Tikka穿彩色纱丽的印度教妇女,包黑色头巾蓄浓密大胡子的锡克壮汉,戴小帽子穿白衣的穆斯林男子身后跟着全身蒙着黑布见眼不见嘴的穆斯林女人,和牛,和狗,和拿着三叉戟的沙度(Sadhu),当然还有从世界各地来的花里胡哨的旅行者。
最妙的是,街头常常可以见到两个印度男子亲密地牵手甚至爱抚对方,而他们一再强调只是朋友。三个月的旅程后,我终于深刻地了解这确实是友谊的表现,与同性之爱完全没有关系,而相反印度男女之间则很保守,很少有在公共场合肢体接触的行为。
中午在Main Bazaar的Sam’s Cafe吃午餐,叫了银盘Thali,类似我们熟悉的套餐:两张Chapati,一种烤出来的面饼;一格土豆加青豆Masala;一格Raita酸奶;一份沙拉;一格不能识别的糊状物;以及一大勺米饭。
食物并不好吃,有趣的是印在员工T恤背后的文字:
If you are humble,
Nothing can touch you.
Neither praise nor disgrace,
Because you know what you are.
后来知道这是特蕾莎修女的话,大意为:如果你足够谦卑,就没有什么可以扰动你;无论是赞颂还是贬损,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印度,灵性的密语在很多微小的地方闪现,只等你去发现。
小贴士:在印度吃饭我从来没有给过小费,除非是非常满意,会留下约10%的金额凑成整数。

街头随处可见的暧昧,不再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