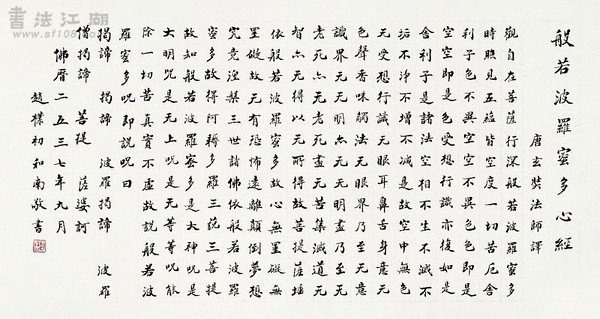天堂的雪终于呈现惨白的肤色
七色雨不经意间停住了脚步
无尾风悄悄加快了行踪
四季不太分明
似一个难测结局的预言
……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四季分明的天堂总能让你找到自己心灵的位置。但现在,这里的忘忧树、长恨花、恋风草甚至无心鸟都糊涂了,它们在迷茫地开放或是鸣叫,不懂眼前的情景,好像幻境中镜子里更加彷徨的自己。
你试着爱过一个人么?
你曾被爱人抛弃么?
你一定有父母亲人,你曾与他们做过突然的死别么?
你试着写下过自己的故事么?
我在我的故事中自卑
我的故事如此的混乱
注定无人问津
我的叙述这样平庸
难逃后人鄙夷地遗弃
然而
我却无法从我的故事中自拔
也无法挽救我低劣的叙述
因为我是个白痴
是个废物
我本身的想法比我的叙述更混乱
但我的故事还是成为了你我共鸣的一瞬
因为你我都曾爱过。
……
当爱人离开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多么地爱她。
就如同父王母后突然在我眼前离开,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我是多么地需要他们。
如果没有意识到爱,就不会感觉到痛。
如果没有痛,心便不会碎。
心若碎了,心就死了。
我不敢再问津爱情了,虽然我知道我也不会有再爱的资本和机会,但若再给我一次爱的机会,我想我会选择放弃,为了绝望而放弃。
……
我的血喷到很多人的身上,因为无尾风的缘故,在漫天的飞雪中那银色的鲜血象是一阵亮白的雾。楠佳似乎愣了一下,而后眼中迅速闪过一道我不懂的眼神,她慢慢将脸上的血揩净。子庄缓缓走过来,看着楠佳,眼中的光茫温柔而灼热。只有荼芥没有任何眼神,他将那杆红色的长矛高高举起,缓缓指向我心脏的位置。
这时,子庄一把抓住荼芥的长矛:“等一等,我不想让他就这么死掉,那样对他来说不是痛苦而是解脱,我要让他活着,活到他自己不想活了为止。”子庄的声音冷冷的,比这漫天的飞雪更寒,比荼芥的长矛更锋利。
我呆呆地站着,不知道为什么异常平静,我想想些事情,却发现什么也想不出来。即使是子庄用荼芥长矛废掉了我的右手,戳瞎了我的左眼时,我也没有吭声。真奇怪,我本来感觉很痛很痛,但马上又分不清这种热辣辣的断肠一样的感觉是什么,我有些糊涂了,我甚至分不清疼痛是何物了。
我用仅剩的眼睛看到禾族和叛军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像是在围观一个怪物。我真的不疼,你们不相信么?可是我说不出一句话,这才是令我心慌的,我成哑巴了?……
柳杨好像是惊叫了一声,然后便奔向子庄,我听不清她在冲着子庄嚷些什么。我只是呆呆地望着楠佳,血把我左边的脸全糊住了,很难受。楠佳的眼睛睁的大大的,可我已经读不懂她的眼神了。我和她的那些幸福仿佛忘忧树飘散的叶子,见到无尾风便石化成了粉末。这一刻是我最后一次以怀恋往日幸福的眼神望着她。我机械地把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了,很自然地盯在了地上,从此我便很少抬头去看谁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
我还在父王和母后的尸体旁,他们的表情那样的安祥,我感觉他们也许是睡着了吧。我握着他们冰冷的手,不忍心叫醒他们。
“穆渺!婵媛!你……你们以为一切都完了么?不!不!来人!把这两个贱人大卸八块,把他们剁碎!还愣着干什么!去!剁碎他们!全都剁碎!”荼芥突然像疯了一样,他夺过一柄长刀领着几名叛军冲了过来。
父王和母后的手很漂亮,白皙而有力,纹理都是那样细腻。我一直在渴望他们的手能抚摸我的头,轻轻地,柔柔地,就像这样。
我拿着父王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母后的手放在我的怀里,因为我的右手不好使了,所以一次只能让父王和母后中的一个抚摸我。
他们都向我投来惊异之极的眼光,那眼光中甚至有一种柔和和慌恐,也许还有丝歉意,我读不太懂。
我拿着父王的手,抱着母后的手,就呆呆地跪在那里。
父王和母后只能给我留下他们的手,其余的部分没有了,全没有了,荼芥他们让父王和母后消失了,一点儿都没有了。
……
“这个王子疯了。”不知人群中是谁这样说了一句,这让我有点生气,你们不认识我,凭什么说我呢?人群中有些在窃窃私语了,我听不清了。我也懒得去听了,现在是我理想实现的时候了,父母都在抚摸我的头。我先拿着父王的手抚摸,然后再拿着母后的手抚摸我的头,好开心啊!要是早下一场这样的雪有多好啊!父母就能抚摸我了,呵呵?……父王和母后终于摸到我的头了?……哈哈?……我禁不住笑出声来,我想唱歌,但却发不出声,只能“咿呀——咿呀——”地哼哼,不过没关系,有父母的手就足够了,这真是让人开心的一天。
子庄好像是走了过来,好像是把一个钩子钩进了我的前胸,好像钩住了我的一段骨头,好像钩得很结实,他一拽我就不得不跟着他走,好像有点疼。可是我感觉不太清楚,我只是轮换着拿着父母的手抚摸我的头,我笑了?……
“子庄!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还用刺骨钩折磨他!你?……”好像是柳杨,这个人我以前见过,还和她说过话,可是不太熟,她长得很漂亮。
“这样,他就跑不掉了,不过我倒不觉得他怎么样了,你看他痛苦么?他很开心也说不定,看,他还在笑呢?谁说刺骨钩是最折磨人的刑具,我看是一件让我开心的玩具,呵呵?……未来的王?被我牵着,呵呵?……”好像是子庄吧,我不太敢认,好久没见他了,听说他被人废了右手和左眼,还被人用钩子钩住骨头折磨,好可惜啊!本来想分给他一只手的,不过我只有父母这两只手了,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就算了吧,他就比我可怜多,至少我现在还有父母疼。
……
“全军回城!共庆胜利!现在天国统一了!”荼芥大喝一声,军队开始浩浩荡荡向王城走去,人好多啊。
……
我看到一个绝色美人,她长得美极了,白皙的脸庞好像罩着一层银色的目光,我以前认识一个叫楠佳的姑娘和她长的真是一模一样,后来去了哪里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美人哪里都好,就是眼圈有些发红,有些潮湿,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真让我很不好意思。
作为王子,我应该懂礼貌才对,父王和母后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于是我拿起父王的手向她摇了摇,再拿起母后的手向她摇了摇,对了,对人应该微笑,于是我又冲她笑了笑。
这个美女真是很没礼貌,竟然“呼”地一下背过身去不理我了,真是个奇怪的人啊!
……
七色雨不经意间停住了脚步
无尾风悄悄加快了行踪
四季不太分明
似一个难测结局的预言
……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四季分明的天堂总能让你找到自己心灵的位置。但现在,这里的忘忧树、长恨花、恋风草甚至无心鸟都糊涂了,它们在迷茫地开放或是鸣叫,不懂眼前的情景,好像幻境中镜子里更加彷徨的自己。
你试着爱过一个人么?
你曾被爱人抛弃么?
你一定有父母亲人,你曾与他们做过突然的死别么?
你试着写下过自己的故事么?
我在我的故事中自卑
我的故事如此的混乱
注定无人问津
我的叙述这样平庸
难逃后人鄙夷地遗弃
然而
我却无法从我的故事中自拔
也无法挽救我低劣的叙述
因为我是个白痴
是个废物
我本身的想法比我的叙述更混乱
但我的故事还是成为了你我共鸣的一瞬
因为你我都曾爱过。
……
当爱人离开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是多么地爱她。
就如同父王母后突然在我眼前离开,我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我是多么地需要他们。
如果没有意识到爱,就不会感觉到痛。
如果没有痛,心便不会碎。
心若碎了,心就死了。
我不敢再问津爱情了,虽然我知道我也不会有再爱的资本和机会,但若再给我一次爱的机会,我想我会选择放弃,为了绝望而放弃。
……
我的血喷到很多人的身上,因为无尾风的缘故,在漫天的飞雪中那银色的鲜血象是一阵亮白的雾。楠佳似乎愣了一下,而后眼中迅速闪过一道我不懂的眼神,她慢慢将脸上的血揩净。子庄缓缓走过来,看着楠佳,眼中的光茫温柔而灼热。只有荼芥没有任何眼神,他将那杆红色的长矛高高举起,缓缓指向我心脏的位置。
这时,子庄一把抓住荼芥的长矛:“等一等,我不想让他就这么死掉,那样对他来说不是痛苦而是解脱,我要让他活着,活到他自己不想活了为止。”子庄的声音冷冷的,比这漫天的飞雪更寒,比荼芥的长矛更锋利。
我呆呆地站着,不知道为什么异常平静,我想想些事情,却发现什么也想不出来。即使是子庄用荼芥长矛废掉了我的右手,戳瞎了我的左眼时,我也没有吭声。真奇怪,我本来感觉很痛很痛,但马上又分不清这种热辣辣的断肠一样的感觉是什么,我有些糊涂了,我甚至分不清疼痛是何物了。
我用仅剩的眼睛看到禾族和叛军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像是在围观一个怪物。我真的不疼,你们不相信么?可是我说不出一句话,这才是令我心慌的,我成哑巴了?……
柳杨好像是惊叫了一声,然后便奔向子庄,我听不清她在冲着子庄嚷些什么。我只是呆呆地望着楠佳,血把我左边的脸全糊住了,很难受。楠佳的眼睛睁的大大的,可我已经读不懂她的眼神了。我和她的那些幸福仿佛忘忧树飘散的叶子,见到无尾风便石化成了粉末。这一刻是我最后一次以怀恋往日幸福的眼神望着她。我机械地把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了,很自然地盯在了地上,从此我便很少抬头去看谁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
我还在父王和母后的尸体旁,他们的表情那样的安祥,我感觉他们也许是睡着了吧。我握着他们冰冷的手,不忍心叫醒他们。
“穆渺!婵媛!你……你们以为一切都完了么?不!不!来人!把这两个贱人大卸八块,把他们剁碎!还愣着干什么!去!剁碎他们!全都剁碎!”荼芥突然像疯了一样,他夺过一柄长刀领着几名叛军冲了过来。
父王和母后的手很漂亮,白皙而有力,纹理都是那样细腻。我一直在渴望他们的手能抚摸我的头,轻轻地,柔柔地,就像这样。
我拿着父王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母后的手放在我的怀里,因为我的右手不好使了,所以一次只能让父王和母后中的一个抚摸我。
他们都向我投来惊异之极的眼光,那眼光中甚至有一种柔和和慌恐,也许还有丝歉意,我读不太懂。
我拿着父王的手,抱着母后的手,就呆呆地跪在那里。
父王和母后只能给我留下他们的手,其余的部分没有了,全没有了,荼芥他们让父王和母后消失了,一点儿都没有了。
……
“这个王子疯了。”不知人群中是谁这样说了一句,这让我有点生气,你们不认识我,凭什么说我呢?人群中有些在窃窃私语了,我听不清了。我也懒得去听了,现在是我理想实现的时候了,父母都在抚摸我的头。我先拿着父王的手抚摸,然后再拿着母后的手抚摸我的头,好开心啊!要是早下一场这样的雪有多好啊!父母就能抚摸我了,呵呵?……父王和母后终于摸到我的头了?……哈哈?……我禁不住笑出声来,我想唱歌,但却发不出声,只能“咿呀——咿呀——”地哼哼,不过没关系,有父母的手就足够了,这真是让人开心的一天。
子庄好像是走了过来,好像是把一个钩子钩进了我的前胸,好像钩住了我的一段骨头,好像钩得很结实,他一拽我就不得不跟着他走,好像有点疼。可是我感觉不太清楚,我只是轮换着拿着父母的手抚摸我的头,我笑了?……
“子庄!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还用刺骨钩折磨他!你?……”好像是柳杨,这个人我以前见过,还和她说过话,可是不太熟,她长得很漂亮。
“这样,他就跑不掉了,不过我倒不觉得他怎么样了,你看他痛苦么?他很开心也说不定,看,他还在笑呢?谁说刺骨钩是最折磨人的刑具,我看是一件让我开心的玩具,呵呵?……未来的王?被我牵着,呵呵?……”好像是子庄吧,我不太敢认,好久没见他了,听说他被人废了右手和左眼,还被人用钩子钩住骨头折磨,好可惜啊!本来想分给他一只手的,不过我只有父母这两只手了,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就算了吧,他就比我可怜多,至少我现在还有父母疼。
……
“全军回城!共庆胜利!现在天国统一了!”荼芥大喝一声,军队开始浩浩荡荡向王城走去,人好多啊。
……
我看到一个绝色美人,她长得美极了,白皙的脸庞好像罩着一层银色的目光,我以前认识一个叫楠佳的姑娘和她长的真是一模一样,后来去了哪里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美人哪里都好,就是眼圈有些发红,有些潮湿,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真让我很不好意思。
作为王子,我应该懂礼貌才对,父王和母后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于是我拿起父王的手向她摇了摇,再拿起母后的手向她摇了摇,对了,对人应该微笑,于是我又冲她笑了笑。
这个美女真是很没礼貌,竟然“呼”地一下背过身去不理我了,真是个奇怪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