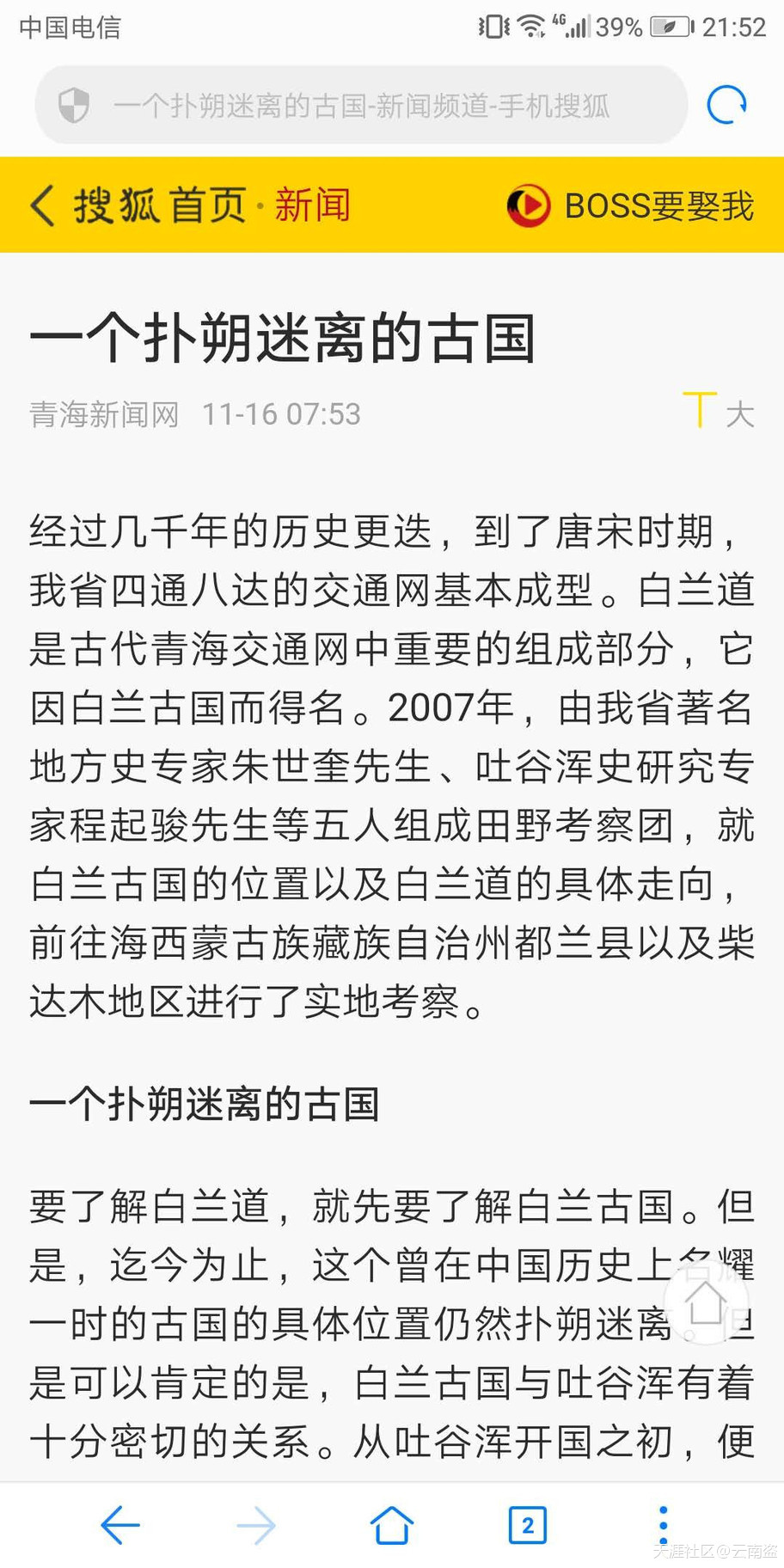江和尚吓得身子一抖,猛抬头,一下看见我。
“他——他——他是谁?”他惊得张口结舌。
他旁边,一下冒出两个脑袋,一个瘦脸是孙强,一个半秃,正是吴兴禄。
“嚯!”孙强一下认出来:“那个得梅毒的!”
“就他?”吴兴禄瞪着我:“他啷个在二楼?”
“不逑晓得!”孙强一下反应过来:“对了!肯定从翻窗子进去的!”
“给老子下来!”吴兴禄狠狠道。
我心念急转: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状况,时间紧急,没工夫跟他们打哑谜了,得尽快说明来意!
拿定主意,几步走下楼梯,那三人一脸惊惶,全部后退。
我一把扯下口罩:“江淮山,给老子张开狗眼看,我是谁!”
江和尚一凛,明显被我脸上的“尸蜡”镇住,打量我几眼,猛一下认出来:“搞X巴!关小峰!”
我点点头:“好眼力。”
“你跑这儿来干啥?”江和尚打量我,兀自不相信:“还有,你脸上又咋回事?”
“你们认识?”旁边,吴兴禄问。
“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江和尚道:“我跟他在保山坐过牢。还有,那次送棺也有他。”
“知道了。”吴兴禄点头:“听陈舜年说过,你们从神木岭救了个小伙子出来,就是他?”
“就他!”江和尚又来回打量我:“你咋跑这儿来了?”
我指了指二楼:“上头咋回事?”
江和尚一凛,瞟了楼上一眼,咧嘴一笑:“你看见了?”
我点点头。
“我跟陈老板弄过来的。”
陈老板!
我一凛:“陈舜年?”
江和尚点头。
我一下很兴奋,左右到处看:“他也来重庆了?我靠!在哪儿?”
“才走。”江和尚道:“到成都去了。”
我一愣:“成都?去成都干啥?”
江和尚嘿嘿一笑:“有事。”
我正要追问,这时听到身后有人呻吟,回头一看,黎兰已经醒了,睁开眼,一脸迷蒙到处看。
“你咋样?”我赶紧问。
黎兰一下看见我,张开嘴,突然又看见了其他人,欲言又止。
“她是谁?”吴兴禄冷冷问。
“我朋友。”我道。
“朋友?”吴兴禄一脸寒霜,厉声问:“你们一个鬼鬼祟祟在门口偷看,一个偷偷摸摸爬到二楼去,你们想做啷门(注:什么)?”
我叹口气,指了指我脸:“有人叫我来找你。说你能治我这个东西。”
“谁?”
“表哥。”
吴兴禄一凛:“徐万忠?”
我点点头。
“他人呢?”吴兴禄兀自不信。
我指了指地面:“下去了。”
吴兴禄没听懂:“下去?下哪儿去了?”
我犹豫一下,心说这哪儿说得清楚,还是先办正事要紧。
“要不这样。”我道:“你先给我看一下。看完我给你说。”
吴兴禄呆呆瞪视我,半晌才指了指旁边一道门:“小孙,带他先进去。”
孙强犹豫一下,推开门,示意我进去,我也没办法,只好走进去,里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孙强关上门,只听他们三个在外面嘀嘀咕咕,我也懒得偷听,一屁股坐床上。
足足等了10分钟,吴兴禄才走进来,顺手关上门。
他没理我,开始戴手套,又戴上口罩,这才走过来,来回打量我脸,又伸手碰了一下:“啥感觉?”
我摇摇头:“没感觉。”
想起一事,冷笑了一下:“那个姓孙的说这个是二期梅毒。”
“把衣服脱了。”吴兴禄冷冷道。
我三两下脱去衣服,露出上半身,一时盯着天花板,不敢去看。
吴兴禄定定看了半天,点点头:“好。穿上。”
我一愣:“完了?”
“完了。”吴兴禄扯开口罩。
“不用药?”
“用药?”吴兴禄鼓起眼睛:“我想不出办法。用什么药!”
我心一紧:“啥意思?你是说我这个——”
“我治不来。”
“治不来?”我顿时大急:“那,那你知不知道是啥东西?”
吴兴禄盯着我,摇摇头,眼神有些怪。
“他们说是尸蜡,是不是?”
吴兴禄冷冷一笑:“你又没死。啷个会是尸蜡!”
“那是什么?”
吴兴禄冷冷盯我,半天才道:“有种东西,叫‘鸡婆皮’,你听说过没有?”
鸡婆皮!
我一愣:“没听说!什么东西?”
“没听说就算了。”吴兴禄冷冷道:“你肯定去过童古寨,那儿有一座瞿婆庙,里头有幅画,画上面那个人的脸是空白的,没画五官,你晓不晓得这件事?”
我一凛:“知道!说那个人就是瞿婆!”
“嗯。”吴兴禄点点头:“那个人不是神话编出来的,历史上就有这个人,有名有姓,叫瞿宗寅。”
“瞿宗寅!”
我脑子里怪光一闪:这名字好像谁提到过!
“对。”吴兴禄道:“画上面为啥没画出她的脸,你晓不晓得原因?”
“什么?”
“她的脸被活生生换掉了。”
我一个激灵:“什么?”
“说她死之前身上长出了一层东西,后来活生生,把她身体整块皮,包括脸皮,全部换掉了。”
“换掉?”我喘不过气:“怎么换?”
“这个就不太清楚。”吴兴禄道:“反正说,最后她死之前活活换成了另外一张脸。”
“另外一张?”我喘口气:“换成什么?”
“不清楚。”吴兴禄冷冷道。
我吞了吞口水:“你意思,我身上长得这个,就是那个瞿宗寅身上长得那东西?”
吴兴禄一皱眉:“不好说。但有一点很像。”
“什么?”
“就是这种光泽。”吴兴禄道:“我看过一个小册子,上面有几句话提到了那件事,其中就说那个东西,像一层蜡。”
“像蜡?”我冷笑一下:“像蜡的东西多了!”
“嗯。”吴兴禄点点头:“所以你也不用紧张。我也是随口一说,说不定不是那东西。”
我有些气急败坏:“那你说个屁!”
吴兴禄瞟我一眼,默默脱掉手套。
我浑身突然像散了架,倒在床头,脑子里“嗡嗡嗡”乱响:那幅画上面,瞿婆的确没画出五官,居然是这个原因!
不过,他说的那什么‘鸡婆皮’也太玄了,怎么可能活活把一张脸换掉!这简直闻所未闻,肯定是乱编!
我不由抬手,看了一眼,那几坨“暗红”就跟恶灵一般,我突然有点想发狂,想拿起菜刀,干脆把手砍下来再说!
那我身上的那些东西呢,咋办!几刀,把身子也砍成几截?
我只感觉一阵狂躁,不由抓住床头的铁栏,“哗哗”一阵猛摇,摇得整个床“咚咚”敲地。
门一下开了,探进一个脑袋,是孙强。
“啷门?”他一脸惊惧。
“没事。”吴兴禄冷冷看我一眼。
这时江和尚走进来,拿着一个手机,“嗯嗯嗯”不行说。
他径直走到我跟前,把手机一递:“来。接电话。”
我一愣:“谁?”
江和尚蒙住嘴巴:“陈舜年。”
陈舜年!
我身子一震,赶紧“喂”一声。
“你好啊小关兄弟!”那头响起一个宏亮声音:“久违了,哈哈!”
我只感觉说不出的激动:不用说了,就听这个声音就知道,那头是陈舜年,如假包换!
“好个屁!”我张嘴就骂:“老子快死了!”
那头明显愣了一下,然后笑道:“哪里这么容易死?”
顿了顿,他又道:“这样,刚才江淮山把你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我现在在成都,不太方便过来,要不,你跟淮山到我这边来,我还有几件事要请教你,你看如何?”
我听得不耐烦:“如何个屁!今天就过来!不,现在!现在就过来!”
那头愣了一下,笑道:“哈哈哈,关兄弟就是爽快!好,我在成都恭候大驾。”
我点点头,想起一事,瞟了那三个人一眼,压低声音:“对了,我有个事情提前给你说一下。”
“什么?”
“关于你父亲。”我道:“我有他一条消息。”
那头忽然没声音,明显僵住。
过半天,才道:“我父亲?”
我一凛:他声音明显在发抖。
“对。”我又压低声音:“你就在成都等!老子过来给你说。”
挂了手机,我递给江和尚:“走!”
江和尚愣住:“现在?”
“对。”我跳下床:“陈老板说的。”
江和尚还在发愣,我不理他,走出里屋,外面,黎兰站那儿,手足无措,我赶紧把她拉到一边:“现在走。去成都。”
黎兰一愣,扫视我脸一眼:“那你身上——”
“他们治不好。”我咬咬牙:“管他妈的,死就死。”
黎兰像想起什么:“对了,他说不定有办法!”
我点点头:“你情夫?”
黎兰脸一红。
这时江和尚三人走出来,只见吴兴禄瞟了二楼一眼,点点头:“好。那就恁个(注:就这样)。那就等陈老板过来再说。”
我一凛:他们一定在说那副棺材,多半黑衣毕扒尸体不带走了,就留在这里。
一时也不好问,江和尚已经走过来,朝我挥挥手,我拍了拍黎兰,三人出了诊所大门。
外面,整个老街黑咕隆咚,我看了看手表,凌晨3点了。
很快回到路口,那辆越野车停在“富康”旁边,我们三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就开越野车过去,至于“富康”,江和尚说附近有个冶金公司,里头可以停车,干脆开过去停,等办完事回来再说。
黎兰犹豫了一下,同意了,于是一起开过去,停好,我正好把那个大旅行包放里头,只带了那个小包走,这样也好办事。
上了越野车,辨明方向,朝城外开去。
开了一截,我想起棺材里头的黑衣毕扒,忍不住问:“尸体咋回事?”
“给你说了。”江和尚道:“我跟陈舜年运过来的。”
旁边,黎兰一脸惊恐,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不相信:“从哪儿?神木岭?”
“算是吧。”
我没听懂:“算是?你们把尸体从那个洞穴里头抬出来了?”
“不是我们抬的。”江和尚道:“是桑花。”
“桑花?”
“嘿嘿。就她。”江和尚道:“她把她师傅从里头抬出来,然后埋在那座雪山底下,我们——嘿嘿,把尸体又给挖出来。”
挖出来!
我有些懵:“怎么回事?”
江和尚瞟了一眼后视镜,嘿嘿笑道:“不能再说了。再说下去,嘿嘿,这个妹儿绝对要去报警!”
我回头看了黎兰一眼,冷笑道:“放心。她不敢。她见了警察,自己都要躲。”
江和尚一愣:“怎么?”
我不耐烦:“少废话!当时咋回事!”
江和尚嘿嘿一笑:“说实话,要叫我运一具尸体从那头运到重庆,嘿嘿,给老子三个胆子老子都不敢,陈老板,嘿嘿,胆子确实够大。”
顿了顿,他道:“当时你不是在甲底乡养伤吗,我跟他又去了一趟神木岭,之前我们就去了一趟,就是把你救出来那次。”
我点点头,忽然想起一事:“对了,他怎么知道进去的路?”
“他说是那个叫表哥的人留下的,画在一张纸条上,是他无意找到的。”江和尚像想起什么:“对了,刚才听你提到表哥,他叫什么,徐万忠?”
我点点头,不想岔开:“那,你们后来去了又怎么样?”
“去了后我就陪他到处找,两座雪山,还有神木岭,挨着挨着走,整整五天。”
我想起一事:“那个洞,你们进去了?”
“就神木岭里头那个大洞?”江和尚摇头:“没进去。我们发现了那个口子,就你们从上头掉下来那个口子,但上不去,太高了,我们当时估计应该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去,找了半天,没发现。”
“那桑花呢?”
“桑花是我们准备出去时候发现的。”江和尚道:“当时是晚上,我们就看见一个人背了另一个人,就在那块沼泽地那儿,慢慢走,我们当时很震惊,说怎么突然会有人,感觉跟鬼一样,就跟上去,结果发现是桑花,背的人居然是一具尸体,就是阿迷婆婆。”
我暗暗心惊:“她一个人?”
“是。”江和尚道:“当时我们就问她咋回事,她看见我们,也很震惊,后来她说,说这次送棺死了好几个人,童古寨的人不干,想叫她带路,来搬尸体,她坚决不同意,因为她师傅死前交代过,来神木岭的路线,绝对不能透露给外人,这是个死规定,所以当时她就找了个借口溜了,偷偷来神木岭,把她师傅的尸体背出来,准备就在附近就地埋。”
我点点头:应该是这样。
但这时候,突然隐隐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似乎发现了一件不对劲的事情,却说不清是什么。
“那后来呢?”我随口问。
“后来,我们就一起把阿迷婆婆埋了,就在第二座雪山底下,一个荡荡(注:山旮旯)里头,埋了后桑花就走了,我们也跟她一起出山,在外头,分了手,她说她不能回童古寨了,至于去哪儿,她没说,后来就走了,我本来也想早点回去,回甲底乡,结果等桑花一离开,陈舜年就说,走,回去!我就问他回哪儿去,他说,回去把尸体挖出来!”
我听得心惊肉跳:“他没说原因?”
“你听我慢慢说。”江和尚顿了顿:“当时我也吓一跳,但还是跟他进山了,到了坟头那儿,三刨两刨,把尸体挖出来,我当时就叫他说清楚,当时尸体上裹了一块布,他直接就把布扯了,把尸体的上半身露出来,我才看见了那个东西,居然——”
我突然一阵深寒,想也没想就道:“是不是一个石盘?”
江和尚吓一跳,一个急刹。
车子剧烈一抖,黎兰惊叫一声,江和尚却不管,回头瞪我:“你咋知道?”
我做个手势,叫他靠边,江和尚回头看了一眼,发动车,开到路边。
“你咋知道?”他又瞪眼问。
我摆摆手:“这个事以后再说!”
我只感觉喘不过气,想了半天,双手张开,在胸膛位置比出一个“圆形”:“这么大!有没有?”
江和尚缓缓点头:“差不多。”
“在肉外头还是里头?”
江和尚瞟了黎兰一眼:“在里头。缝进去的。”
“缝进去!”我顿时气紧:“外面看得出来?”
江和尚慢慢点头,双眼露出恐惧:“看得出来。整整一圈,全部缝的那种线,就是那种手术专用线,就感觉——”
“感觉什么?”
“嘿嘿。”江和尚怪笑了一下:“就感觉先用一把刀,在她胸口划了一个大圈,然后把那层圆形的皮提起来,把那个东西放进去,最后重新把皮缝上去,就是那个感觉。”
后面,黎兰忽然发抖问:“你们——你们在说什么?”
我只听得一身皮肤疼,似乎有一把无形的“刀刃”正在身上游走,赶紧缩了缩身体,想起一事,赶紧问:“陈舜年怎么知道她那儿缝了一个石盘?”
“这个就不清楚。”江和尚道:“他没说。”
我点点头:“后来呢?你们怎么一路送到重庆来?”
“是他联系的石老三,石老三叫他来找吴兴禄。”
我一愣:“石老三?谁?”
“就阿香的三叔。”
我一下想起来:“那个医生?穿灰色西服的那个?”
“是。”江和尚道:“他跟吴兴禄是师兄弟。”
我一愣:“师兄弟?”
“嗯。”江和尚道:“吴兴禄以前当知青时候,就在甲底乡插的队,他们的师傅是同一个人,是甲底乡一个赤脚医生,傈僳族人,很有名,不过前几年死了。”
我点点头,有一种恍然的感觉,看来徐万忠跟吴兴禄之间,似乎也是通过这层关系认识的。
“你们怎么送过来的?”我问。
“嚇,就不说了吧。”江和尚嘿嘿一笑:“反正,中间有两次差点穿帮,运气好,不然老子多半又进去了,嘿嘿。”
我点点头:“那,那东西现在在哪儿?”
江和尚朝窗玻璃前方一指:“成都。”
“多久取出来的?”
“下午。”江和尚道:“在吴兴禄一个朋友那里。”
说到这里,江和尚摇摇头,一脸恐惧:“你不晓得当时好吓人,在一具死了十多天的尸体身上动刀,啧啧......”
我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一个画面:一具光溜溜的尸体,散发恶臭,一个人拿着手术刀,轻轻划开她胸口的皮......
我顿时一身鸡皮,缩了缩,才问:“那东西,具体什么样子?”
江和尚不语,发动车子,开了一截才道:“等会儿到了你自己看。”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对了,怎么把它拿到成都去?”
“你终于问这个问题了。”江和尚嘿嘿一笑:“到了成都,等他给你说。”
车子在黑暗中穿行,过了一座桥,像是嘉陵江,眼看着重庆市区被慢慢抛在后面。
我闭上眼睛,开始盘算。
事情忽然起了重大变化,黑衣毕扒的胸口,竟然也出现了那个诡异“石盘”!
而杨学礼,根据那盘录影带,他的胸口明显也有一个“盘状”的物体,而在录像里头,他就是利用那个东西,活生生,让乐山大佛发生了“闭眼”的状况!
佛闭眼!
羊鬼沟沟!
对了,徐万忠说过一句话,说,“杨学礼多半知道开启羊鬼沟沟的方法”!
我忽然一阵燥热:
我靠!
羊鬼沟沟,莫非,是黑衣毕扒开启的?
我猛一下睁开眼,望着窗外黑暗。
对!应该就是这样!
杨学礼利用身上那个“盘”,让乐山大佛“闭眼”!
而黑衣毕扒,也用那个“石盘”,开启了“羊嘴”!
他二人一定掌握了某个邪恶的办法!或者说,某种邪恶的“术”!
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乐山大佛,跟羊鬼沟沟,是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为何都跟那个“石盘”产生了关联?
我点点头:看来,“佛闭眼”这件事,远远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乐山大佛背后,一定还隐藏了另外一个神秘物体。
会是什么?
莫非......跟那个“佛镇”有关?
我一时有些懵,看来,得马上找到陈舜年,他一定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他那里一定有答案。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还有多久到?”
江和尚一愣,嘿嘿一笑:“才出重庆。你急个屁啊!嘿嘿。”
我点点头,不语。
这时他像想起什么,右手在身上一摸,摸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我狐疑接过:“什么?”
“吴兴禄走之前给我的。”江和尚道:“差点忘了。说是给你看。”
我一看,是一个塑料袋子,里头装了一坨纸。
“啥东西?”我问。
“应该是好东西。”江和尚神秘一笑:“说是你身上那个病,那里头说不定找得到办法。”
我一凛,赶紧把那坨纸展开,明显是刚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密密麻麻全是文字。
我摸出火机,火光摇曳下粗粗一看,里面出现了什么“皮薄为痈”,什么“取黑铅,黄芪,硫磺”,什么“中表六散”,明显是一本医学书籍。
我狐疑看了看,翻到反面,一下注意到中间有三段文字下面勾了横线,一开始赫然就是三个字——“瞿婆者......”
瞿婆!
我浑身一震,赶紧细看。
那段文字如下:
“瞿婆者,名讳宗寅,滇西蒲甘之地董董族人也,世袭比爬者,广明九年(995年)离家而亡,明治二年(1009年)复归,彼时身染恶疾,如鬼皮覆体,泽如赤蜡,刀刺莫能脱,膏剂莫能去也,是为“覆疰”之疾,半载后暴毙,面如陌鬼,皆传:盖其盗走《食血经》受其血咒是也。”
而在“覆疰”两个字旁边,画了一根黑线,连到右边空白处,用钢笔写了三个字——“鸡婆皮”。
覆疰!
莫非,我身上这个东西,叫“覆疰”?
我再次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一遍,暗暗心惊:关于“覆疰”的描述,竟然跟我的情况几乎一样,“鬼皮覆体,泽如赤蜡”,是不是说那东西像一层“皮”一样覆盖住全身,然后光泽看起来,像红颜色的蜡烛!
我死死盯住最后一段——“半载后暴毙,面如陌鬼,皆传盖其盗走《食血经》受其血咒是也。”
《食血经》!
好恐怖的名字!是什么东西?
“半载后暴毙”!
莫非,我只有半年的生命可以活!
乱编的!肯定是乱编的!
我一阵莫名的惊惶,一把,揉成一团。
旁边,江和尚狐疑看我:“怎么样?”
“哪儿来的?”我问。
“一本书。撕下来的。”
“他当时咋个说?”
“吴兴禄?”江和尚道:“他就说拿给你看,说里头说不定有办法,咋样,写的啥东西?”
“《食血经》。”我道:“你听说过没有?”
“什么经?”江和尚没听清。
我叹口气,只觉得浑身无力,不想再说。
江和尚还想问,这时手机响,他拿起来,说了几句,挂断。
“妈X!”他骂了一句。
“怎么?”我问。
“陈舜年。”他道:“叫我们先到成都去等他,他有事走了。”
我一愣:“走哪儿去了?”
“他没说。”江和尚一脸狐疑:“神神秘秘的,多半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江和尚摇摇头:“他走的很急,肯定是大问题。妈的,只有到了成都再说。”
早上9点过时候到了成都,左拐右拐,在一个市场门口停下,我看见外面挂了一个长牌子,写着“文殊院古钱币市场”几个大字。
江和尚跳下车,叫我们在外头等,他去问。
说完他匆匆走进大门,足足半小时才回来,一脸纳闷,说这件事有点奇怪。
原来陈舜年昨天下午从重庆过来后,直接就来的这里,本来是来找里头一个叫“大师兄”的人,之后大师兄请他吃了晚饭,帮他在附近找了一家宾馆,本来说好今天上午再见一次面,但是刚才8点过时候,陈舜年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有事情,先走一步,办完事再回来,当时大师兄就觉得奇怪,什么事情走这么急。
我点点头:“他4点钟时候给你打电话,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成都了。”
江和尚一脸狐疑:“这件事不对劲。我们是3点时候跟他通了话,当时他还叫我们来成都碰头,那时候还没事,也就是说就在跟我们通了话之后,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想到一个问题:“他来成都几个人?”
“就他一个。”江和尚道。
“他找大师兄办什么事?”
江和尚犹豫一下:“就是那个东西。”
我一凛:“那块石盘?”
“是。”江和尚道:“上面有一排符号,他请大师兄看。”
符号!
我一凛:“什么符号?”
“他最开始说是西夏文字。”江和尚道:“后来又说不是。”
西夏文字!
我一个激灵:“西夏鬼字?”
“西夏鬼字......”江和尚一皱眉:“我也搞逑不懂,反正那些东西就刻在石盘表面,一圈一圈。”
我暗暗心惊:青海石碟!
对,冯华好像说过,那些石碟表面就是一圈一圈的皱褶,然后里头全部刻的是那种西夏鬼字!
我的天,果然是同一种东西!
这太恐怖了,黑衣毕扒的身体里头,怎么会出现“青海石碟”?
按照江和尚说的,是有人把它活生生缝进去的,是谁?是黑衣毕扒本人,还是某个更神秘的人?
对了,还有杨学礼!
他胸口明显也缝了一个石盘,他那个又是谁缝进去的?
“有多重?”我随口问。
“可能。”江和尚皱眉道:“两斤不到。”
“什么材质?石头还是什么?”
“嘿嘿。”江和尚怪笑了一下:“就这个吓人。”
我一愣:“怎么?”
“我当时摸了一下。”江和尚道:“摸起来像石头,但是感觉里头,吸了血。”
“吸血?什么意思?”
“嘿嘿。”江和尚瞟了黎兰一眼:“只是我感觉。那个东西摸起来明显是石头,但是颜色是那种深红色,我还第一次看见这种颜色的石头,最吓人的是里头还有很多黑颜色的小管子。”
“小管子?”我没听懂。
“对。”江和尚指了指自己的手背:“就跟血管一样,东一段西一段,很短,所以当时我第一感觉就觉得它就像吸了人血一样。”
我点点头:“它缝在身上这么久,肯定有血浸进去。”
“也是。”江和尚嘿嘿一笑。
我一时有些彷徨,看了看市场大门:“那现在你打算咋办,就在成都等?”
江和尚眨巴几下眼睛,看了看黎兰:“我倒无所谓。主要是你们二位——”
我跟黎兰对视一眼,都有点不知所措。
我想起一事,赶紧问:“司徒骏当时在哪个考古队?”
黎兰想了想:“文物局第三考古所。”
“在哪儿?”
“西宁。”
我点点头,拿定主意:“那好。先去西宁。先去查一下司徒骏的底。”
听说我们要去青海,江和尚很吃惊,不停问原因。
我朝黎兰一指:“她去找他情夫。我去找我情妇。”
江和尚明显没听懂,呵呵一笑:“你情妇?谁?老子认不认识?”
“冯华。”黎兰抢先道。
江和尚脸色一变:“冯华?她不是死在神木——”
我咬咬牙,不吭声。
黎兰一脸好奇:“她死了?真的假的?”
江和尚指了指我:“你问他。”
黎兰好奇看我,欲言又止。
“没见到尸体,都不算死。”我冷冷对江和尚道:“我们这次先去西宁,然后还要去一趟格尔木,看你了,你要去就一起开车去,不去,我们坐火车去。”
江和尚一脸狐疑,眼睛眨巴几下,摸出手机:“我先给陈老板汇报一下。”
说完走到一边,一会儿走回来:“妈X,关机了!”
“那你快决定!”我不耐烦。
江和尚咧嘴一笑:“那你们去买票。我,嘿嘿,还是在这儿等算了。”
跟江和尚告辞,我跟黎兰叫了个车,直接去“火车北站”,买了两张票,K1058,晚上10点钟上车,要坐17个小时,第二天下午2点过到西宁。
也没地方去,心情都不好,在附近“府河”边看见有人喝茶,就要了两杯盖碗茶,坐着,也懒得说话,都盯着河水,各自想心事。
下午时候黎兰找我要了100块钱,在附近一个服装摊埋了一套衣裤,在一个公共厕所把那件白大褂换了,又买了一些洗漱用具,还买了个小包,100块钱用的精光。
好容易等到晚上,吃了东西,进了“北站”候车厅,等了一阵,上了火车。
找到铺位,她中铺,我下铺,她去厕所洗漱回来,爬上去,铺盖一蒙,直接睡觉。
我坐在铺位上,发了一阵呆,烟瘾来了,于是走到中间连接处,蹲下,把口罩下半截撩开,摸出烟来抽。
这时一个列车员推了一个小车子从我身边走过,边走边懒洋洋叫:“啤酒,花生,方便面......”我只感觉肚子一阵饿,赶紧叫住,买了一包“老灶”花生,扯开就吃。
列车员推着小车,走进隔壁车厢,忽听有个人招呼他一声:“喂,来瓶啤酒。”
我一个激灵:这人是谁!
“啤酒五块。”列车员道。
“这么贵?”那人朗声笑道:“四块八行不行,哈哈!”
我“忽”一下站起来:
陈舜年!
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几步跑进隔壁车厢,一看,只见过去第二格中铺,探出一个脑袋,大背头,一脸坑坑洼洼,一对鼓眼睛很亮堂,正笑吟吟一手拿啤酒,一手给钱。
我靠!不是陈舜年是谁!
想着我几步走过去,一把抓住啤酒瓶:“再买一瓶!”
陈舜年猝不及防,愣住。
周围几个乘客都狐疑看我一眼。
陈舜年上下打量我,笑道:“兄弟认错人了吧!”
我看了周围人一眼,心想要是把口罩拉下来,肯定要引起恐慌。
于是嘿嘿一笑:“认错个屁!你叫老子来成都找你,结果你屁股一拍,上火车溜了!”
陈舜年一惊,双眼精光四射,一下反应过来:“你——你关小峰?”
我点点头:“再买一瓶。”
“相逢不如偶遇。没问题,哈哈哈!”陈舜年满脸发光,一下从床上跳下来,摸出钱,又买了一瓶,还买了一包牛肉干,笑道:“来来来,正好,对饮成双人。”
我心头一阵翻滚,无数东西冒到嘴巴边,但看了看周围,好几个人都把我们望着,这里明显不是说话的地方。
于是我指了指车厢连接处,掉头就走。
陈舜年点点头,跟上来,我蹲下来,张嘴,狠狠把啤酒盖咬开,“咕嘟”先灌了一大口。
“抢喝?不够意思。”陈舜年也蹲下,一口也咬开盖子,啤酒泡一下冒出来,他也不管,“砰”跟我碰了一下,也是一大口。
我看看左右无人,一把扯下口罩,只感觉呼吸爽快了许多,叼烟,狠狠抽了一口。
陈舜年死死盯着我的脸,点点头:“怎么回事?”
“覆疰。”我道:“听说过没有?”
“覆疰!”陈舜年眉头一皱。
我又狠狠抽了一口:“算了,这事儿等会儿再说,你怎么在火车上,也去西宁?”
“是。”陈舜年点头:“但不是目的地。”
我一愣:“还要去哪儿?”
“有个地方不知你听说否。”陈舜年缓缓道:“大柴旦镇。”
大柴旦镇!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名字,赶紧问:“在哪里?”
“德令哈过去。快到甘肃了。”
“去那儿干什么?”
“这个待会儿再说。”陈舜年凑过来,双目如电:“你怎么也在车上?去哪儿?”
“西宁。”
“西宁?”陈舜年一皱眉:“不是叫你在成都等吗,你去西宁干什么?”
“一句话说不清。”我想起一事:“对了,你去大柴旦镇怎么没对江和尚说?”
“他?”陈舜年轻蔑一笑:“他就算了。贪得无厌。”
我一愣:“怎么说?”
陈舜年摇摇头:“算了,不说他,对了——”
他盯着我:“你说你有我父亲的消息?”
我点点头:“是表哥告诉我的。”
“表哥?”陈舜年一下想起:“那个姓徐的?”
“对。徐万忠。”
陈舜年一凛:“你见到他了?”
“在乐山。”我道:“一个叫锣场村的地方。”
“锣场村?”
“对。他临走时候给我说了一句话,说你父亲多半埋在那座坟包里头。”
“坟包?什么坟包?”
“锣场村那儿有一座坟包,是个无主坟,里头有一具棺材,是黑颜色的,现在里头是一副猪骨头,但是徐万忠给我说,以前里头很有可能埋的是你父亲。”
陈舜年有些懵:“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又埋了一副猪骨头?”
我喝了一口酒:“总之事情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给我说的。”
“乐山......”陈舜年眉头紧锁,似乎在想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过会儿他回过神,问:“那表哥呢,他现在在哪儿?”
我指了指地面:“下去了。”
“下去?下哪儿去?”
我看看左右无人,凑过去:“我实话给你说,我才从锣场村逃出来,我身上这个怪东西就是在那儿底下感染上的,徐万忠,他更恐怖,他直接下去了。”
“下哪儿?”
“我们在那儿挖了一个地洞,后来发生很多事情,还死了好几个人,徐万忠当时也在,他给我说,底下埋了一个羊怪。”
“羊怪?”
“对。是个羊头人身的东西,他后来就钻下去了,说是去查一件事,我当时已经要死要死,没下去,就逃上去了,那个坟包的事情就是我们分手时候他说的,他说一定要找到你,给你说这件事。”
黑暗中陈舜年死死盯着我,似乎不完全相信我的说的话,过半天才问:“那,那座坟包现在还在不在?”
我摇摇头:“我走的时候还在。但现在不好说。”
陈舜年一愣:“怎么说?”
“我们逃走时候,来了一支部队,把整个锣场村封锁了。”
“部队!”陈舜年很惊诧。
“对。我们是装作120才逃出去的,当时已经塌陷成一个大坑,他们来了两个直升机,还吊了好几个人下去查看,那座坟包就在附近,所以我估计现在已经被他们发现了。”
陈舜年点点头,把啤酒瓶对准嘴巴,却不喝,呆呆想事情。
我心头却冒出无数疑问,赶紧问:“我问你,黑衣毕扒怎么回事,江和尚说是你们两个直接把尸体挖出来然后送到重庆,到底咋回事?”
“她身上缝了一个东西。”
我点点头:“石盘。对了,在哪里,在不在你身上?”
“我放大师兄那儿了。”
“你怎么知道她身上有那个东西?”
陈舜年看我一眼,不语,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我一看,是个棕色外壳的小笔记本,厚厚的,里面的纸页全部泛黄,明显是个很有年份的东西。
“我父亲给我的。”他翻到一页:“你看这幅画。”
我凑过去一看,猛一个激灵:
“神穴图!”
“什么?”陈舜年一愣。
我不语,定睛一看,不由头皮发麻:这幅图跟《神穴图》几乎一模一样!也是中间躺了一个巨大的“人形”怪物,有手有脚,然后周围坐了7个“小人”,也都是古装,伸出一只手,手里头似乎拿了一个“竹棍”,指着中间那个“巨怪”。
“我看过一幅画!”我只感觉呼吸不畅:“跟你这幅一模一样!就只有一点,那幅画里头这个人身上全是穴位,你这里头——”
我猛的意识到一件事,一下定住,指着“人怪”胸口那坨黑色东西:“你是说,这个东西——”
“对。”陈舜年道:“是个石盘!我父亲写的是‘石碟’!”
“石碟!”我一凛:“在哪儿?”
陈舜年指了指:“你看这儿。”
我定睛一看,图案周围东一团西一团,画了几个小方框,里头写了很多字,明显是对图案的注释,其中有一个方框,里头就两个字——“石碟??”,后头打了两个问号。
石碟!
青海石碟!
我心中大震,死死盯着图案,半晌抬起头:“你父亲是谁?”
陈舜年合上本子。
“陈元。”他道。
陈元!
我脑子里飞速搜索了一下,确定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他干啥的?怎么有这幅画?”
陈舜年像想起什么,又打开,翻了几下翻到一页:“你看。”
我定睛一看,中间画了三个“人形”,全部呈“下蹲”姿势,其中一个长了一个“纺锤形”脑袋,上面五官呈颠倒状态,还有一个只有脑袋,没有五官,还有一个直接就没有脑袋。
“倒头祭司!”我脱口而出。
陈舜年神秘一笑,合上。
“你父亲是考古的?”
“本来只能算一个古董商。”陈舜年道:“在那次去柴达木之前。”
柴达木!
我愣住。
陈舜年“咕嘟”灌了一大口啤酒,抹抹嘴巴,摸出一包烟,一人一杆。
他深深抽了一口,一对鼓眼睛望着我身后的车窗外面,看眼神,明显陷入回忆。
火车忽然“忽——”一声,周围一下寒冷,进入了一个隧道。
“应该是1932年。”陈舜年开口:“我父亲受邀请,加入了一个考古队,领队的是个德国人,叫冯.莫伦堡。”
“冯.莫伦堡......”
我喃喃重复,心头冒出一个异常感觉。
“对。”陈舜年道:“他有个中国名字,叫冯穆人。”
冯穆人!
我一震:那封信!
陈舜年直直盯着车窗外,继续道:“此人是1931年底到的北平,当时我父母才结婚,我母亲姓贾,我外公叫贾五爷,在北平琉璃场开了一家古玩店,叫‘凤麟阁’。”
我一愣:“凤麟阁?”
“对。凤麟阁。”陈舜年咧嘴一笑:“就是我现在的门面名字。”
“你们是从北京迁过去的?”
“对。1949年。”陈舜年继续道:“当时是这样,那个冯穆人到了北平后,通过一个熟人找到我父亲,说他们马上要组一个队伍,去青海,去寻找一个古代王国遗址,至于为何找我父亲,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清朝内务府一名采办,跟古董经常打交道,特别是西域那一带的文物珍宝,我父亲很熟悉,那时候经常有青海还有内蒙新疆一带的王公贵族,给朝廷上贡,或者地皮被占了,跑到北平来,把家里的东西典当,我父亲当时在内务府就专门对这些东西进行鉴定。”
我点点头:“他就去了?”
“对。”陈舜年道:“按照我母亲的说法,他们是1932年1月上旬离开北平的,最开始一共5个人,三个老外,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男的就是我父亲——”
一男一女!
我忽然一股异样感觉:“还有个女的?”
“对。”陈舜年像想起什么:“对了,给你看个东西。”
说完他又打开笔记本,一翻,翻到某页,我发现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陈舜年取出照片,递给我:“这就是他们在柴达木拍的。”
我接过,一看,是一张黑白照片,呈焦黄色,明显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上面照出六个人,前面三个坐着,后面三个站着,是一张合影。
“这个就是冯穆人。”陈舜年一指中间那个人。
我一凛,一看,那人50岁模样,戴帽子,高鼻深目,络腮胡。
而他左右,是两个外国人,我心中一凛:那封信里头提到一个土耳其人,叫“伊尔寒”,肯定是其中一人。
“这是我父亲。”
陈舜年指着最右边站着的那人。
我一看,那人也50岁左右,又高又瘦,穿一件皱巴巴的西服,神情木然。
这时我注意到后排,中间,站了一个人,穿一套灰扑扑的长袍,十八九岁模样,脸很白,眉目秀丽,一看就是个女人。
我一指:“她就是那个女的?”
“是。”陈舜年道。
我不由又仔细看了这女的一眼,只见她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冯华!
我忽然一股恶寒:天!这女的怎么长得像冯华!
“她啥名字?”我下意识问。
“姓夏。”陈舜年道:“叫夏文衡。”
夏文衡!
我点点头,不动声色,心头却飞速旋转:那封信,就是冯穆人写给这个“文衡”的,叫她一起做一件事,伪造“青海石碟”事件,当时我跟冯华就判断,此人既然是北大的老师,那肯定跟那个姓“夏”的人有关系,按照林文盛所说,1955年时候,就是他同寝室一个老师,姓夏,叫他把一个石碟找出来,藏好,而之后对青海鬼字的调查,也就是从那年开始。
所以当时我跟冯华就判断,这个“文衡”跟那位姓“夏”的老师,一定存在某种关系,要么是夫妻,要么是兄妹,不然那姓“夏”的不可能得到那个石碟,现在看来,这个“文衡”居然叫夏文衡,那不用说了,她二人一定是兄妹关系!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恐怖的事情,这个“夏文衡”,怎么长得像冯华?
我不由死死盯着那人看,旁边陈舜年奇道:“怎么?你好像认识这个女的?”
我不吭声,盯着“夏文衡”,似乎,又跟冯华不像了。
我抬起头:“感觉她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是么?”陈舜年笑道:“那就太有缘分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一直对这个夏文衡心存怀疑。”
我一愣:“怎么?”
陈舜年指了指笔记本:“里头有几段叙述,是我父亲对夏文衡的记录,我发现他跟我一样,也对此人非常警惕,此人的年龄,身份,还有参加考古队的目的,按照我父亲的文字,一直是一个谜。”
我点点头,心中狐疑:按照那封信的内容,这个“夏文衡”应该在北大任职,这个身份似乎不需要保密,莫非,这里头还有其他隐情?
一时搞不懂,赶紧问:“那后来呢,他们去了柴达木?”
“去了。”陈舜年道:“这本笔记就是那次的整个资料。”
我想到一个问题:“你说的那个古国,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铁羊国?”
“铁羊国......”陈舜年点点头:“我纠正一下,其实应该叫铁羊坟。”
铁羊坟!
“是一座坟?”我问。
“是当地一种古称。”陈舜年道:“有一个古国,叫白兰国,听说过吗?”
“白兰国......”我摇摇头:“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好!”陈舜年咧嘴一笑:“厉害!居然一下就问到点子上。”
我没听懂:“什么意思?”
“是这样。”陈舜年解释:“白兰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大致方位就在柴达木一带,时间大概在公元2世纪左右,这都是史书上的记载,之后,被一个叫‘吐谷浑’的国家给灭掉了,也不叫灭,就是被吞并了,照理说既然国家都灭亡了,应该没人去关心它,但是据我的了解,此后有很多搞考古的人都一直在研究这个国家,有外国,也有内地,一直在试图判断它的具体方位,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其实他们不是想找到白兰国本身,因为它本身的位置大致已经确定下来了,目前的说法有三处,但其实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么多人寻找的,其实是它的一个古都。”
“古都?”
“对。就是它最早的一座都城。”陈舜年道:“就是铁羊坟。”
我点点头:“你的意思,92年那次,就是去寻找铁羊坟的位置?”
“对。”
“铁羊坟......”我念了一遍:“铁羊?羊?”
陈舜年没吭声。
“羊......”
我只感觉从右脚脚心位置,渐渐渗透出一层酥麻,沿着右腿朝身体发散,赶紧猛的站起来,动了动,那股“酥麻”忽然又消失了。
陈舜年狐疑打量我:“怎么?”
我重新蹲下:“那个都城为什么叫铁羊坟?有一座坟,还是怎么?”
“不知道。”陈舜年顿了顿,道:“但是,史书上对这个都城有一种记载,应该是他们去寻找的原因。”
“什么记载?”
“有好几本古籍都记载了同一件事。”陈舜年道:“说西夏国的龙脉,在那里。”
西夏龙脉!
我一凛:“在铁羊坟?”
“对。”
“他们那次去,是去找西夏龙脉?”
陈舜年没回答,露出一个复杂表情,过半晌才说:“其实龙脉一说,我觉得是一个很虚的东西,根据这本笔记,他们那次去柴达木,‘龙脉’一说其实只能算其中一项考虑,他们五个人包括我父亲,其实都是很实际的人,对那种虚的东西,我看了笔记,其实并不相信,我感觉他们应该是去寻找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
“不好说。”
“不好说?”我一愣,指了指笔记本:“里头有没有记录?”
“有。在后半部分。”陈舜年忽然古怪笑了笑:“但上面那些......我不知道该不该称之为记录。”
说完这句,陈舜年拿起酒瓶“咕嘟”喝了一大口,放下,打开笔记本。
我赶紧凑过去。
这时一个人从右边车厢走出来,靠在铁门边,用打火机点烟,离我们也就半米不到,陈舜年瞟了他一眼,放下笔记本。
那人也瞟了我一眼,移开视线。
此人60多岁,穿一件灰色夹克,黑裤子,身材矮小,獐头鼠目。
但也就不到半秒,他忽然脸色一变,两只“鼠眼”一下子,重新盯在我脸上,露出一个惊恐神色。
我知道他看见了我脸上那些“鬼东西”,也懒得拉上口罩,拿起酒瓶“咕嘟”灌了几口,同时狠狠看他。
那人似乎害怕了,移开视线,缓缓走到对面车窗处,望着外面,像是在欣赏夜景,但我却有个奇怪感觉,他明显在用眼角余光堤防着我。
一时都没说话,陈舜年看了看手表。
“11点半了。”他压低声音问:“你在哪个车厢?”
我朝右边努努嘴。
“什么铺?”
“下铺。”我道。
“好。到你那儿去。”他道:“这儿太显眼。过去慢慢说。”
我心想也是,现在整个车厢都熄灯了,夜深人静,我们两个一直在这儿说话,要是引起乘警的注意就麻烦了。
于是提起酒瓶,往车厢里头走,走了一段,总觉得不对劲,回头一看,那“鼠眼”老头正定定看着我,四目对视,他似乎有点害怕,一下把脑袋扭过去。
我暗暗起疑:我脸上那些东西的确看起来很恐怖,这几天我都习惯外人的眼光了,但这个老头似乎有点异常,他眼神里除了惊讶,明显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一时不解其意,也懒得多想,回到铺位上,只闻到一股浓烈的臭袜子味道,中铺上,黎兰鼾声阵阵,我不由好笑:这女人看着秀秀气气,怎么睡觉鼾声这么大,真要是跟她睡觉那就有的受。
“是不是那个医生?”陈舜年忽然问。
我点点头:“江和尚给你说了?”
“说了。”陈舜年狐疑看着黎兰:“她什么情况?你怎么带她到成都来?”
“她在医院给我治病。”我压低声音:“结果,当场死了一个人。”
陈舜年一愣:“怎么回事?”
我犹豫一下,心想这一两句哪里说得清,赶紧道:“简单给你说一下,她当时跟另外一个医生给我治病,结果,出了个状况,她把那个医生电死了。”
“电死?失手?”
我摇摇头:“算不上失手。那个医生——啧啧,当时被附体了。”
“附体!”陈舜年明显不太相信。
我赶紧坐下来,陈舜年也坐下,我压低声音:“是这样,当时那个医生出了一个很恐怖的状况,她也是为了自救,就用电线把他电死了,后来那个医生还从八楼上跳下来,我跟她当时也是慌不择路,就跑了,后来听说警察在找她,我们这次去青海,准备先去西宁,第二站就要去格尔木,那儿有个人,知道整个事情的内情,黎兰准备找到他,看他有没有办法帮她洗脱罪名。”
“格尔木!”陈舜年狐疑问:“那个人是谁?”
“叫宋传明。是昆明市局一个法医。”
“昆明市局?”陈舜年问:“怎么跑到格尔木去了?”
“谭国富那个案子就是他在验尸。”我想起一事:“对了,说是谭国富好像没死。”
“没死?”陈舜年一凛:“你怎么知道?”
“就是这个宋传明在负责这件事,是上个月的事,他后来就被秘密调到格尔木去了。”我顿了顿:“谭国富据我们估计,也被送到了格尔木!”
“什么?”陈舜年脸色一变:“为什么?”
我看了看周围,车厢内黑沉沉,都在熟睡。
我凑过去,压低声音:“有个799局,你听说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