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顶贴。
《成精记》:界门纲目科属种,怪力乱神人鬼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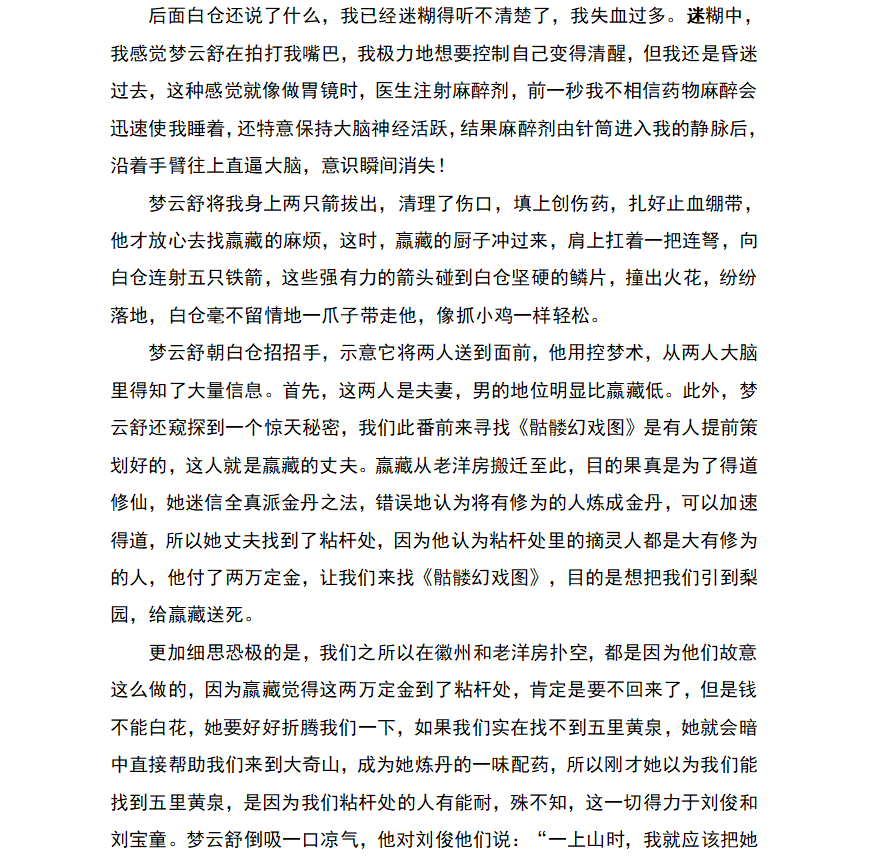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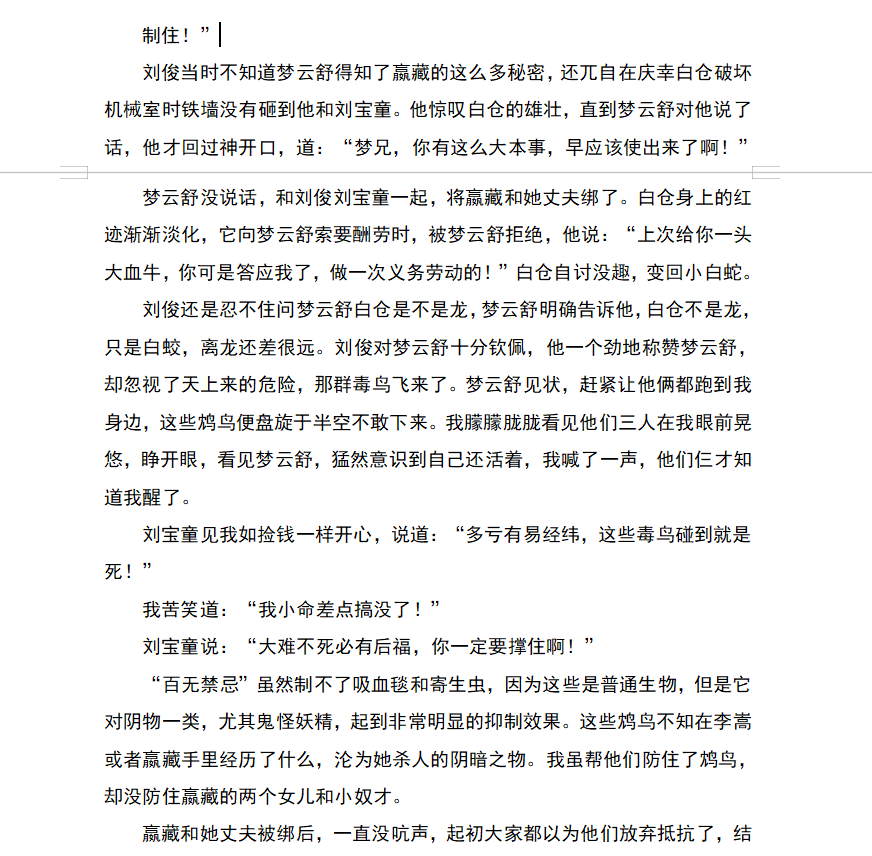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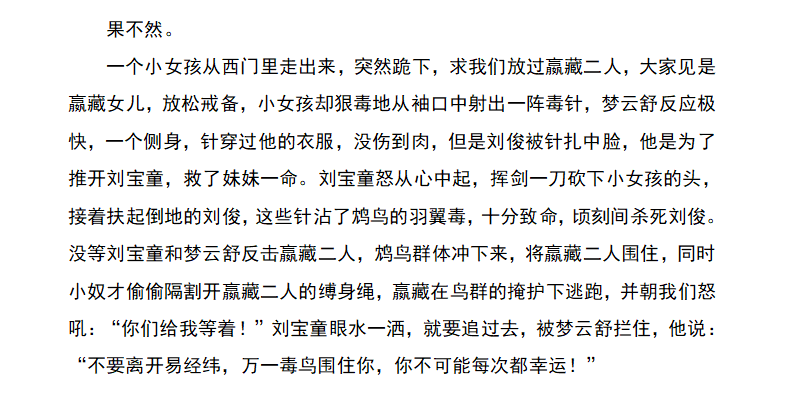
刘宝童立马回到刘俊身边,撕心裂肺地哭喊,这种无奈,就像去年小姨给小姨夫哭丧一样,正如《教父3》第二代教父迈克尔·柯里昂抱着自己死去的女儿那般悲痛。梦云舒极力地控制自己在这场混乱中的情绪,他心里明白《骷髅幻戏图》这个任务失败了,买家就是卖家,还牺牲了两个人,我们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
刘宝童哭了短短一会,便擦干泪水站起来,说:“我哥不能白白牺牲!”
梦云舒看着她,问道:“你要怎么做?”
刘宝童说:“杀嬴藏,拿李嵩画!”
梦云舒这时才把他从嬴藏和其丈夫的脑中获取的信息告之刘宝童,另外嬴藏手中一共有八幅李嵩画,不是七幅,梨园后门的悬崖下只是其中《百鬼闹》这一幅画的藏身处,其他七幅藏在梨园其他地方,都设有机关防盗。刘宝童和我听完,都十分吃惊。梦云舒说他也没想到嬴藏阴谋筹划得如此高深,一开始我们来到梨园,他本想着见到了《骷髅幻戏图》,再根据嬴藏的意思来采取对应措施,这样稳妥一点。他向刘宝童致歉,说:“这事怪我,在嬴藏说鸩鸟是她养的时候,我就应该警惕她,没想到她会下如此毒手!”
我说:“最毒妇人心!”但是说完,我觉得话讲得不对,刘宝童也是女人。
梦云舒建议我们最好先离开,一是安置下刘俊的遗体,二是我还受了重伤,嬴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后面再来报仇也不晚。我同意梦云舒的建议,一是因为我的伤,二是穷寇莫追。刘宝童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捡起刘俊的长剑,收进剑盒(剑盒表面是笛盒,装笛子用,目的是为了躲避车站检查),扛起他哥。梦云舒则扶起我,架着我走。
我们谨慎地走出梨园,下了山,路过田明尸体时,刘宝童将田明也拖走,回到我们上午来的地方,废弃的李嵩故村遗址。我们身处浙杭,不能像湘西那边,尸体可以找赶尸匠送回老家,在这里,要火化才行。但是,火化尸体不是件简单的事,要到殡仪馆,要出示各类证明,刘宝童考虑了下,决定将刘俊送往殡仪馆火化,而田明,由于她没法证明她和田明的关系,殡仪馆要求通知田明亲属来杭州认领尸体才能火化。
田明有两个儿子,赶来后,刘宝童告诉他们,田明和刘俊在山里中了蛇毒,毒发身亡的。田明一个继承他衣钵的锁匠儿子相貌厚道,趴在田明遗体旁哭声连连,但是田明二儿子,在苏州某公家单位上班,比较机警,怀疑田明的死和我们有关,不肯火化,还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当场给不出结果,取了样,要回所里诊断。刘宝童还被警方带回派出所录了口供,和田明二儿子闹得不愉快。
这些事是刘宝童在第二天去医院看我时说的,我当时已经做完手术缝合好伤口在住院部吊水治疗。她的情绪非常低落,脸色憔悴不堪,她说她哥这是客死异乡,还没留个全尸入土为安,只能抱个骨灰盒回家。我替她感到难过。刘宝童和田明的老家离得不远,都在苏北。
在等了几天后,法医那边出了结果,说田明的确是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的,田明二儿子才放过刘宝童。我们虽然对法医鉴定的结果感到意外,但是也庆幸法医给了这个结果,悬着的心落了地,我们谁都不想被警方盯上,无端生出许多是非,尤其是刘宝童,她还亲手杀了一个女孩。
可是刘宝童在离开派出所后,被一个人拦住去路,这人身着长衫,留一撮羊胡子,年纪五十有长。他告诉刘宝童,法医鉴定的结果其实是他给的,但是他知道死的两人中的并不是蛇毒,而是早已失传的鸩毒。刘宝童吃惊地望着这人,默不作声,没搭腔地走开。这人紧跟其后,对她说:“我不是什么坏人,只是爱钻研这些毒物,如果你知道鸩鸟下落,还麻烦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刘宝童冷冰冰地说:“这鸟的毒,碰到就是死,我劝你最好没事别找事去!”
这人呵呵一笑,说道:“再毒的东西都有解药能解,一物克一物,你今天务必告诉我鸩鸟在什么地方,不然,你还得回这里,那两人可不是正常死亡。”
刘宝童明白这人来历不浅,只好向他透露了梨园所在位置,这人饶有兴趣道:“没想到大奇山里藏着这等好货,谢谢了,大妹子!”
刘宝童哭了短短一会,便擦干泪水站起来,说:“我哥不能白白牺牲!”
梦云舒看着她,问道:“你要怎么做?”
刘宝童说:“杀嬴藏,拿李嵩画!”
梦云舒这时才把他从嬴藏和其丈夫的脑中获取的信息告之刘宝童,另外嬴藏手中一共有八幅李嵩画,不是七幅,梨园后门的悬崖下只是其中《百鬼闹》这一幅画的藏身处,其他七幅藏在梨园其他地方,都设有机关防盗。刘宝童和我听完,都十分吃惊。梦云舒说他也没想到嬴藏阴谋筹划得如此高深,一开始我们来到梨园,他本想着见到了《骷髅幻戏图》,再根据嬴藏的意思来采取对应措施,这样稳妥一点。他向刘宝童致歉,说:“这事怪我,在嬴藏说鸩鸟是她养的时候,我就应该警惕她,没想到她会下如此毒手!”
我说:“最毒妇人心!”但是说完,我觉得话讲得不对,刘宝童也是女人。
梦云舒建议我们最好先离开,一是安置下刘俊的遗体,二是我还受了重伤,嬴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后面再来报仇也不晚。我同意梦云舒的建议,一是因为我的伤,二是穷寇莫追。刘宝童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捡起刘俊的长剑,收进剑盒(剑盒表面是笛盒,装笛子用,目的是为了躲避车站检查),扛起他哥。梦云舒则扶起我,架着我走。
我们谨慎地走出梨园,下了山,路过田明尸体时,刘宝童将田明也拖走,回到我们上午来的地方,废弃的李嵩故村遗址。我们身处浙杭,不能像湘西那边,尸体可以找赶尸匠送回老家,在这里,要火化才行。但是,火化尸体不是件简单的事,要到殡仪馆,要出示各类证明,刘宝童考虑了下,决定将刘俊送往殡仪馆火化,而田明,由于她没法证明她和田明的关系,殡仪馆要求通知田明亲属来杭州认领尸体才能火化。
田明有两个儿子,赶来后,刘宝童告诉他们,田明和刘俊在山里中了蛇毒,毒发身亡的。田明一个继承他衣钵的锁匠儿子相貌厚道,趴在田明遗体旁哭声连连,但是田明二儿子,在苏州某公家单位上班,比较机警,怀疑田明的死和我们有关,不肯火化,还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当场给不出结果,取了样,要回所里诊断。刘宝童还被警方带回派出所录了口供,和田明二儿子闹得不愉快。
这些事是刘宝童在第二天去医院看我时说的,我当时已经做完手术缝合好伤口在住院部吊水治疗。她的情绪非常低落,脸色憔悴不堪,她说她哥这是客死异乡,还没留个全尸入土为安,只能抱个骨灰盒回家。我替她感到难过。刘宝童和田明的老家离得不远,都在苏北。
在等了几天后,法医那边出了结果,说田明的确是被毒蛇咬伤中毒身亡的,田明二儿子才放过刘宝童。我们虽然对法医鉴定的结果感到意外,但是也庆幸法医给了这个结果,悬着的心落了地,我们谁都不想被警方盯上,无端生出许多是非,尤其是刘宝童,她还亲手杀了一个女孩。
可是刘宝童在离开派出所后,被一个人拦住去路,这人身着长衫,留一撮羊胡子,年纪五十有长。他告诉刘宝童,法医鉴定的结果其实是他给的,但是他知道死的两人中的并不是蛇毒,而是早已失传的鸩毒。刘宝童吃惊地望着这人,默不作声,没搭腔地走开。这人紧跟其后,对她说:“我不是什么坏人,只是爱钻研这些毒物,如果你知道鸩鸟下落,还麻烦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刘宝童冷冰冰地说:“这鸟的毒,碰到就是死,我劝你最好没事别找事去!”
这人呵呵一笑,说道:“再毒的东西都有解药能解,一物克一物,你今天务必告诉我鸩鸟在什么地方,不然,你还得回这里,那两人可不是正常死亡。”
刘宝童明白这人来历不浅,只好向他透露了梨园所在位置,这人饶有兴趣道:“没想到大奇山里藏着这等好货,谢谢了,大妹子!”
昨天被系统删除的部分今天已经补上,另外今天也已更新。
谢谢大家顶贴,谢谢古月的打赏。提前祝大家五一快乐,劳动光荣!
晚上还有事情,明天上午补今天的。谢谢大家支持。五一快乐
回到医院后,刘宝童向我们提了此事,并问我们还打不打算再上梨园,夺回李嵩画。梦云舒想了想,借着要回合肥交差的理由,说暂时不去梨园了。
刘宝童说:“那我回老家安置我哥了。”她沮丧的样子令人心疼。
梦云舒问她要了固话号码,同时也把合肥粘杆处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了她,梦云舒说:“你哥不会白白牺牲,等我们休整好,再定时间去梨园拿回李嵩画!”
刘宝童手伸向梦云舒,和他握了手,并祝我早日康复,随后告辞离开。
我趴在病床上回想这过去的一个多礼拜时间发生的事,上下忙活,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白折腾。我想着这趟回合肥,J哥和范山人要对我们失望了。
在杭州住院治疗结束后,我提出要去梦云舒家里看看,他拒绝了,于是,我们回了趟全椒,拜访了活老九,梦云舒把情况说给它听了,活老九一开始以为这么复杂的情况是我俩编织出来的,但是梦云舒向它起誓保证,活老九才有点相信,不过它提出要和我们一起走一趟大奇山,目的很明确,得到李嵩画。梦云舒没有直接拒绝,说要先回合肥向粘杆处详细交待情况。活老九暂时同意,特意叮嘱我们去之前一定要带上它。
当天我们没有回合肥,而是回了趟白酒。
从全椒等车到家后,时候已经近黄昏了。二老不在家,门上的大锁紧紧扣着,我摸了下门后的洋钉,没有钥匙(以前农村人出门,大门虽然上锁,但是经常会把钥匙挂在后门的洋钉上,或者藏于墙台上捶衣棒下面),我便到田里去找。二老种了七亩多地,这个季节正是翻土的时间,我猜他们应该在田里忙活。
我找到自家的农田时,看到三姐和三姐夫弯着腰在田里干活,三姐夫用铁锹通水沟,三姐则往田土上洒锅膛灰。我的小外甥坐在田埂上,玩着三姐夫给他捉的田鸡。夕阳无限美,只是近黄昏,残阳红透半边天,田野到处鸣叫着蛙声和虫声,这一幕只会在美丽的农村出现。我高举双手朝他们喊,伤口处立马一阵疼痛,疼得我眼一闭,梦云舒说:“你还没好清,动作小一点,你姐能看见你!”
小外甥听见我的声音,立马踉踉跄跄朝我跑来,憨态可掬。我冲过去蹲下,对他又亲又抱的,他还不忘丢掉手里的田鸡。我不能抱起他,便丢掉他的田鸡玩具,牵着他走到田里,对三姐说:“你俩也不买个玩具给我大外甥!”
三姐拍拍手上的锅膛灰,擤了把鼻涕,沾了一鼻头的灰,对我说:“玩具不要钱买啊,你怎搞又跑回来了?”三姐是和我开玩笑的。三姐夫说她,“经纬有些日子没回来了,好不容易回来,你还说人家又跑回来了,走吧走吧,不挖了,明天再来,回去给我们家大学生做晚饭去!这是你朋友啊?”
三姐和三姐夫都没见过梦云舒,我赶紧介绍道:“妈嘞!差点忘了我师父,这是我师父啊!梦云舒同志!”
他俩立马双眼放光,道:“啊!你就是梦大哥啊,哎呦,欢迎欢迎!经纬讲你和我大我妈差不多大,这确实看不出年纪啊,是不是要叫梦叔啊?”
梦云舒不让他们叫梦叔,就叫他梦大哥,还显得年轻。
三姐让我外甥喊梦云舒“老爹”,外甥嘴巴很甜,立马叫梦云舒“老爹”,我告诉他“老爹”就是爷爷的意思。梦云舒哈哈笑道:“我也没准备红包啊!”
我问三姐二老去哪了,三姐说去水湾老太那烧香去了。我之前提过,自从古河老太倒台后,水湾两个老太号称花娘子和老郭友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了,可能这三人不是活老九的人,但是活老九肯定会对他们仨下手。我告诉三姐:“以后我不在家时,禁止你们去这老太那老太烧香,搞不好都像古河老太一样,身上附了什么妖怪,耍花招骗钱!我们天天和这些成精的东西打交道,都知道这些鬼东西什么情况,上次我不都说了,不要去信这些鬼东西!”
三姐夫在旁边说:“经纬,大和妈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们看人家都去求香,也想去给我们求求平安。”
我说:“烧香拜佛都是上午去,这水湾老太,下午还能去烧香啊,这和张开裘的耶稣教一样,肯定不正规!”我这话不是瞎扯的,烧香上坟看望病人这一类活动都是忌讳下午时间段,姑苏城的寒山寺,大老板们为了新年第一柱香和第一声钟,抢得挤破头,我们当地的三塔寺,每年正月十五头柱香,都要找关系才能烧上。
到家后,小外甥一直缠着梦云舒,要他陪他玩,梦云舒坐在小板凳上,小外甥围着他一直转圈,时不时跑他怀里歪着头,爬他腿上骑着一点不认生。
刘宝童说:“那我回老家安置我哥了。”她沮丧的样子令人心疼。
梦云舒问她要了固话号码,同时也把合肥粘杆处的电话和地址告诉了她,梦云舒说:“你哥不会白白牺牲,等我们休整好,再定时间去梨园拿回李嵩画!”
刘宝童手伸向梦云舒,和他握了手,并祝我早日康复,随后告辞离开。
我趴在病床上回想这过去的一个多礼拜时间发生的事,上下忙活,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白折腾。我想着这趟回合肥,J哥和范山人要对我们失望了。
在杭州住院治疗结束后,我提出要去梦云舒家里看看,他拒绝了,于是,我们回了趟全椒,拜访了活老九,梦云舒把情况说给它听了,活老九一开始以为这么复杂的情况是我俩编织出来的,但是梦云舒向它起誓保证,活老九才有点相信,不过它提出要和我们一起走一趟大奇山,目的很明确,得到李嵩画。梦云舒没有直接拒绝,说要先回合肥向粘杆处详细交待情况。活老九暂时同意,特意叮嘱我们去之前一定要带上它。
当天我们没有回合肥,而是回了趟白酒。
从全椒等车到家后,时候已经近黄昏了。二老不在家,门上的大锁紧紧扣着,我摸了下门后的洋钉,没有钥匙(以前农村人出门,大门虽然上锁,但是经常会把钥匙挂在后门的洋钉上,或者藏于墙台上捶衣棒下面),我便到田里去找。二老种了七亩多地,这个季节正是翻土的时间,我猜他们应该在田里忙活。
我找到自家的农田时,看到三姐和三姐夫弯着腰在田里干活,三姐夫用铁锹通水沟,三姐则往田土上洒锅膛灰。我的小外甥坐在田埂上,玩着三姐夫给他捉的田鸡。夕阳无限美,只是近黄昏,残阳红透半边天,田野到处鸣叫着蛙声和虫声,这一幕只会在美丽的农村出现。我高举双手朝他们喊,伤口处立马一阵疼痛,疼得我眼一闭,梦云舒说:“你还没好清,动作小一点,你姐能看见你!”
小外甥听见我的声音,立马踉踉跄跄朝我跑来,憨态可掬。我冲过去蹲下,对他又亲又抱的,他还不忘丢掉手里的田鸡。我不能抱起他,便丢掉他的田鸡玩具,牵着他走到田里,对三姐说:“你俩也不买个玩具给我大外甥!”
三姐拍拍手上的锅膛灰,擤了把鼻涕,沾了一鼻头的灰,对我说:“玩具不要钱买啊,你怎搞又跑回来了?”三姐是和我开玩笑的。三姐夫说她,“经纬有些日子没回来了,好不容易回来,你还说人家又跑回来了,走吧走吧,不挖了,明天再来,回去给我们家大学生做晚饭去!这是你朋友啊?”
三姐和三姐夫都没见过梦云舒,我赶紧介绍道:“妈嘞!差点忘了我师父,这是我师父啊!梦云舒同志!”
他俩立马双眼放光,道:“啊!你就是梦大哥啊,哎呦,欢迎欢迎!经纬讲你和我大我妈差不多大,这确实看不出年纪啊,是不是要叫梦叔啊?”
梦云舒不让他们叫梦叔,就叫他梦大哥,还显得年轻。
三姐让我外甥喊梦云舒“老爹”,外甥嘴巴很甜,立马叫梦云舒“老爹”,我告诉他“老爹”就是爷爷的意思。梦云舒哈哈笑道:“我也没准备红包啊!”
我问三姐二老去哪了,三姐说去水湾老太那烧香去了。我之前提过,自从古河老太倒台后,水湾两个老太号称花娘子和老郭友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了,可能这三人不是活老九的人,但是活老九肯定会对他们仨下手。我告诉三姐:“以后我不在家时,禁止你们去这老太那老太烧香,搞不好都像古河老太一样,身上附了什么妖怪,耍花招骗钱!我们天天和这些成精的东西打交道,都知道这些鬼东西什么情况,上次我不都说了,不要去信这些鬼东西!”
三姐夫在旁边说:“经纬,大和妈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们看人家都去求香,也想去给我们求求平安。”
我说:“烧香拜佛都是上午去,这水湾老太,下午还能去烧香啊,这和张开裘的耶稣教一样,肯定不正规!”我这话不是瞎扯的,烧香上坟看望病人这一类活动都是忌讳下午时间段,姑苏城的寒山寺,大老板们为了新年第一柱香和第一声钟,抢得挤破头,我们当地的三塔寺,每年正月十五头柱香,都要找关系才能烧上。
到家后,小外甥一直缠着梦云舒,要他陪他玩,梦云舒坐在小板凳上,小外甥围着他一直转圈,时不时跑他怀里歪着头,爬他腿上骑着一点不认生。
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从东边下坡上来,唱嗷嗷的,心情十分不错。父亲看见我和梦云舒,欢喜若狂地朝我们挥舞着手。梦云舒站起来,礼貌地和二老打招呼,母亲见我们没有倒水给梦云舒喝,客气地跑去厨房倒了一碗热水给他,还批评我道:“你师父来了,水都不知道倒吗?!”
我问她,“哎!妈,妈!我小墨迹呢?”
母亲忽然慌张起来,一副前后寻找的样子,说:“妈嘞!这完了,易**,小墨迹呢?”
父亲白了她一眼,“小墨迹不在你那啊?!”
母亲着急道:“不在我这啊,哪有啊!”
我心里一凉,想到小墨迹被他们弄丢了,梦云舒也跟着紧张起来,结果小墨迹自己从母亲口袋里挤出来,跳到地上,朝我跑来。我立马知道母亲故意在吓我,我一边接上小墨迹,一边说她:“妈!你装得真像!”她掐着腰,哈哈笑起来。
我揉着了一顿小墨迹,它爬到我头上,在头发里蹲着,掏来掏去。
三姐夫洗完手坐到梦云舒旁边和他聊天,他是个话痨。母亲从屋里扛出一头拴着镰刀的长竹竿,要割点香椿头做一道菜。这时候的香椿头已经不如三月初时那么嫩,但是因为经常被割,目前还能吃,香椿头炒黑臭干可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佳肴,相信大多数人没有品尝过。
我跟着母亲在香椿树下捡香椿头,忍不住说了她几句,让她不要再去给水湾老太送钱,我说:“妈,这水湾老太搞到末末了(意思是搞到最后),要是有问题,像古河老太那样,还是要被我们收掉,都是一些没有大道的猫狗之辈,骗农村人钱!”
母亲不让我这么说,她说水湾老太真是花娘子附身给人看病祛灾,大家都说灵验。当然,她也是为了我好,不管真假,求个平安总没错。她觉得我天天跟着别人后面逮成精的灵物,肯定会得罪“赤黄白柳”这类大仙。“赤黄白柳”我想不必多说,很多人对这四个东西做过大文章,解读过度。其中,这个“柳”代表蛇。母亲那天说水湾两个老太告诉去烧香的人,她们前一夜看见一条好粗的大白蛇从门前水塘里游到院子门口,向她们传达了一些旨意。我当时就告诉母亲,这肯定是水湾老太编的故事,就算是真的,和梦云舒的白仓大仙比起来,大白蛇只是白仓一个脚趾头大的小妖。
我和梦云舒在家里待了一晚,第二天启程回合肥,期间,我没敢和母亲说我受的伤,怕她又要担心唠叨我。虽然交通不便,我还是在从乡下到了县城后,绕到二姨家去看望外婆,她两边嘴巴的肉拽拽的,又长胖了,我告诉她,下次我再回来时,我就把她接到家里去住一程,反正有拖拉机也方便。我和外婆长聊了很久,以至于梦云舒在村头等了太长时间,见到我,就数落我是老墨迹!我告诉他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感情深,外婆越来越老,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我十分害怕她有一天会离开我。
梦云舒理解我,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好好珍惜吧!”
那天下午我们乘车到了合肥,下了车,我俩饿得赶紧找了个路边摊,吃了碗牛肉汤,加了六块烧饼,才填饱肚子。等我们回到粘杆处,发现宫里佛竟然大驾光临。J哥的办公室里,一共五个人,宫里佛看见我们,非常热情地站起来迎接我俩,说道:“两位功臣回来了!哈哈!苏总管,你这里人才济济啊!”
J哥靠在椅子上,问我们:“东西拿到了吗?”
我摇摇头,正准备解释,J哥拦了我的话,说:“今天先不谈摘灵的事,你们的救命恩人来了!”
我和宫里佛紧紧握了手,坐到张小美旁边,悄悄问她:“张姐,你屁股好了啊?”
张小美说:“好差不多了,你俩去徽州后,我就出院了,贴着膏药在的,慢慢就会痊愈。”
我俩悄悄话没再继续,听宫里佛说起他和J哥的师父。之前在龙虎山时,宫里佛提到他师父是最伟大的虫师,精于内外虫术。宫里佛说他师父俗名为杨青红,绰号色彩哥,道号曾道子,曾经在重阳宫里修道,主要工作还是做虫类研究。重阳宫地位和天师府一样重要,旁边是王重阳“活死人墓”的成道宫。宫里佛和J哥在重阳宫和成道宫都待过不少日子,后来随师父到了终南山,悉心传授他俩内外虫术。曾道子控尽天下虫类,靠的不是蛮力武力,而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曾道子对待万虫皆友善,即使是某些害虫,使得这些虫类都敬畏他,在他羽化时,有万虫送葬之壮观场景。
我问她,“哎!妈,妈!我小墨迹呢?”
母亲忽然慌张起来,一副前后寻找的样子,说:“妈嘞!这完了,易**,小墨迹呢?”
父亲白了她一眼,“小墨迹不在你那啊?!”
母亲着急道:“不在我这啊,哪有啊!”
我心里一凉,想到小墨迹被他们弄丢了,梦云舒也跟着紧张起来,结果小墨迹自己从母亲口袋里挤出来,跳到地上,朝我跑来。我立马知道母亲故意在吓我,我一边接上小墨迹,一边说她:“妈!你装得真像!”她掐着腰,哈哈笑起来。
我揉着了一顿小墨迹,它爬到我头上,在头发里蹲着,掏来掏去。
三姐夫洗完手坐到梦云舒旁边和他聊天,他是个话痨。母亲从屋里扛出一头拴着镰刀的长竹竿,要割点香椿头做一道菜。这时候的香椿头已经不如三月初时那么嫩,但是因为经常被割,目前还能吃,香椿头炒黑臭干可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佳肴,相信大多数人没有品尝过。
我跟着母亲在香椿树下捡香椿头,忍不住说了她几句,让她不要再去给水湾老太送钱,我说:“妈,这水湾老太搞到末末了(意思是搞到最后),要是有问题,像古河老太那样,还是要被我们收掉,都是一些没有大道的猫狗之辈,骗农村人钱!”
母亲不让我这么说,她说水湾老太真是花娘子附身给人看病祛灾,大家都说灵验。当然,她也是为了我好,不管真假,求个平安总没错。她觉得我天天跟着别人后面逮成精的灵物,肯定会得罪“赤黄白柳”这类大仙。“赤黄白柳”我想不必多说,很多人对这四个东西做过大文章,解读过度。其中,这个“柳”代表蛇。母亲那天说水湾两个老太告诉去烧香的人,她们前一夜看见一条好粗的大白蛇从门前水塘里游到院子门口,向她们传达了一些旨意。我当时就告诉母亲,这肯定是水湾老太编的故事,就算是真的,和梦云舒的白仓大仙比起来,大白蛇只是白仓一个脚趾头大的小妖。
我和梦云舒在家里待了一晚,第二天启程回合肥,期间,我没敢和母亲说我受的伤,怕她又要担心唠叨我。虽然交通不便,我还是在从乡下到了县城后,绕到二姨家去看望外婆,她两边嘴巴的肉拽拽的,又长胖了,我告诉她,下次我再回来时,我就把她接到家里去住一程,反正有拖拉机也方便。我和外婆长聊了很久,以至于梦云舒在村头等了太长时间,见到我,就数落我是老墨迹!我告诉他我从小是外婆带大的,感情深,外婆越来越老,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我十分害怕她有一天会离开我。
梦云舒理解我,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好好珍惜吧!”
那天下午我们乘车到了合肥,下了车,我俩饿得赶紧找了个路边摊,吃了碗牛肉汤,加了六块烧饼,才填饱肚子。等我们回到粘杆处,发现宫里佛竟然大驾光临。J哥的办公室里,一共五个人,宫里佛看见我们,非常热情地站起来迎接我俩,说道:“两位功臣回来了!哈哈!苏总管,你这里人才济济啊!”
J哥靠在椅子上,问我们:“东西拿到了吗?”
我摇摇头,正准备解释,J哥拦了我的话,说:“今天先不谈摘灵的事,你们的救命恩人来了!”
我和宫里佛紧紧握了手,坐到张小美旁边,悄悄问她:“张姐,你屁股好了啊?”
张小美说:“好差不多了,你俩去徽州后,我就出院了,贴着膏药在的,慢慢就会痊愈。”
我俩悄悄话没再继续,听宫里佛说起他和J哥的师父。之前在龙虎山时,宫里佛提到他师父是最伟大的虫师,精于内外虫术。宫里佛说他师父俗名为杨青红,绰号色彩哥,道号曾道子,曾经在重阳宫里修道,主要工作还是做虫类研究。重阳宫地位和天师府一样重要,旁边是王重阳“活死人墓”的成道宫。宫里佛和J哥在重阳宫和成道宫都待过不少日子,后来随师父到了终南山,悉心传授他俩内外虫术。曾道子控尽天下虫类,靠的不是蛮力武力,而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曾道子对待万虫皆友善,即使是某些害虫,使得这些虫类都敬畏他,在他羽化时,有万虫送葬之壮观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