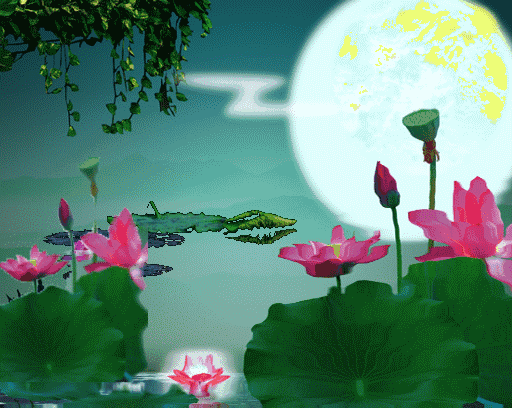正坤讪笑一下说:“就是那谁嘛,那个小任。刚好在街上碰到,就一块儿来吃个饭。”
李大明说:“二哥,要不,你跟小任都端出来吃吧,外头凉快一些。咱兄弟俩平时在一块吃饭的机会也不多,刚好喝上几口。”
正坤说声:“那行吧。”拧身就往门里走,却没注意,差点跟迎门出来的服务员撞个满怀。那服务员急忙就往一旁趔,握在手里的两瓶啤酒也差点没掉落地上,少不得要嘟囔一下。正坤听在耳朵里,心里有些窝火,但一想妹妹妹夫都在跟前,跟一个服务员计较未免掉价,便没吱声,却快步走进门去。见任晓霞已吃毕了,他便也两口扒拉光了盘中的炒面,从裤袋里掏出一团卫生纸擦了擦嘴,这才说:“是正淑她对象开的账。”又说:“咱出去跟他们坐一会儿吧。”任晓霞笑着点了点头。
……又过了四五十分钟,四个人方离开饭馆。李大明摩托车带了正淑,继续往北新街西段骑去。正坤跟任晓霞则沿着街边,不紧不慢地朝服装厂方向走去。
走了一程后,任晓霞突然说:“咱俩也认识好几个月了,可你还不知道我在哪住着吧?”
正坤想了想说:“我还真不知道呢!”
任晓霞便又说:“当领导的还就是官僚!一点都不知道关心群众。”
正坤道:“我是啥领导哎?只是个实习生,最多过一年就走了。说不定过上两年我回来的时候,你就混成领导了呢!”
“可是在我心里,你就是领导!”
“那就领导吧。”
任晓霞噗嗤一笑,又说:“那就请领导关心一下我这个群众,到我屋坐一会儿吧。反正你上班还早呢,对吧?”
正坤也笑了笑说:“在厂里可不敢叫我领导噢,免得人笑话。”
任晓霞道:“遵命,领导!”
又往前走了不多远,任晓霞将手一指说:“马上到了,前边那条巷子就是。”
正坤笑道:“原来服装厂的宿舍楼在这儿啊?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你真是官僚!”任晓霞笑瞪他一眼说,“咱厂里哪有啥宿舍楼呢?你们罗原城里的人,都在自家屋里住着,我们外地人都在厂里头东一坨西一坨乱住着,办公楼里头住的也有,车间里头住的也有。我的宿舍本来就在我车间前面,总共八间宿舍,住了六十四个女工。我嫌太挤掐,就自己在外头租了一间房。平时自己想做个饭啥的,也方便些。”
不知不觉间,两人已进了这个叫做“仁义巷”的巷子。往巷里又走了十来米,任晓霞推开一扇铁门,将正坤领进了一座院子里。这是一座很有些农家气息的院子,一座四间两层楼房盖着瓦帽子面南背北坐落着。紧靠东院墙(也就是正对着这扇铁门的那堵院墙),四个木桩子以及好几根枯树枝连同拉在木桩之间几根铁丝架起了几藤黄瓜。院子里的地面却平平整整的,除了那坨种黄瓜的角落外,全以混凝土铺就。在这院子里打量了一圈后,王正坤暗暗觉得,这才是人住的地方,他家那院子,整日家都潮乎乎的,空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鱼腥味与霉味还有其它一些说不出名目的古怪味道。他家的正房都是土墙,不用说,院子里更是晴天满地尘土,雨天是一院子泥水……
他突然就想,任晓霞也去他家里好几回了,不知道心里头会不会笑话他家像个猪圈呢?正想着,忽听得任晓霞笑道:“领导,你瓷到那儿弄啥呢?到屋里坐吧。”正坤这才回过神来,却见任晓霞站在一楼最西边那间屋子的门口,门在她身后却已经敞开了。
他便笑了笑,走过去,口里说着:“这院子还蛮干净。”任晓霞也笑了笑说:“倒也还行。院里住的都是上班的,也没有小娃,也没人养狗啊啥的,所以收拾起来也方便。关键是房东厉害,虽说不在这儿住,但给房客排了卫生值日表,每人两天往过轮。房东要是来了,看见院子不干净,也不多说话,一查是谁值日,就在谁门上贴个条子,罚款五块,叫最迟第二天就给她屋缴。如果没交,不客气,第三天她就会来撵你走。”
说话间,两个人都已进了屋子。任晓霞便又招呼正坤坐,她则忙手忙脚地给他倒茶。正坤在紧靠东墙的一张长条沙发里落了座,瞅了眼面前的茶几子,又瞅了一眼东西向横拉在屋子中间的那道布帘子,然后便在帘子外边这间狭小的空间里乱瞅起来,却见除了沙发、茶几之外,还有一张三斗桌靠窗放着,桌面上放有案板和锅碗盆瓢,桌子底下却码了好些蜂窝煤,搭眼看去,足有二百来块。西墙下,却是一个蜂窝煤炉子,上面坐着铝壶。一旁的地上一字儿摆着米袋子、面袋子以及一小堆洋芋、少许青菜、小葱等物,下面都铺着硬纸板。
他便笑了笑说:“你一个人住,咋还置办了这么些家具?还米面啥都有,经常做饭啊?”
任晓霞已泡好了茶,双手捧过来放在正坤面前,一边说着话,一边去他身边坐下:“我还置办家具啊?是前面那个房客搬走的时候留下的,人家多半是个大款,沙发、茶几,床板、床头,煤炉子,啥都没拿走。房东本来想把这屋里的东西搬到她家里去呢,见我说话嘴甜,又是外地人,挣钱不容易,就答应叫我免费用。那个长条桌是我叫了两个小伙子从厂里拿出来的。所以呢,这屋里除了我身上穿的,床上铺的盖的,跟锅啊、碗啊啥的是我买的,别的东西,我买的还真不多。”
正坤笑道:“你这嘴也真能说!”突然无意间朝她胸前瞥了一眼,便隐隐看见了她月白色短袖衫里的半抹丰腴,不由的把脸腾地红了,恰好任晓霞看在眼里,笑问:“你咋了?是不是屋里太热,把脸都热红了?”
“不,不是。我想上厕所。”正坤胡乱搪塞着。
“厕所在最东边,楼梯间的隔壁。门上写有字。”任晓霞笑道,“你能寻着吧?要是寻不着,我领你去?”
正坤说声:“你说的啥话?!”急忙站起身来,抢出门去。
任晓霞也紧跟着走到门口,见他不紧不慢地朝厕所走去,不觉噗嗤一笑,然后急忙折身进屋,却将门砰地关上,急急往布帘子里边去了。
正坤并没有尿意,所以在厕所里呆了不足两分钟便出来了。回到任晓霞屋门口时,见门关着,便推了推,却没推开,他便打算离开,再一想,没打招呼就走,未免不美,就朝屋里喊道:“小任,我走了噢。”
“你急得弄啥啊?我正给你拿好东西呢!”任晓霞的声音从里间响了出来。须臾,门开了。她身上竟已换了衣服,不再是短袖衫长裤子,而是换成了一件连衣裙,颜色灰不拉几的,正坤猛一看去,就像是睡裙一样。
“到里间坐吧,有风扇,凉快些。”将正坤让进屋后,任晓霞却又将门碰住,一边说着话,一边就将他朝布帘子里边引。里间果然有一台落地扇,对着一张单人床,呼呼地吹着。床前一角,却搁着一只塑料脸盆。盆子里堆着胸*罩、裤*头,它们的下面却是任晓霞刚才穿的长裤和短袖。
看到盆里的那些东西,正坤不由得又把脸红了。任晓霞看了一眼他的脸,又瞅了一眼脸盆,讪笑一下说:“刚才确实怪热的,我身上黏糊糊的,所以就趁你上厕所,把衣服换了。”
正坤点了点头,“噢”了一声,又问:“你说的好东西呢?是啥好东西?”
任晓霞笑道:“你急啥?先坐,床边坐。等凉快一会儿了,我给你取。”
正坤便去床边坐下。任晓霞也去床边,挨着他坐下了。默默坐了一会儿后,任晓霞突然侧身朝向他,笑道:“你看我这连衣裙咋样?是用咱厂裁衣服剩下的下脚料做的。”
正坤把头一低说:“挺好的。”
“你看都不看,咋知道好不好?你把布料摸的试一下吧。”任晓霞说着,却又将脊背给了他,“哎,你先给我帮忙把拉链拉一下,我够不着。”
正坤扭头一看,却见她裙子后面的拉链半开在脊背上,不觉有些奇怪,他印象中刚才她的连衣裙拉链好像不是这样子。不过,也许是他刚才没注意吧?
正坤愣了愣神,诚惶诚恐地站起身来,又略一弯腰,抖抖索索地就帮她拉连衣裙拉链。不想因为太紧张,拉链并没拉上去,手指却碰触在了她的肌肤上。他触了电似的浑身一阵酥麻,却又隐约看见,她的裙子下面好像没有穿胸*罩。他不由得心里咚咚狂跳起来,连咽了好几口唾沫,急忙将双手缩回,有些不知所措了。
恰这时,任晓霞转过身来,埋怨道:“你咋慢成这了?”他猛然发现,她的裙子前领早已垮塌到胸*脯上,便半截浑圆白腻跌入他眼中。
正坤呆愣愣地好半日也说不出话来。
“你看啥呀!”随着一声软叫,任晓霞竟仰面倒了下去。正坤隐隐感觉到被一股什么力量带着,便也朝前倾倒了,不偏不倚,恰好压在她身上。不知道是他动的手,还是任晓霞自己动的手,反正片刻之后,她的裙子便离开了身体,缩成一堆,团在了她脑袋的一侧。他把手胡乱一模,这才发现,她不光没穿胸*罩,就连裤*头也没穿……
后来,他心里懊悔极了,便胡乱地穿上了衣裤,又扯过毛巾被胡乱地盖在她身上。然后,侧坐在床边,低声说:“对不起,我不该……”
任晓霞脸上羞羞地红着,半日不语。突然又低声埋怨道:“你还讲究是大学生呢,咋那么粗野?我现在还疼得要命!”
正坤看了她一眼,不觉也把脸红了,低声说:“你咋了?啥地方疼?”
任晓霞脸上越发红得厉害,将头迈向一边,淡淡地说:“你还问我?你刚才弄啥了?你说我啥地方疼?!不信你自己看!”说话间早揭起毛巾被,掀到一边。
正坤扭头一看,却见她大腿上有好几处猩红的斑点,不觉有些吃惊,喃喃道:“咋像是血……”话音未落,却早被她猛地一拉,便又扑倒在她身上。然后任晓霞便吃吃笑了,悄声说:“我现在不是姑娘娃了,但是我愿意。”
正坤半日不语,却怔怔地看着她的脸,然后就忍不住亲了她一口。任晓霞也回亲了他一下,又说:“你是不是有些喜欢我?”
正坤想说:“我不知道。”但没说出口,却胡乱地“嗯”了一声。
“一个大学生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激动得不行。”任晓霞说着,又亲了正坤一口,然后便看着他的眼睛,悄声说:“要不,你也把衣服脱了,躺一会儿吧。”
“啊?”正坤有些犹豫。
“不愿意脱了算了,你滚!我还当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呢,想不到把人便宜一占,就不想认账了!”任晓霞似乎有些生气了,一边说一边狠狠地瞪他。
正坤喉咙里说了声:“我脱……”爬起身来,一颗颗解开了衣扣。
当他一丝不挂地躺在她身边时,她却突然一翻身,趴在了他身上,悄声说:“你吃*奶不?”
正坤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便说:“我小时候屋里困难,我妈奶*水少,那时候也没有奶粉……”
一句话未说完,任晓霞却噗嗤笑了说:“瓜子!”
“啥?”
任晓霞也不言语,却将身子朝上蹭了蹭,把一枚草*莓塞进他嘴里。正坤一下子感觉到浑身涨得要爆炸了,便猛一翻身,将她压在了身底……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浑身汗津津地翻身下来。任晓霞却迷离着眼睛,一抹头发乱在脸上,似乎睡着了。
又躺了半日后,正坤突然说:“我一定要对你负责!”
任晓霞猛张开眼睛,侧起身子,看着他说:“谁要你负责了?我喜欢你,所以跟你睡觉,我愿意!”
“我一定要对你负责!”正坤继续说着,“等我大学毕业后,一定跟你结婚!”
“我可没奢望那么多!”任晓霞脸上悬着笑,“你以后放心去念书,我不缠你。要是你以后还能记得我,时里猛里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心满意足了。”
正坤说:“你放心,我不是没良心的人!”
“你不要心里有啥负担。”任晓霞悄声说,“你以后要是到大地方工作了,把我忘了就忘了吧。”说着说着,却又趴到了他身上。
“你咋还想啊?我都不行了……”正坤心里多少有点怯火。
任晓霞却噗嗤一笑,然后就逮住他的肩膀,狠狠咬了下去。
正坤疼得“哎哟”一声,说:“你咬我弄啥?”
“我要给你留个记号,你以后把我忘了不要紧,只要肩膀上有这二十四个牙印就行。”任晓霞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很认真地说。
正坤笑了笑,没有言语。
任晓霞又说:“反正我这儿你也能寻着了,你以后不管啥时候只要想我了就来。”
正坤看着她的眼睛,“嗯”了一声,突然又问:“你刚才说要给我好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事?”
“讨厌!”任晓霞欠起身子,在他腔子上楔了一拳,又瞪他一眼说:“你把我当成啥人了?!好像我是专门勾*引你一样!其实我是真的要给你取好吃的呢,叫你把人害的,都没顾得取!”
“啥好东西呀?只个吊我胃口!”
“我爸午季来给我送粮的时候,还捎了些我老家的大板栗,个儿又大,又面得不行,比罗原街道上卖的板栗好吃多了。”任晓霞说着,翻身就下了床。
正坤急忙说:“你弄啥啊?咋不把衣服穿上?精沟子也不嫌怪!”
任晓霞回头朝他笑了一下,说道:“在自己屋里,除了你又没人看得见,有啥怪的?”然后便在床前跪了下去,却将一只手扶着床沿,另一只手朝床底伸了进去。少顷,她拉出来了一个圆鼓鼓的小布口袋,当下就将扎着布袋口的绳子解开了,手伸进去掏出来两个板栗,又站起身上床坐在了正坤身边,将板栗递给他说:“这是生的,可是也甜甜儿的,好吃着呢。”正坤将一个板栗外壳咬开一个小口,用手剥了,又咬了一口板栗瓤,果然甜丝丝的,便笑了一下。任晓霞却又开始给他讲她小的时候跟一帮男娃子一道上树偷板栗之类的趣事。
……不知不觉间已经快两点了,王正坤便急忙穿了衣服欲去上班。
任晓霞今日是慢倒班,早上八点刚下了班,要到明日下午四点才去上班,今日下午因为没什么事,便赖在床上不肯起来。
正坤走到门口正欲开门出去时,她却突然喊道:“哎,下午下班了到我这儿吃饭吧。我给你做好吃的。”
“做啥好吃的?”正坤回头笑问。
“你来了就知道了!”
正坤便不再吱声,却笑着开门出去,又很小心地将门拉上,试了试确定锁住了,才放心离去。快到巷子口时,他却又莫名其妙地唱起流行歌曲来:“……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