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各位鼓励!
莫言你读书万卷,且到此处来,听野老谝闲 (乡村奇人奇事的真实记录
野老谝闲之第十篇
二 财主
民国年间我们村有两个财主。一个是李旺财。李旺财做庄稼是全把式,还是个顶呱呱的好木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干木活;木活干到深夜,打个盹,不等天亮就又上地。上集赶会大家都不愿和他相跟,走着走着就站住不动——睡着了。一盒火柴要用一年,还常年吃糠咽菜。他说:吃的再好顶啥用?到肚里还不都成了屎!而且吝啬,左邻右舍二斗麦也不借。拼死拼活,最终置地七十多亩,放过贷,雇过工,正好戴个地主帽子。
和李旺财隔一条巷子的还有一家财主,大号石丁山,人称二财主。之所以称二财主,是因为他是由大财主派生出来的财主,就好比是一棵大树分出来的枝杈。虽是枝杈,因为那树太大,枝杈也就很可观。二财主石丁山在我们村是首富,出了村也叫得响,但和他的东家昝家比起来就差远了,昝家才是方圆几十里的头号大财主。
咱就说说昝家吧。昝家家住昝家沟,几辈子都在川西做麝香生意——从藏民那里收购麝香,拿到成都卖掉,再采购回些绸缎布匹茶叶之类在藏区出售,做两头生意。世代于兹,经验老到,麝香一沾手就分优劣,出价也公道,信誉卓著,生意兴隆,分店很多。石丁山是某个分店的掌柜,类似现在的二级经理。昝家的老祖宗是怎样从一个穷山沟一直跑到遥远的川西的,已无从考证。要之,那时的生意人都跑得远,而且似乎跑得越远那生意便越火,发财也越大,有胆量跑到国外的,自会是沈万三式的国际大财主。至今人们说到昝家,还会提到昝家老爷子做寿那回。那还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去看热闹,我爷爷我奶奶也去了。场面之大之豪华已无人能说得清了,说得清的只是几个断片。断片一:两根红蜡烛足有一人高,木桶粗,上边还刻着龙啊凤啊之类图案,栩栩如生。烛捻子胳膊粗,烛火一尺高,若在上面搭口锅,顷刻可烧开一锅水。断片二:白银制作的“麻姑献寿”真人大小,放在庙里可以当神敬,但比庙里的神像更像神,据说是四川的一个什么大人物送的贺礼。断片三:唱了三天大戏,请的都是晋南最走红的戏班子,唱的是对台戏,琼才的《挂画》就是那回出名的。断片四:还请了几班乐人,远近闻名的吹鼓手齐聚一堂,无异冠军大赛,高手们各显神通,竞奇斗艳,有的竟会两个鼻孔吹唢呐。由残片而窥全貌,那时无疑是昝家的鼎盛时期。后来洪杨造反,昝家元气大伤;再后来军阀混战,更是江河日下;待到抗战前期昝家已沦为小本生意人了。建国后还有人在成都见过昝家的大东家,是在街头摆烟摊。到那个地步仍未回乡,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还是已将客乡作故乡了?不得而知。
二 财主
民国年间我们村有两个财主。一个是李旺财。李旺财做庄稼是全把式,还是个顶呱呱的好木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干木活;木活干到深夜,打个盹,不等天亮就又上地。上集赶会大家都不愿和他相跟,走着走着就站住不动——睡着了。一盒火柴要用一年,还常年吃糠咽菜。他说:吃的再好顶啥用?到肚里还不都成了屎!而且吝啬,左邻右舍二斗麦也不借。拼死拼活,最终置地七十多亩,放过贷,雇过工,正好戴个地主帽子。
和李旺财隔一条巷子的还有一家财主,大号石丁山,人称二财主。之所以称二财主,是因为他是由大财主派生出来的财主,就好比是一棵大树分出来的枝杈。虽是枝杈,因为那树太大,枝杈也就很可观。二财主石丁山在我们村是首富,出了村也叫得响,但和他的东家昝家比起来就差远了,昝家才是方圆几十里的头号大财主。
咱就说说昝家吧。昝家家住昝家沟,几辈子都在川西做麝香生意——从藏民那里收购麝香,拿到成都卖掉,再采购回些绸缎布匹茶叶之类在藏区出售,做两头生意。世代于兹,经验老到,麝香一沾手就分优劣,出价也公道,信誉卓著,生意兴隆,分店很多。石丁山是某个分店的掌柜,类似现在的二级经理。昝家的老祖宗是怎样从一个穷山沟一直跑到遥远的川西的,已无从考证。要之,那时的生意人都跑得远,而且似乎跑得越远那生意便越火,发财也越大,有胆量跑到国外的,自会是沈万三式的国际大财主。至今人们说到昝家,还会提到昝家老爷子做寿那回。那还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去看热闹,我爷爷我奶奶也去了。场面之大之豪华已无人能说得清了,说得清的只是几个断片。断片一:两根红蜡烛足有一人高,木桶粗,上边还刻着龙啊凤啊之类图案,栩栩如生。烛捻子胳膊粗,烛火一尺高,若在上面搭口锅,顷刻可烧开一锅水。断片二:白银制作的“麻姑献寿”真人大小,放在庙里可以当神敬,但比庙里的神像更像神,据说是四川的一个什么大人物送的贺礼。断片三:唱了三天大戏,请的都是晋南最走红的戏班子,唱的是对台戏,琼才的《挂画》就是那回出名的。断片四:还请了几班乐人,远近闻名的吹鼓手齐聚一堂,无异冠军大赛,高手们各显神通,竞奇斗艳,有的竟会两个鼻孔吹唢呐。由残片而窥全貌,那时无疑是昝家的鼎盛时期。后来洪杨造反,昝家元气大伤;再后来军阀混战,更是江河日下;待到抗战前期昝家已沦为小本生意人了。建国后还有人在成都见过昝家的大东家,是在街头摆烟摊。到那个地步仍未回乡,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还是已将客乡作故乡了?不得而知。
再说石丁山。石丁山十三岁就到四川,在昝家的店铺里熬相公,就是做学徒。那时农家子弟读书的少,条件好点的,读书也不过数年,能识的几个字,记的几笔帐,就要自谋生路了。家里地多能自給的,就安安稳稳种地,是为上选;否则就得投门子学点吃饭的本事。熬相公是选择之一,很苦,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熬得上的。石丁山和昝家沾点瓜蔓亲,才获此机会。十三岁的孩子,是如何跋山涉水几千里到四川的?无法想象。去时背个铺盖卷,人小铺盖更小,小得盖不住脚,睡觉时便用根麻绳把被头捆住。不过人聪明,也吃的苦。掌柜晚上要算账,睡得迟,小丁山总要侍候掌柜就寝才休息。鸡叫头遍就起床,先扫地抹桌,生火烧水,听见掌柜在穿衣,赶紧去给掌柜倒尿盆。如此不停不歇,熬了三年,才上了柜台,也就是真正开始学生意了。昝家的规矩,不论掌柜伙计,五年才能回家一次。石丁山要攒钱娶媳妇,七年后才回家。回家路上要走三个月,一个来回是半年,在家住半年,加起来是一年。回家头件事是交账,把挣的钱一袋子交给父亲。父亲拿到钱,赶紧张罗给儿子成亲。五年后石丁山再回来,儿子已经四岁了。会过诸亲友,天色已晚,该就寝了,做父亲的要上炕,四岁的儿子不让,手持笤帚疙瘩站在炕头怒目喝道:哪来的汉子,不许上我妈的炕!夫妻俩先是笑,继而无语。不觉间半年假满,又要上路了。半年里妻子夜夜加班纳鞋,这时便作一包袱裹好,送丈夫上路。路漫漫其修远,又多是山路,啥时一包袱的鞋都穿烂了,川西的店铺也就到了。
石丁山为什么要从昝家辞职,回乡做二财主,没人说得清。回来后,先是到吕梁山上开煤矿,是与人合伙开的,他是合伙人兼掌柜。从来煤矿都讲究通风,老法子是用扇麦的扇车。踩扇车的都是壮小伙子,两人一班,一个时辰换个班。石丁山开风气之先,用锅驼机排风。锅驼机现在不见了,被淘汰几十年了,那时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机器一响,风如雷吼,见者无不惊诧。开锅驼机的是高薪请来的技师,技师发动机器后便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喝茶抽烟吃糕点,一左一右站着两个花姑娘,手持团扇轻轻扇风。我们村有几个人在煤矿干过活,我爹是其中之一,见过那场面。煤矿很赚过一阵子钱,后来因为冒水停办,石丁山又干了一阵子布匹生意。
石丁山的特别处,是从来不把钱财当一回事。所作善事甚多,若作总结报告,有如下几条突出事迹:一、他家牲畜多,左邻右舍时常借用,石丁山不想让大家看他的脸色,索性买了两头牛一头驴,每天早晨由长工拴在池塘边的老槐树下,随便谁家想用就用,用完了仍拴在原处即可。二、他家地多粮亦多,青黄不接时免不了有人上门告借,石丁山有求必应,不但不计利息,反而倒贴。倒贴的方式,是粮库里有一大一小两个斗,借出粮食用大斗,收回粮食用小斗。三、村中有几个鳏寡孤独,瓮里无粮却没胆子开口求借,石丁山会主动打发长工送去粮食。四、从不拿财主架子,心胸宽阔,待人和善。比如夏收拾麦,割过的麦地当然可拾,但总得等人家割完运完,才可进地。石家的麦地则不然,前边长工短工还在挥镰收割,后边拾麦的就跟上了。一般拾下的麦子总是参差不齐,麦穗大小不一,这里拾下的麦子却齐刷刷一把又一把,一看而知是从麦堆里抽出来的。长工老高就先看不过眼,建议管一管。石丁山说:他们拿的再多也是背,咱们是大车拉,能搬过咱们吗?反倒常常鼓励拾麦的老弱妇孺道:好好拾,渴了那边有水,饿了有馍!好像是到他家作客。
石丁山的特别处,是从来不把钱财当一回事。所作善事甚多,若作总结报告,有如下几条突出事迹:一、他家牲畜多,左邻右舍时常借用,石丁山不想让大家看他的脸色,索性买了两头牛一头驴,每天早晨由长工拴在池塘边的老槐树下,随便谁家想用就用,用完了仍拴在原处即可。二、他家地多粮亦多,青黄不接时免不了有人上门告借,石丁山有求必应,不但不计利息,反而倒贴。倒贴的方式,是粮库里有一大一小两个斗,借出粮食用大斗,收回粮食用小斗。三、村中有几个鳏寡孤独,瓮里无粮却没胆子开口求借,石丁山会主动打发长工送去粮食。四、从不拿财主架子,心胸宽阔,待人和善。比如夏收拾麦,割过的麦地当然可拾,但总得等人家割完运完,才可进地。石家的麦地则不然,前边长工短工还在挥镰收割,后边拾麦的就跟上了。一般拾下的麦子总是参差不齐,麦穗大小不一,这里拾下的麦子却齐刷刷一把又一把,一看而知是从麦堆里抽出来的。长工老高就先看不过眼,建议管一管。石丁山说:他们拿的再多也是背,咱们是大车拉,能搬过咱们吗?反倒常常鼓励拾麦的老弱妇孺道:好好拾,渴了那边有水,饿了有馍!好像是到他家作客。
石丁山志在经商,但鬼子来了,天下财主都不免穷途末路,他也丢下生意逃难到西安,抗战胜利后才回来。回来名义上还是二财主,却已有名无实了,只剩百十亩地了。不久土改,他家给定了地主,那是政策,不定不行,但没一个人要斗争他,全村人都千方百计保护他。村里斗争会开过好几次,先打死一个叫李长发的汉奸,接着斗争李旺财,差点没给打死。石丁山却自管坐在家里抽水烟,连斗争会也没参加过一次。大家伙儿都似乎忘了他。至今我们村里人聊起闲话,李旺财还是笑柄,对于石丁山,大家都还是感念不已。
@竹素园主人
野老谝闲之第十篇
二 财主
民国年间我们村有两个财主。一个是李旺财。李旺财做庄稼是全把式,还是个顶呱呱的好木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干木活;木活干到深夜,打个盹,不等天亮就又上地。上集赶会大家都不愿和他相跟,走着走着就站住不动——睡着了。一盒火柴要用一年,还常年吃糠咽菜。他说:吃的再好顶啥用?到肚里还不都成了屎!而且吝啬,左邻右舍二斗麦也不借。拼死拼活,最终置地七十多亩,放过贷,雇过工,正好戴个地主帽子。
和李旺财隔一条巷子的还有一家财主,大号石丁山,人称二财主。之所以称二财主,是因为他是由大财主派生出来的财主,就好比是一棵大树分出来的枝杈。虽是枝杈,因为那树太大,枝杈也就很可观。二财主石丁山在我们村是首富,出了村也叫得响,但和他的东家昝家比起来就差远了,昝家才是方圆几十里的头号大财主。
咱就说说昝家吧。昝家家住昝家沟,几辈子都在川西做麝香生意——从藏民那里收购麝香,拿到成都卖掉,再采购回些绸缎布匹茶叶之类在藏区出售,做两头生意。世代于兹,经验老到,麝香一沾手就分优劣,出价也公道,信誉卓著,生意兴隆,分店很多。石丁山是某个分店的掌柜,类似现在的二级经理。昝家的老祖宗是怎样从一个穷山沟一直跑到遥远的川西的,已无从考证。要之,那时的生意人都跑得远,而且似乎跑得越远那生意便越火,发财也越大,有胆量跑到国外的,自会是沈万三式的国际大财主。
至今人们说到昝家,还会提到昝家老爷子做寿那回。那还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去看热闹,我爷爷我奶奶也去了。场面之大之豪华已无人能说得清了,说得清的只是几个断片。
断片一:两根红蜡烛足有一人高,木桶粗,上边还刻着龙啊凤啊之类图案,栩栩如生。烛捻子胳膊粗,烛火一尺高,若在上面搭口锅,顷刻可烧开一锅水。
断片二:白银制作的“麻姑献寿”真人大小,放在庙里可以当神敬,但比庙里的神像更像神,据说是四川的一个什么大人物送的贺礼。
断片三:唱了三天大戏,请的都是晋南最走红的戏班子,唱的是对台戏,琼才的《挂画》就是那回出名的。
断片四:还请了几班乐人,远近闻名的吹鼓手齐聚一堂,无异冠军大赛,高手们各显神通,竞奇斗艳,有的竟会两个鼻孔吹唢呐。
由残片而窥全貌,那时无疑是昝家的鼎盛时期。后来洪杨造反,昝家元气大伤;再后来军阀混战,更是江河日下;待到抗战前期昝家已沦为小本生意人了。建国后还有人在成都见过昝家的大东家,是在街头摆烟摊。到那个地步仍未回乡,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还是已将客乡作故乡了?不得而知。
野老谝闲之第十篇
二 财主
民国年间我们村有两个财主。一个是李旺财。李旺财做庄稼是全把式,还是个顶呱呱的好木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干木活;木活干到深夜,打个盹,不等天亮就又上地。上集赶会大家都不愿和他相跟,走着走着就站住不动——睡着了。一盒火柴要用一年,还常年吃糠咽菜。他说:吃的再好顶啥用?到肚里还不都成了屎!而且吝啬,左邻右舍二斗麦也不借。拼死拼活,最终置地七十多亩,放过贷,雇过工,正好戴个地主帽子。
和李旺财隔一条巷子的还有一家财主,大号石丁山,人称二财主。之所以称二财主,是因为他是由大财主派生出来的财主,就好比是一棵大树分出来的枝杈。虽是枝杈,因为那树太大,枝杈也就很可观。二财主石丁山在我们村是首富,出了村也叫得响,但和他的东家昝家比起来就差远了,昝家才是方圆几十里的头号大财主。
咱就说说昝家吧。昝家家住昝家沟,几辈子都在川西做麝香生意——从藏民那里收购麝香,拿到成都卖掉,再采购回些绸缎布匹茶叶之类在藏区出售,做两头生意。世代于兹,经验老到,麝香一沾手就分优劣,出价也公道,信誉卓著,生意兴隆,分店很多。石丁山是某个分店的掌柜,类似现在的二级经理。昝家的老祖宗是怎样从一个穷山沟一直跑到遥远的川西的,已无从考证。要之,那时的生意人都跑得远,而且似乎跑得越远那生意便越火,发财也越大,有胆量跑到国外的,自会是沈万三式的国际大财主。
至今人们说到昝家,还会提到昝家老爷子做寿那回。那还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去看热闹,我爷爷我奶奶也去了。场面之大之豪华已无人能说得清了,说得清的只是几个断片。
断片一:两根红蜡烛足有一人高,木桶粗,上边还刻着龙啊凤啊之类图案,栩栩如生。烛捻子胳膊粗,烛火一尺高,若在上面搭口锅,顷刻可烧开一锅水。
断片二:白银制作的“麻姑献寿”真人大小,放在庙里可以当神敬,但比庙里的神像更像神,据说是四川的一个什么大人物送的贺礼。
断片三:唱了三天大戏,请的都是晋南最走红的戏班子,唱的是对台戏,琼才的《挂画》就是那回出名的。
断片四:还请了几班乐人,远近闻名的吹鼓手齐聚一堂,无异冠军大赛,高手们各显神通,竞奇斗艳,有的竟会两个鼻孔吹唢呐。
由残片而窥全貌,那时无疑是昝家的鼎盛时期。后来洪杨造反,昝家元气大伤;再后来军阀混战,更是江河日下;待到抗战前期昝家已沦为小本生意人了。建国后还有人在成都见过昝家的大东家,是在街头摆烟摊。到那个地步仍未回乡,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还是已将客乡作故乡了?不得而知。
再说石丁山。
石丁山十三岁就到四川,在昝家的店铺里熬相公,就是做学徒。那时农家子弟读书的少,条件好点的,读书也不过数年,能识的几个字,记的几笔帐,就要自谋生路了。家里地多能自給的,就安安稳稳种地,是为上选;否则就得投门子学点吃饭的本事。熬相公是选择之一,很苦,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熬得上的。石丁山和昝家沾点瓜蔓亲,才获此机会。十三岁的孩子,是如何跋山涉水几千里到四川的?无法想象。去时背个铺盖卷,人小铺盖更小,小得盖不住脚,睡觉时便用根麻绳把被头捆住。不过人聪明,也吃的苦。掌柜晚上要算账,睡得迟,小丁山总要侍候掌柜就寝才休息。鸡叫头遍就起床,先扫地抹桌,生火烧水,听见掌柜在穿衣,赶紧去给掌柜倒尿盆。如此不停不歇,熬了三年,才上了柜台,也就是真正开始学生意了。
昝家的规矩,不论掌柜伙计,五年才能回家一次。石丁山要攒钱娶媳妇,七年后才回家。回家路上要走三个月,一个来回是半年,在家住半年,加起来是一年。回家头件事是交账,把挣的钱一袋子交给父亲。父亲拿到钱,赶紧张罗给儿子成亲。五年后石丁山再回来,儿子已经四岁了。会过诸亲友,天色已晚,该就寝了,做父亲的要上炕,四岁的儿子不让,手持笤帚疙瘩站在炕头怒目喝道:哪来的汉子,不许上我妈的炕!夫妻俩先是笑,继而无语。
不觉间半年假满,又要上路了。半年里妻子夜夜加班纳鞋,这时便作一包袱裹好,送丈夫上路。路漫漫其修远,又多是山路,啥时一包袱的鞋都穿烂了,川西的店铺也就到了。
石丁山为什么要从昝家辞职,回乡做二财主,没人说得清。回来后,先是到吕梁山上开煤矿,是与人合伙开的,他是合伙人兼掌柜。从来煤矿都讲究通风,老法子是用扇麦的扇车。踩扇车的都是壮小伙子,两人一班,一个时辰换个班。石丁山开风气之先,用锅驼机排风。锅驼机现在不见了,被淘汰几十年了,那时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机器一响,风如雷吼,见者无不惊诧。开锅驼机的是高薪请来的技师,技师发动机器后便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喝茶抽烟吃糕点,一左一右站着两个花姑娘,手持团扇轻轻扇风。我们村有几个人在煤矿干过活,我爹是其中之一,见过那场面。煤矿很赚过一阵子钱,后来因为冒水停办,石丁山又干了一阵子布匹生意。
石丁山的特别处,是从来不把钱财当一回事。所作善事甚多,若作总结报告,有如下几条突出事迹:
一、他家牲畜多,左邻右舍时常借用,石丁山不想让大家看他的脸色,索性买了两头牛一头驴,每天早晨由长工拴在池塘边的老槐树下,随便谁家想用就用,用完了仍拴在原处即可。
二、他家地多粮亦多,青黄不接时免不了有人上门告借,石丁山有求必应,不但不计利息,反而倒贴。倒贴的方式,是粮库里有一大一小两个斗,借出粮食用大斗,收回粮食用小斗。
三、村中有几个鳏寡孤独,瓮里无粮却没胆子开口求借,石丁山会主动打发长工送去粮食。
四、从不拿财主架子,心胸宽阔,待人和善。比如夏收拾麦,割过的麦地当然可拾,但总得等人家割完运完,才可进地。石家的麦地则不然,前边长工短工还在挥镰收割,后边拾麦的就跟上了。一般拾下的麦子总是参差不齐,麦穗大小不一,这里拾下的麦子却齐刷刷一把又一把,一看而知是从麦堆里抽出来的。长工老高就先看不过眼,建议管一管。石丁山说:他们拿的再多也是背,咱们是大车拉,能搬过咱们吗?反倒常常鼓励拾麦的老弱妇孺道:好好拾,渴了那边有水,饿了有馍!好像是到他家作客。
石丁山志在经商,但鬼子来了,天下财主都不免穷途末路,他也丢下生意逃难到西安,抗战胜利后才回来。回来名义上还是二财主,却已有名无实了,只剩百十亩地了。不久土改,他家给定了地主,那是政策,不定不行,但没一个人要斗争他,全村人都千方百计保护他。村里斗争会开过好几次,先打死一个叫李长发的汉奸,接着斗争李旺财,差点没给打死。石丁山却自管坐在家里抽水烟,连斗争会也没参加过一次。大家伙儿都似乎忘了他。至今我们村里人聊起闲话,李旺财还是笑柄,对于石丁山,大家都还是感念不已。
@竹素园主人
各位朋友大力支持本帖,多谢!读帖之余,赏赏礼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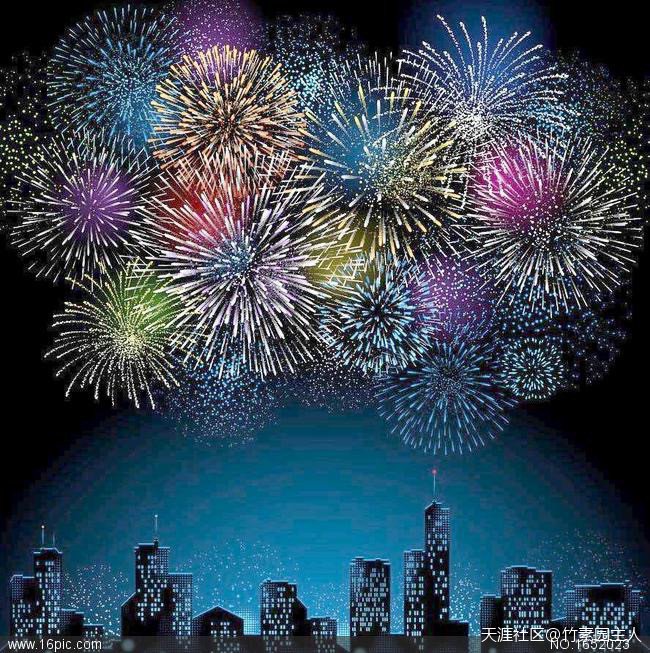
各位朋友大力支持本帖,多谢!读帖之余,赏赏礼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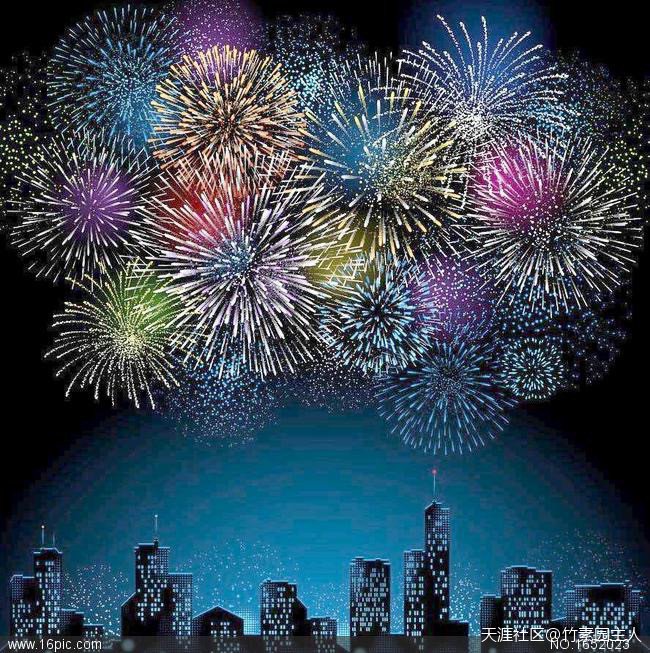
野老谝闲之第十一篇
捞 媳 妇
许多年前我们村有个穷汉,姓吴,年近三十还是光棍一条,而且脾气古怪,说话做事罔顾常规,人便说他八成不够,七成勉强,便叫他吴老七。其实吴老七也不是一无所长,有时还可以说是粗中有细。比如种葫芦。葫芦谁也会种,但吴老七的葫芦与众不同,是那种能盛一斗谷子的大葫芦。这么大的葫芦如今已难见到了,当年老七家的屋梁上就挂那么两个,是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葫芦里盛的是谷子,相当于一个迷你谷仓,是防饥荒的。之所以高高挂起来,是为了防潮,更为防鼠。
每年开春,吴老七都要在自家院子的北墙根种一溜儿葫芦,待葫芦蔓长到五六尺长,就每五棵扭成一股,嫁接到了一起。五条根供一条藤,而且只留一个葫芦,那葫芦自然会长得很大很大。光大还不行,还要厚,才能承重.办法是每日都要捧着葫芦上下左右摩挲一番,远看就像练什么拳法。其间浇水施肥,蹲苗打掐,都有拿法,是为家传秘籍。
吴老七的葫芦很有名,一斗麦子一个,多年行情不变。大葫芦还是摆渡器材,四个葫芦捆成一副筏子,可以载一个人过黄河。
吴老七另一特长是水性好。我们村距离黄河三十多里地,不算近,也不算太远。吴老七舅舅家在黄河边,从小爱在那里玩,长大后就在黄河上混日子,做“背客”。
何谓背客?就是背着客人过黄河的苦力。
黄河的河岸摇摆不定,码头无从建设,乘船过河,上船下船都要涉水。男人好说,挽起裤腿蹚过去就是。女人就不行,小脚尖尖如锥子,扎进去容易拔出来难,所以必须请人背。如果是盛夏,背客们都赤条条一线不挂(此乃风俗,流传已久),和刚从他妈肚子里生出来一样,大姑娘小媳妇怎不尴尬?然而再尴尬,也只能请他们背,还要花钱。
捞 媳 妇
许多年前我们村有个穷汉,姓吴,年近三十还是光棍一条,而且脾气古怪,说话做事罔顾常规,人便说他八成不够,七成勉强,便叫他吴老七。其实吴老七也不是一无所长,有时还可以说是粗中有细。比如种葫芦。葫芦谁也会种,但吴老七的葫芦与众不同,是那种能盛一斗谷子的大葫芦。这么大的葫芦如今已难见到了,当年老七家的屋梁上就挂那么两个,是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葫芦里盛的是谷子,相当于一个迷你谷仓,是防饥荒的。之所以高高挂起来,是为了防潮,更为防鼠。
每年开春,吴老七都要在自家院子的北墙根种一溜儿葫芦,待葫芦蔓长到五六尺长,就每五棵扭成一股,嫁接到了一起。五条根供一条藤,而且只留一个葫芦,那葫芦自然会长得很大很大。光大还不行,还要厚,才能承重.办法是每日都要捧着葫芦上下左右摩挲一番,远看就像练什么拳法。其间浇水施肥,蹲苗打掐,都有拿法,是为家传秘籍。
吴老七的葫芦很有名,一斗麦子一个,多年行情不变。大葫芦还是摆渡器材,四个葫芦捆成一副筏子,可以载一个人过黄河。
吴老七另一特长是水性好。我们村距离黄河三十多里地,不算近,也不算太远。吴老七舅舅家在黄河边,从小爱在那里玩,长大后就在黄河上混日子,做“背客”。
何谓背客?就是背着客人过黄河的苦力。
黄河的河岸摇摆不定,码头无从建设,乘船过河,上船下船都要涉水。男人好说,挽起裤腿蹚过去就是。女人就不行,小脚尖尖如锥子,扎进去容易拔出来难,所以必须请人背。如果是盛夏,背客们都赤条条一线不挂(此乃风俗,流传已久),和刚从他妈肚子里生出来一样,大姑娘小媳妇怎不尴尬?然而再尴尬,也只能请他们背,还要花钱。
背客的收入其实微薄且不固定,乐此不疲的大抵是些穷光棍。这些光棍双目炯炯,遇到大姑娘小媳妇就一拥而上。年轻女客上背,背客的双手起先还正人君子般很规矩,从背后托着女客屈起的膝盖。然而没走几步,一个趔趄,似乎是有大浪打来,要被河水冲倒似的,就在女客的惊叫声中,那双手不觉间就转移了位置,抓住了女客的大腿,上下其手起来;又蹒跚其步,迟迟其行,延长这个过程。被占了便宜的女客无可奈何,只能佯作不知,待到上岸常常面红耳赤头晕目眩站脚不稳。竟也有由此与背客挂上关系的。吴老七从事的就是这么一种职业,女人的大腿自然是摸过无数,然而也仅此而已。
吴老七穷得弹壁无灰,扫地无土,但找媳妇还很挑剔,不漂亮不要。但只要漂亮,则其余不问。这应该是他年近三十依旧光棍一条的原因。当然原因还有,比如穷。
然而运气不久来了。
那天吴老七又到黄河边背客,遇到一个熟人,说起闲话来,知道他姨姨的女婿,就是他的表姐夫,在西安做生意发了财。表姐夫原本也是穷光蛋一个,他能发财,老七为何不能呢?吴老七便拿定主意要到西安去,去投奔表姐,改变穷困命运。没盘缠,怎么办?老七屋里屋外看个遍,唯有一坛泡柿子(其作法类似四川榨菜)可以变现。时值盛夏,酸酸的泡柿子也正好上市。老七把泡柿子放进两个木桶里,再把坛子里的酸水倒满木桶,再拿两块布蒙住桶口,捆好,做一担担了上路。
盘算得很好:一边赶路一边卖柿子,买卖也做了,路也赶了。起身那天又特意拐了几个弯子,多跑了几个村庄,边走边吆喝,一直吆喝到黄河边。结果很不理想,一文钱一个的泡柿子只卖了四五个。只得担着担子上了渡船。船老大都是熟人,船钱可免。等了一个时辰,一船人坐满了,便开船。
吴老七穷得弹壁无灰,扫地无土,但找媳妇还很挑剔,不漂亮不要。但只要漂亮,则其余不问。这应该是他年近三十依旧光棍一条的原因。当然原因还有,比如穷。
然而运气不久来了。
那天吴老七又到黄河边背客,遇到一个熟人,说起闲话来,知道他姨姨的女婿,就是他的表姐夫,在西安做生意发了财。表姐夫原本也是穷光蛋一个,他能发财,老七为何不能呢?吴老七便拿定主意要到西安去,去投奔表姐,改变穷困命运。没盘缠,怎么办?老七屋里屋外看个遍,唯有一坛泡柿子(其作法类似四川榨菜)可以变现。时值盛夏,酸酸的泡柿子也正好上市。老七把泡柿子放进两个木桶里,再把坛子里的酸水倒满木桶,再拿两块布蒙住桶口,捆好,做一担担了上路。
盘算得很好:一边赶路一边卖柿子,买卖也做了,路也赶了。起身那天又特意拐了几个弯子,多跑了几个村庄,边走边吆喝,一直吆喝到黄河边。结果很不理想,一文钱一个的泡柿子只卖了四五个。只得担着担子上了渡船。船老大都是熟人,船钱可免。等了一个时辰,一船人坐满了,便开船。
如今过黄河再不用坐渡船了,太方便了,但也失去了体会惊涛骇浪的机会。那渡船我坐过几次,很是惊心动魄。偌大渡船,一到河心,忽成一叶扁舟,忽上忽下,摇摆不定。船夫们一边扳桨,一边嗨哟嗨哟喊着号子。那声音很恐怖,据说是故意惊吓客人,以便减轻渡船的重量。但老七例外,他敢在大浪里游泳,何况坐船乎?他只是想着快点上岸赶路。
可是,船还在河心,船两侧的浪还是那么高,摇摆不定的渡船却突然安如泰山,纹丝不动了。船夫们也不唱恐怖的号子了,只是惊慌地四顾。怎么回事呢?
原来,船搁浅了,铆在河心动不了了!
奇怪,渡船怎么会在浪涛滚滚的河心搁浅呢?这事儿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都使人莫名惊诧,但在黄河里却是见惯不惊。
原来,黄河的河床由泥沙铺就,等于是条布满沙丘的水下沙漠。沙漠里的沙丘在浪涛的剧烈冲刷下不断滚动,变幻莫测,正是俗谚所谓的“黄河没底海没岸”——不是深得没底,而是没个固定不变的底。吴老七的渡船阴差阳错,恰被一个流动过来的沙丘顶了起来。
可是,船还在河心,船两侧的浪还是那么高,摇摆不定的渡船却突然安如泰山,纹丝不动了。船夫们也不唱恐怖的号子了,只是惊慌地四顾。怎么回事呢?
原来,船搁浅了,铆在河心动不了了!
奇怪,渡船怎么会在浪涛滚滚的河心搁浅呢?这事儿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都使人莫名惊诧,但在黄河里却是见惯不惊。
原来,黄河的河床由泥沙铺就,等于是条布满沙丘的水下沙漠。沙漠里的沙丘在浪涛的剧烈冲刷下不断滚动,变幻莫测,正是俗谚所谓的“黄河没底海没岸”——不是深得没底,而是没个固定不变的底。吴老七的渡船阴差阳错,恰被一个流动过来的沙丘顶了起来。
吴老七在黄河边长大,知道黄河的脾气,比如船家晚上把船泊在河湾,睡一觉醒来,船竟给高高撂在沙滩上,远离了河道;比如某人在河滩地种了庄稼,眼看要成熟了,某天早上,却发现他的庄稼连同土地,被大河隔断在河对岸,如此等等。但渡船被搁浅在河心,吴老七也还是头一次见到。以吴老七的水性,完全可以跳下船游到对岸,然而却舍不得那一担泡柿子。
渡口再没有第二艘船,无从救援。众乘客长吁短叹着等到天黑,接着又等了一夜,船还是不动。待到次日中午,好大好毒的太阳挂在头顶,乘客们就如鱼干似的烤着,不免饥渴起来。吴老七吃了一口干馍,又喝了一口泡柿子水解渴。这提醒了乘客们,立即伸过几只手来。顾客上门,吴老七欢迎,然而柿子一角一个,柿子水一角一勺,一文不能少。伸过来的手又缩了回去。
熬到下午,人都快给烤干了,终于有人拿出铜元来要与老七交易,老七却不干了:柿子一元一个,柿子水一元一勺。愿买愿卖,公平交易。
老七赢了,一枚枚铮亮的银元递到了手上。又熬一天,柿子和柿子水存货不多了,于是继续涨价,走货依旧顺畅。最后两桶泡柿子变成了半桶银元,这时船也移动了。
吴老七大喜,也不去西安了,返身渡河回家。次日便有人给老七提亲,老七笑而不答。
原来老七早相中了一个漂亮女子,是三十五里外北常庄的一位姑娘,名叫常翠叶。
有人问:老七,你咋认识那个常翠叶的?
老七不羞不臊道:背客嘛,还能咋认识?前阵子背她下船,我拧她屁股,她拧我耳朵,她还说你要爱见我,就来娶我,娶到你家里天天由你摸。前头咱有心无力,这阵行了!
大家窃笑,便到常家庄。找熟人一打听,确有常翠叶其人,二十三岁,好人样,原先嫁给一家财主,因婚外情被休,已晾在娘家一年多了。大家知道老七只要漂亮,不问其余,就去登门提亲,不料却被一口回绝。
原来老七虽然名噪黄河两岸,爱摸女人大腿却是主要内容,发浑财一事虽然也震动一时,却由此似乎更加臭名远扬。背客那么多,等同都是摸,为何老七一人成名?想来是那双摸葫芦的手功夫太深之故吧。姑且存疑待考。
媒人们泄气而归,向老七汇报了。老七抱怨道:你们找她爹妈干啥,咋不找翠叶呢?
大家笑道:那你干脆直接去找不是得了?
老七想想有道理,就做了崭新一身衣服,戴了礼帽,借了一匹高头大马,骑着去了北常庄。进的村,一路问询,在翠叶家门前栓了马,提了马鞭就进门。进门就喊:翠叶翠叶!
渡口再没有第二艘船,无从救援。众乘客长吁短叹着等到天黑,接着又等了一夜,船还是不动。待到次日中午,好大好毒的太阳挂在头顶,乘客们就如鱼干似的烤着,不免饥渴起来。吴老七吃了一口干馍,又喝了一口泡柿子水解渴。这提醒了乘客们,立即伸过几只手来。顾客上门,吴老七欢迎,然而柿子一角一个,柿子水一角一勺,一文不能少。伸过来的手又缩了回去。
熬到下午,人都快给烤干了,终于有人拿出铜元来要与老七交易,老七却不干了:柿子一元一个,柿子水一元一勺。愿买愿卖,公平交易。
老七赢了,一枚枚铮亮的银元递到了手上。又熬一天,柿子和柿子水存货不多了,于是继续涨价,走货依旧顺畅。最后两桶泡柿子变成了半桶银元,这时船也移动了。
吴老七大喜,也不去西安了,返身渡河回家。次日便有人给老七提亲,老七笑而不答。
原来老七早相中了一个漂亮女子,是三十五里外北常庄的一位姑娘,名叫常翠叶。
有人问:老七,你咋认识那个常翠叶的?
老七不羞不臊道:背客嘛,还能咋认识?前阵子背她下船,我拧她屁股,她拧我耳朵,她还说你要爱见我,就来娶我,娶到你家里天天由你摸。前头咱有心无力,这阵行了!
大家窃笑,便到常家庄。找熟人一打听,确有常翠叶其人,二十三岁,好人样,原先嫁给一家财主,因婚外情被休,已晾在娘家一年多了。大家知道老七只要漂亮,不问其余,就去登门提亲,不料却被一口回绝。
原来老七虽然名噪黄河两岸,爱摸女人大腿却是主要内容,发浑财一事虽然也震动一时,却由此似乎更加臭名远扬。背客那么多,等同都是摸,为何老七一人成名?想来是那双摸葫芦的手功夫太深之故吧。姑且存疑待考。
媒人们泄气而归,向老七汇报了。老七抱怨道:你们找她爹妈干啥,咋不找翠叶呢?
大家笑道:那你干脆直接去找不是得了?
老七想想有道理,就做了崭新一身衣服,戴了礼帽,借了一匹高头大马,骑着去了北常庄。进的村,一路问询,在翠叶家门前栓了马,提了马鞭就进门。进门就喊:翠叶翠叶!
不料翠叶不在家,翠叶爹出屋应客,一问是吴老七,拿扁担就打。老七落荒而逃,跑出好远才想起是骑马来的,又大着胆子回头牵了马,丧魂落魄回到家。
大家劝老七另择高配,但老七就是不放弃,一连多日躺在炕上犯相思。这天枕头下似乎发出呼呼的响声,隐隐约约,像刮大风,又像地底下滚过来许多碌碡。老七下意识地跳下炕,往黄河边跑。还没到河边,就听见轰轰轰的波涛声,果然黄河发大水了,路上的男男女女正一缕一缕正往河边赶。
此时黄河摇身一变,海一样浩渺起来。说两岸不辨牛马,那是水面窄些的地方;水面宽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到河对岸。浑黄的水面上,远远近近,星星点点,是什么?是两岸的男女们,正泡在水里捞浮财。
捞浮财也叫捞浮柴,有点分不清,是沿河百姓的一种生存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风俗习惯。往往全家出动,一律赤条条泡进水里,公公儿媳也不回避。为何要赤条条呢?黄河水泥沙太大,有如液体砂轮,再结实的衣服也经不起冲刷。为了爱惜衣着,只好减少些礼仪了。
吴老七爱看这道风景,历年都是捞浮柴的积极分子。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还为了要发财。
发什么财?那要看运气。一般而论,捞些浮柴或烟碳是没问题的。这些木柴和烟碳当然是从河上游冲下来的,数量往往很大,捞不完。冲下来的也不仅仅限于木柴煤炭,运气好,碰上一头猪,一只羊,也和正常。甚至有人捞到过一箱子银元,还有人截住了一艘无主木船,船上还装满了布匹——诸如此类,有时难辨真伪,但影响力极大。
这天老七脱了衣服,有一搭没一搭在河里走。水越来越深,走着走着就漂起来了,就游。也不知游了多长时间,忽觉水流激荡起来,一看,已经离岸很远,快到河心了。
大家劝老七另择高配,但老七就是不放弃,一连多日躺在炕上犯相思。这天枕头下似乎发出呼呼的响声,隐隐约约,像刮大风,又像地底下滚过来许多碌碡。老七下意识地跳下炕,往黄河边跑。还没到河边,就听见轰轰轰的波涛声,果然黄河发大水了,路上的男男女女正一缕一缕正往河边赶。
此时黄河摇身一变,海一样浩渺起来。说两岸不辨牛马,那是水面窄些的地方;水面宽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到河对岸。浑黄的水面上,远远近近,星星点点,是什么?是两岸的男女们,正泡在水里捞浮财。
捞浮财也叫捞浮柴,有点分不清,是沿河百姓的一种生存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风俗习惯。往往全家出动,一律赤条条泡进水里,公公儿媳也不回避。为何要赤条条呢?黄河水泥沙太大,有如液体砂轮,再结实的衣服也经不起冲刷。为了爱惜衣着,只好减少些礼仪了。
吴老七爱看这道风景,历年都是捞浮柴的积极分子。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还为了要发财。
发什么财?那要看运气。一般而论,捞些浮柴或烟碳是没问题的。这些木柴和烟碳当然是从河上游冲下来的,数量往往很大,捞不完。冲下来的也不仅仅限于木柴煤炭,运气好,碰上一头猪,一只羊,也和正常。甚至有人捞到过一箱子银元,还有人截住了一艘无主木船,船上还装满了布匹——诸如此类,有时难辨真伪,但影响力极大。
这天老七脱了衣服,有一搭没一搭在河里走。水越来越深,走着走着就漂起来了,就游。也不知游了多长时间,忽觉水流激荡起来,一看,已经离岸很远,快到河心了。
老七吃了一惊。在惊涛骇浪里游泳,不是不敢,毕竟风险很大,还是回避为好。
老七正要回头,却隐隐约约似乎有人喊救命,而且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这对老七吸引力极大,就极目望去。只见河上游飘下来一个麦秸堆,麦秸堆上坐着个穿红袄的姑娘。那麦秸堆也不知在洪流里漂流了多长时间,眼见着只露出坟头大一个顶子,就要沉入洪流了。然而两岸的人只顾发浑财哪顾得上救人,再说谁有胆量扑到河心里去呢?
老七本不想理会,脑子里却突然划过一道闪电:那女子是不是翠叶呢?于是又望过去,看呀看,有点像,而且越看越像。老七于是一个猛子扑向洪流,在惊涛骇浪间沉沉浮浮,浮浮沉沉,随波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少里,终于靠近了麦秸积,抬头一看,上面坐着的果真是翠叶!
原来,翠叶在娘家住了一年多,哥嫂越来越嫌弃,成日风言风语,这都罢了;老七把她在黄河边的风流话也抖了出去,这丑事不胫而走,很快就飞到北常庄,更弄得翠叶没法见人了,于是索性跳河自尽。落水后又有点后悔,凑巧一个麦秸积漂过来,便爬了上去。真是天缘凑巧,这一爬竟爬上了老七面前。
当下老七大喜,喊:翠叶,哥救你来了!
翠叶也认出了老七,哭喊:哥,救我啊!
老七推着麦秸积向岸边靠,水太急,麦秸堆体积又大,怎么也推不动。眨眼间麦秸堆也给打散了,老七不敢耽误,奋力一跃,将落水的翠叶夹在腋窝下。翠叶呢,那顾得了许多,就拦腰抱住赤裸裸的老七。俩人也不知被巨浪吞没了多少回,喝了多少次水,做了多少回拼死挣扎,侥天之幸,竟突破千难万险,上了河岸。
老七正要回头,却隐隐约约似乎有人喊救命,而且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这对老七吸引力极大,就极目望去。只见河上游飘下来一个麦秸堆,麦秸堆上坐着个穿红袄的姑娘。那麦秸堆也不知在洪流里漂流了多长时间,眼见着只露出坟头大一个顶子,就要沉入洪流了。然而两岸的人只顾发浑财哪顾得上救人,再说谁有胆量扑到河心里去呢?
老七本不想理会,脑子里却突然划过一道闪电:那女子是不是翠叶呢?于是又望过去,看呀看,有点像,而且越看越像。老七于是一个猛子扑向洪流,在惊涛骇浪间沉沉浮浮,浮浮沉沉,随波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少里,终于靠近了麦秸积,抬头一看,上面坐着的果真是翠叶!
原来,翠叶在娘家住了一年多,哥嫂越来越嫌弃,成日风言风语,这都罢了;老七把她在黄河边的风流话也抖了出去,这丑事不胫而走,很快就飞到北常庄,更弄得翠叶没法见人了,于是索性跳河自尽。落水后又有点后悔,凑巧一个麦秸积漂过来,便爬了上去。真是天缘凑巧,这一爬竟爬上了老七面前。
当下老七大喜,喊:翠叶,哥救你来了!
翠叶也认出了老七,哭喊:哥,救我啊!
老七推着麦秸积向岸边靠,水太急,麦秸堆体积又大,怎么也推不动。眨眼间麦秸堆也给打散了,老七不敢耽误,奋力一跃,将落水的翠叶夹在腋窝下。翠叶呢,那顾得了许多,就拦腰抱住赤裸裸的老七。俩人也不知被巨浪吞没了多少回,喝了多少次水,做了多少回拼死挣扎,侥天之幸,竟突破千难万险,上了河岸。
老七吃了一惊。在惊涛骇浪里游泳,不是不敢,毕竟风险很大,还是回避为好。
老七正要回头,却隐隐约约似乎有人喊救命,而且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这对老七吸引力极大,就极目望去。只见河上游飘下来一个麦秸堆,麦秸堆上坐着个穿红袄的姑娘。那麦秸堆也不知在洪流里漂流了多长时间,眼见着只露出坟头大一个顶子,就要沉入洪流了。然而两岸的人只顾发浑财哪顾得上救人,再说谁有胆量扑到河心里去呢?
老七本不想理会,脑子里却突然划过一道闪电:那女子是不是翠叶呢?于是又望过去,看呀看,有点像,而且越看越像。老七于是一个猛子扑向洪流,在惊涛骇浪间沉沉浮浮,浮浮沉沉,随波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少里,终于靠近了麦秸积,抬头一看,上面坐着的果真是翠叶!
原来,翠叶在娘家住了一年多,哥嫂越来越嫌弃,成日风言风语,这都罢了;老七把她在黄河边的风流话也抖了出去,这丑事不胫而走,很快就飞到北常庄,更弄得翠叶没法见人了,于是索性跳河自尽。落水后又有点后悔,凑巧一个麦秸积漂过来,便爬了上去。真是天缘凑巧,这一爬竟爬上了老七面前。
当下老七大喜,喊:翠叶,哥救你来了!
翠叶也认出了老七,哭喊:哥,救我啊!
老七推着麦秸积向岸边靠,水太急,麦秸堆体积又大,怎么也推不动。眨眼间麦秸堆也给打散了,老七不敢耽误,奋力一跃,将落水的翠叶夹在腋窝下。翠叶呢,那顾得了许多,就拦腰抱住赤裸裸的老七。俩人也不知被巨浪吞没了多少回,喝了多少次水,做了多少回拼死挣扎,侥天之幸,竟突破千难万险,上了河岸。
老七正要回头,却隐隐约约似乎有人喊救命,而且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这对老七吸引力极大,就极目望去。只见河上游飘下来一个麦秸堆,麦秸堆上坐着个穿红袄的姑娘。那麦秸堆也不知在洪流里漂流了多长时间,眼见着只露出坟头大一个顶子,就要沉入洪流了。然而两岸的人只顾发浑财哪顾得上救人,再说谁有胆量扑到河心里去呢?
老七本不想理会,脑子里却突然划过一道闪电:那女子是不是翠叶呢?于是又望过去,看呀看,有点像,而且越看越像。老七于是一个猛子扑向洪流,在惊涛骇浪间沉沉浮浮,浮浮沉沉,随波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少里,终于靠近了麦秸积,抬头一看,上面坐着的果真是翠叶!
原来,翠叶在娘家住了一年多,哥嫂越来越嫌弃,成日风言风语,这都罢了;老七把她在黄河边的风流话也抖了出去,这丑事不胫而走,很快就飞到北常庄,更弄得翠叶没法见人了,于是索性跳河自尽。落水后又有点后悔,凑巧一个麦秸积漂过来,便爬了上去。真是天缘凑巧,这一爬竟爬上了老七面前。
当下老七大喜,喊:翠叶,哥救你来了!
翠叶也认出了老七,哭喊:哥,救我啊!
老七推着麦秸积向岸边靠,水太急,麦秸堆体积又大,怎么也推不动。眨眼间麦秸堆也给打散了,老七不敢耽误,奋力一跃,将落水的翠叶夹在腋窝下。翠叶呢,那顾得了许多,就拦腰抱住赤裸裸的老七。俩人也不知被巨浪吞没了多少回,喝了多少次水,做了多少回拼死挣扎,侥天之幸,竟突破千难万险,上了河岸。
翠叶一身红袄绿裤早被洪流冲刷得一丝不剩,依旧紧紧抱着老七,吓坏了。老七坐在沙滩上喘口气,一双手便迫不及待在翠叶的身上上上下下摩挲起来,然后背着翠叶起身回家。一对裸男裸女,大白天,就那么坦然行走在黄河边,不羞不臊一口气走了五十多里地。好在进村时已经天黑,竟让他们顺顺当当进了门。
老七又一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中心,连三十多里外的北常庄也传到了。翠叶的爹娘只好上门认亲,承认既成事实,认了女婿。都说老七前世积了什么德,刚刚发了那样的财,又捞到一个那样漂亮的媳妇。一年后儿子出生,五间大瓦屋也盖起来了,还置了几亩地,买了一头牛。我能记事的时候,老七两口子已经过世,只有老七种的葫芦还挂在他家的屋梁上。
我曾怀疑老七捞媳妇的真实性:洪涛里捞人,谈何容易,而且恰恰捞到的是意中人,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呢?但长辈们说:老七运气好呀,千年一回的事就让他遇上了!如今吴家人丁兴旺,有在村里的,有在城里的,老老少少七八十口,每年清明上坟,站满一埝头。老七已是吴家的五世祖了,那一埝头男女,都是他当年在滚滚洪涛里捞到的。
各位朋友,今日更新至此,明日见。
自嘲二首,各位笑话
冷水煮茶慢慢浓,
细雨润田日日功。
铁杵成针贵坚持,
野老谝闲不再停。
盲目自信胜自卑,
志大才疏亦何妨。
且著臭文三百篇,
蔑视莫言不为狂。
各位好!昨夜野老这里停电,不能与朋友们交流。这会总算好了。
@竹素园主人
自嘲二首,各位笑话(修改稿)
冷水煮茶慢慢浓,
细雨润地丝丝功。
铁杵成针贵有恒,
野老谝闲欲消停。
自信总比自卑强,
志大才疏亦何妨。
且著臭文三百篇,
蔑视莫言不为狂。
自嘲二首,各位笑话(修改稿)
冷水煮茶慢慢浓,
细雨润地丝丝功。
铁杵成针贵有恒,
野老谝闲欲消停。
自信总比自卑强,
志大才疏亦何妨。
且著臭文三百篇,
蔑视莫言不为狂。
@竹素园主人
各位朋友,明日更新
各位朋友,明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