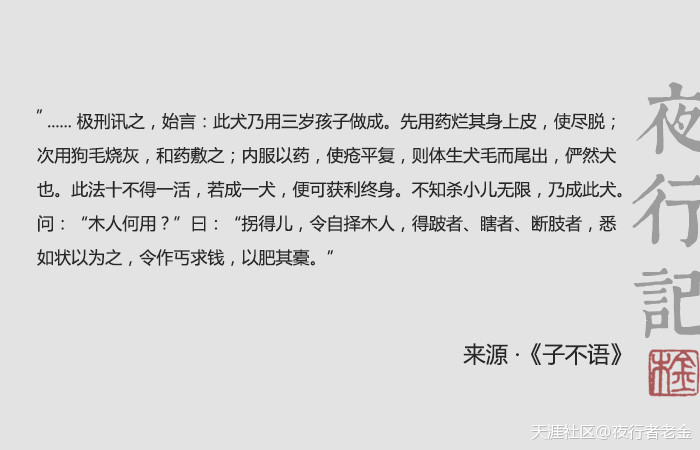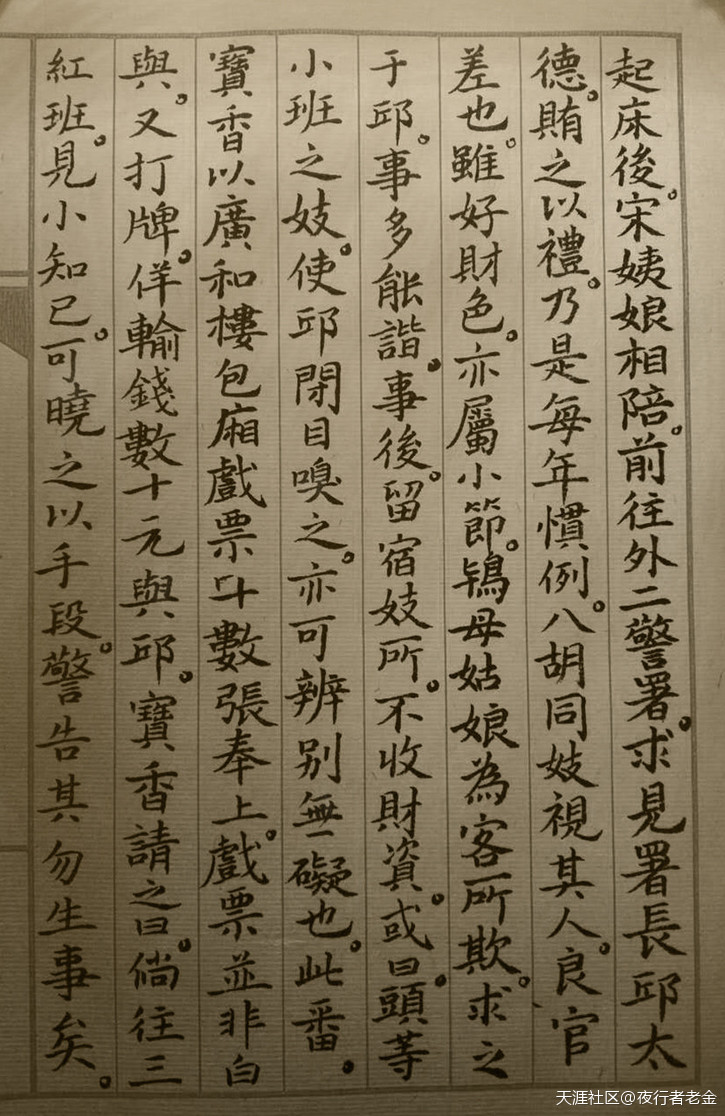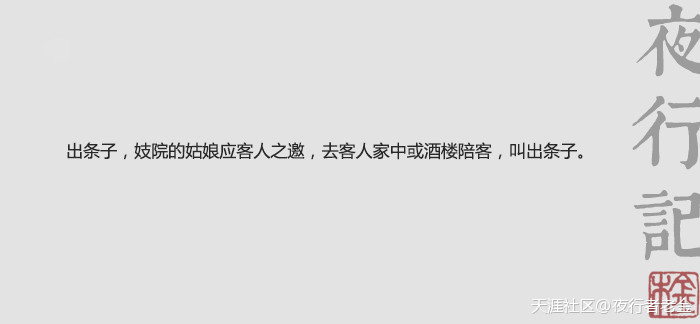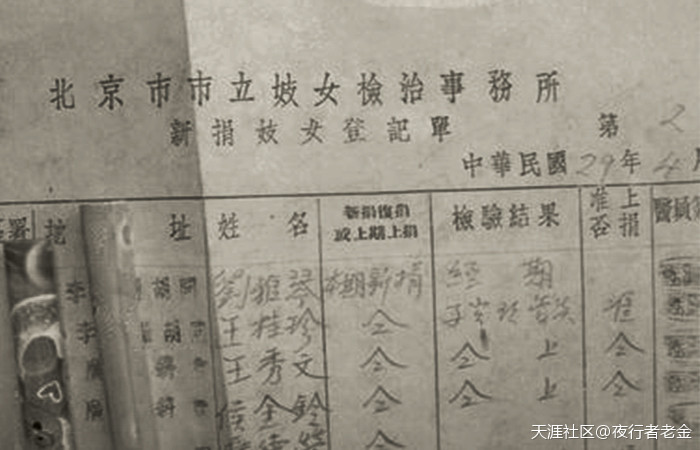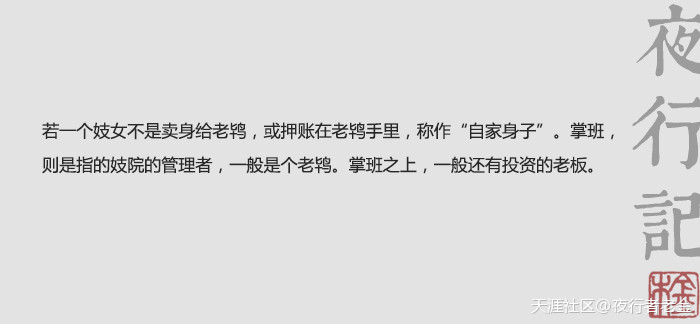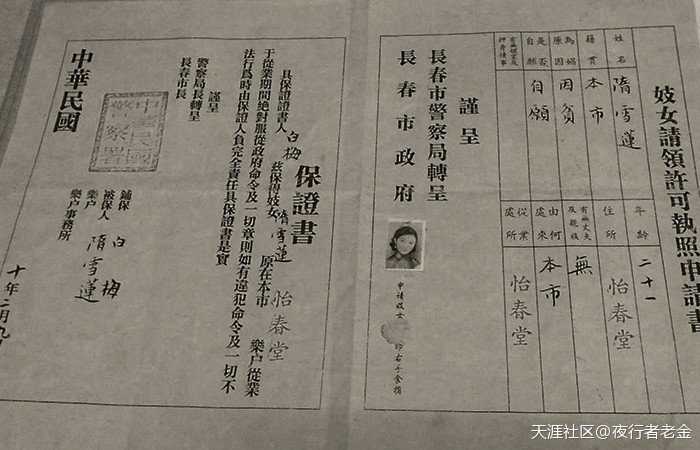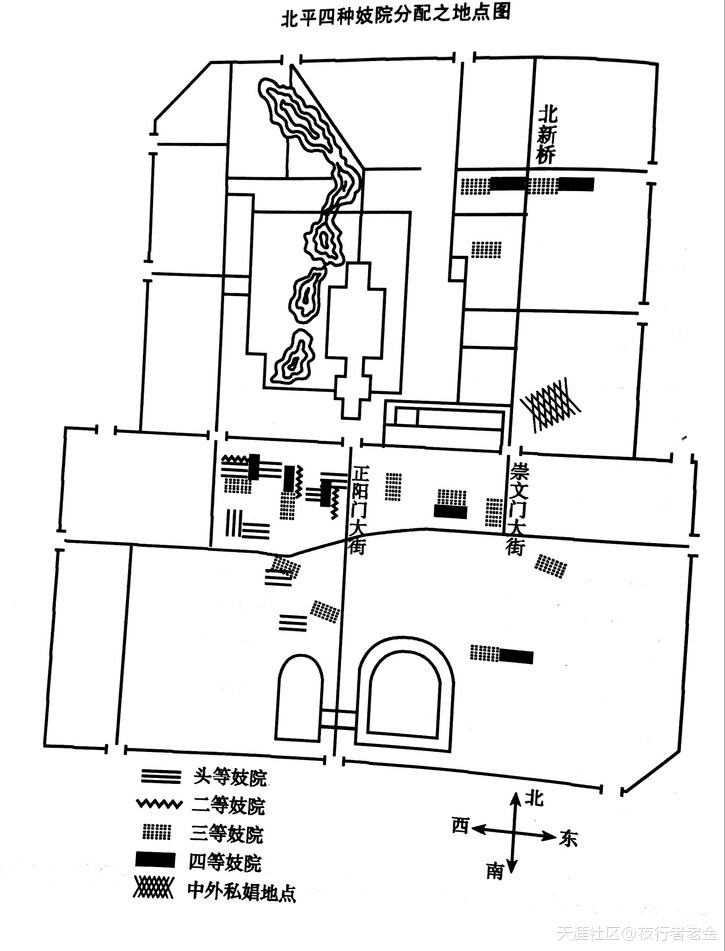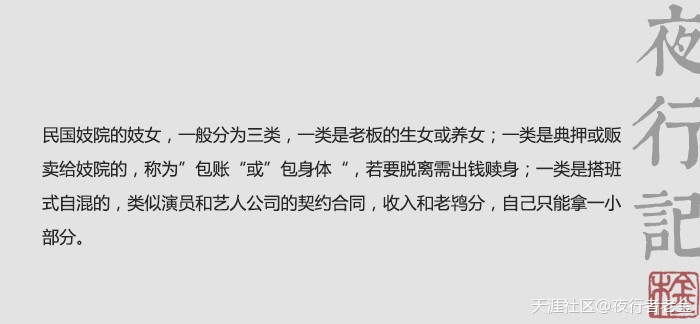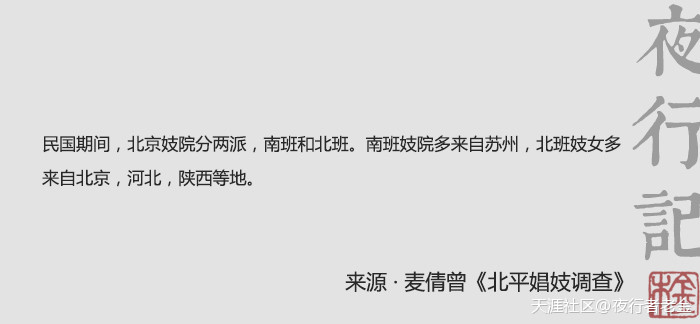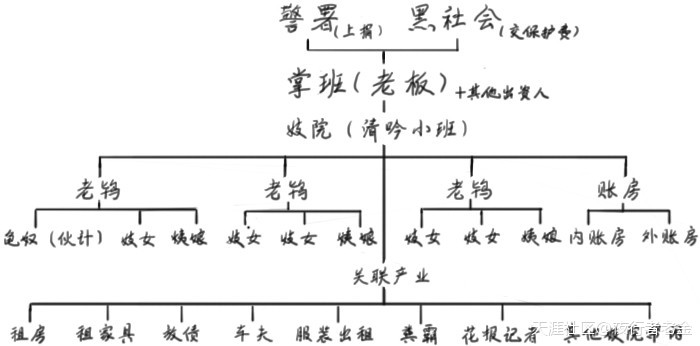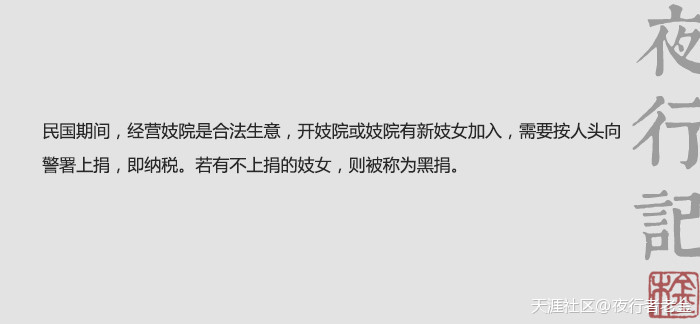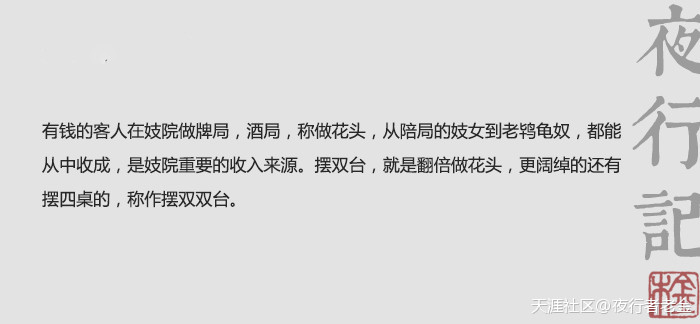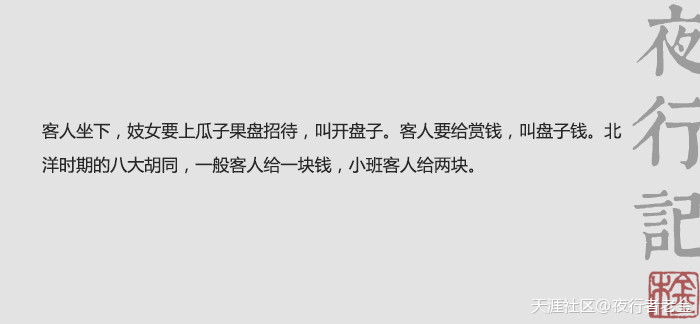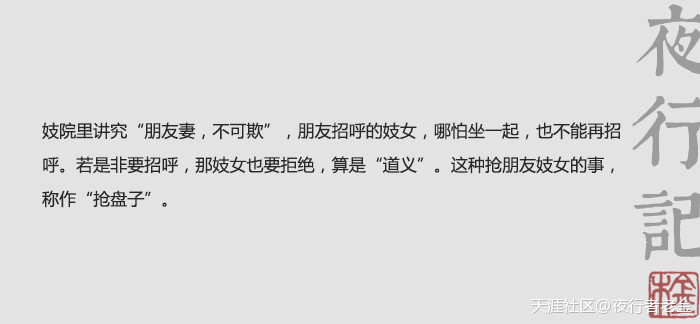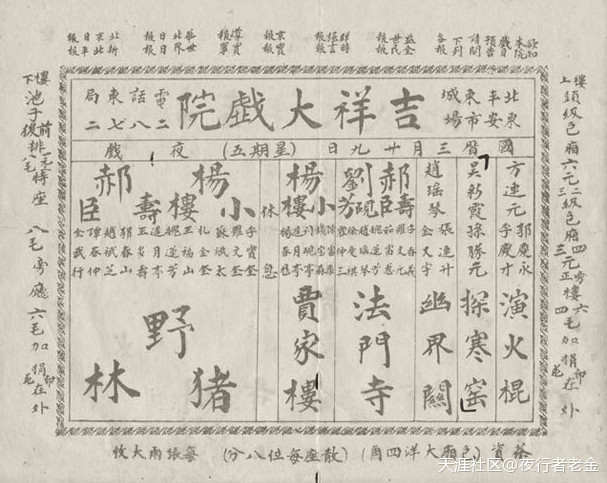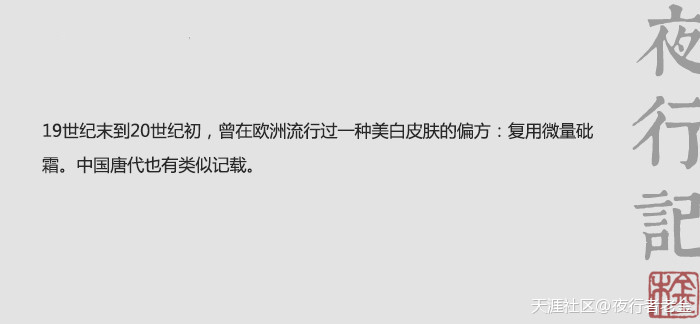我没说话,他继续说:“其实帮你不全是袁公子的面子,我不是他的家奴。如果有了别的门路,打个招呼就走。只是这个五岳门,干的是该千刀万剐的阴损事,我可不想断子绝孙。”
我问他大头娃娃和白骨精怎么回事。
钟树海停下马车,给我递了跟烟,讲了从班主那听来的儿童改造秘术。
五岳门将买来的半岁大婴儿,放进一个小坛子里,只留个脑袋在外面。
坛子底上开个洞,供屎尿流出。
精心喂养小孩几年,脑袋长大,身子不变。长大十岁,敲碎坛子,就成了大头人。
白骨精则更像古代“折割”,用细绳把小孩胳膊扎紧,时间一久,胳膊血液不通就坏死,皮肉腐烂,只剩骨头,再用药,不让小孩发炎死掉。
“但是,碎骨头怎么连缀起来,我那师弟也不明白,全是五岳门门主的邪术。”
“这门主是谁?”
“不太清楚,只知道叫金无影。”
回到城里,我想将事情交给巡警,钟树海不让。
他认为,这是“道上”的事,就要用他们的方法解决。
钟树海已经打听到五岳门的老巢,就在阜成门外护城河附近。
我问他大头娃娃和白骨精怎么回事。
钟树海停下马车,给我递了跟烟,讲了从班主那听来的儿童改造秘术。
五岳门将买来的半岁大婴儿,放进一个小坛子里,只留个脑袋在外面。
坛子底上开个洞,供屎尿流出。
精心喂养小孩几年,脑袋长大,身子不变。长大十岁,敲碎坛子,就成了大头人。
白骨精则更像古代“折割”,用细绳把小孩胳膊扎紧,时间一久,胳膊血液不通就坏死,皮肉腐烂,只剩骨头,再用药,不让小孩发炎死掉。
“但是,碎骨头怎么连缀起来,我那师弟也不明白,全是五岳门门主的邪术。”
“这门主是谁?”
“不太清楚,只知道叫金无影。”
回到城里,我想将事情交给巡警,钟树海不让。
他认为,这是“道上”的事,就要用他们的方法解决。
钟树海已经打听到五岳门的老巢,就在阜成门外护城河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