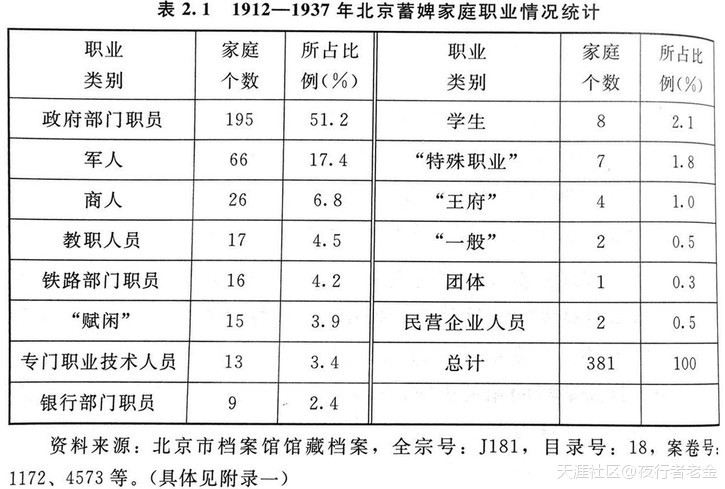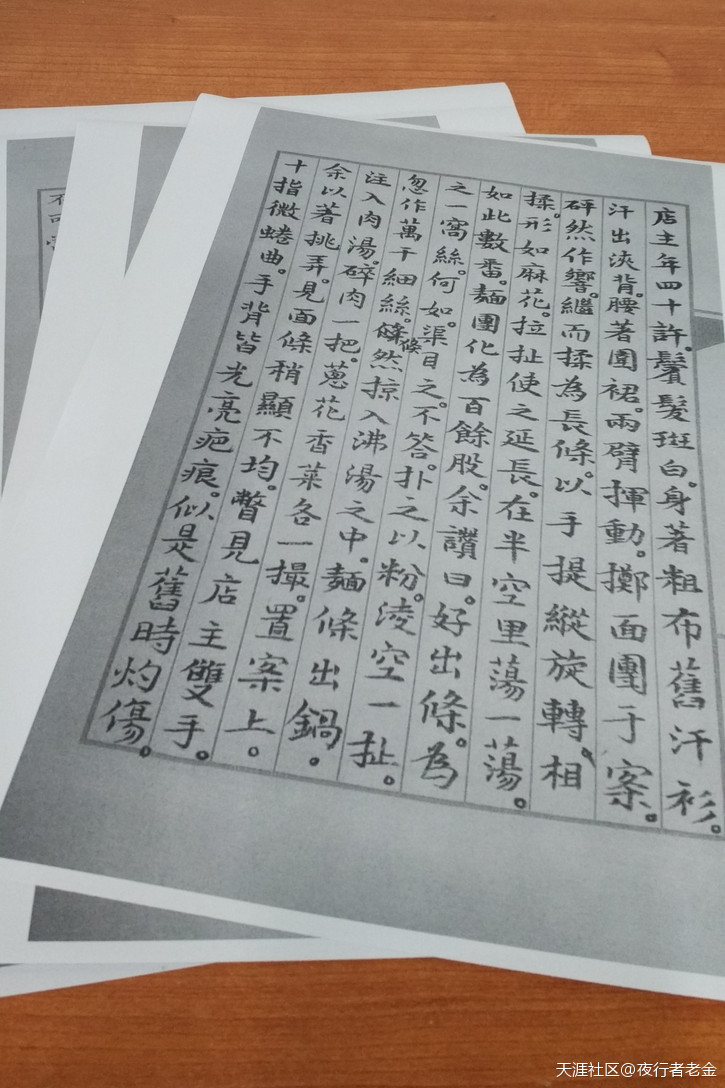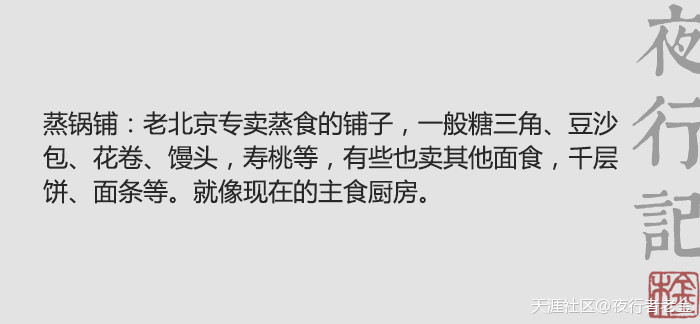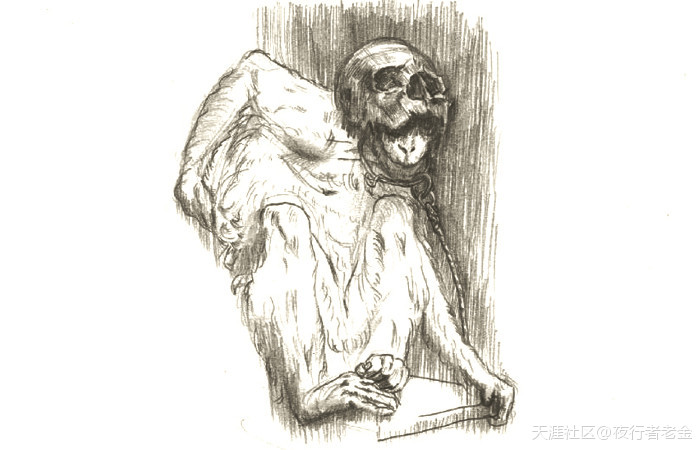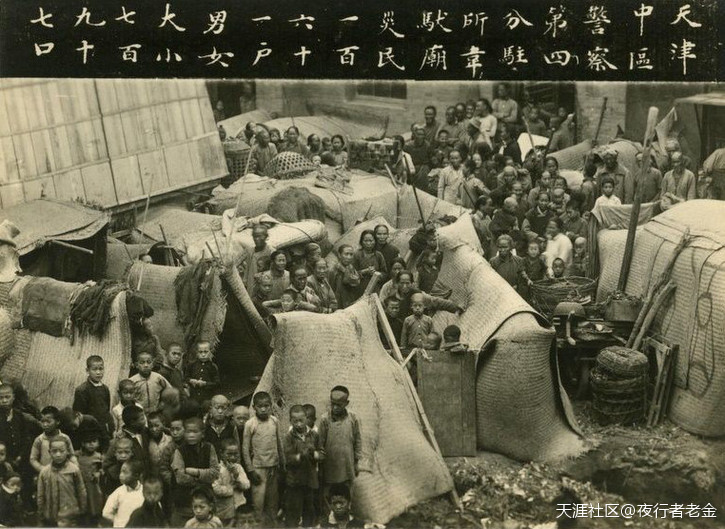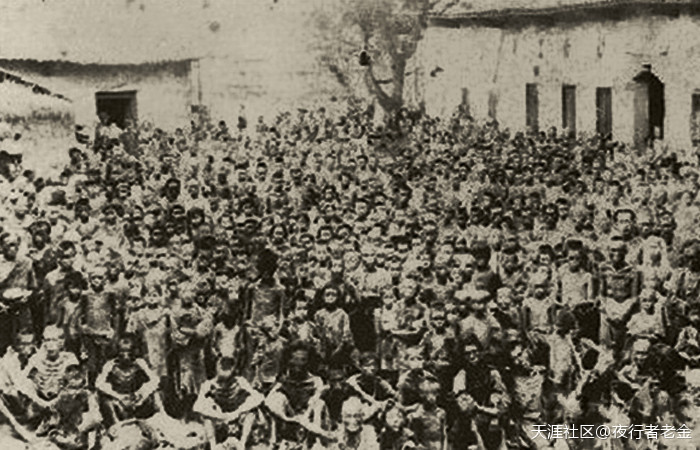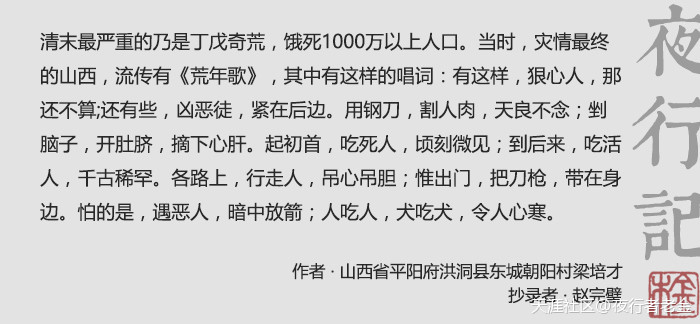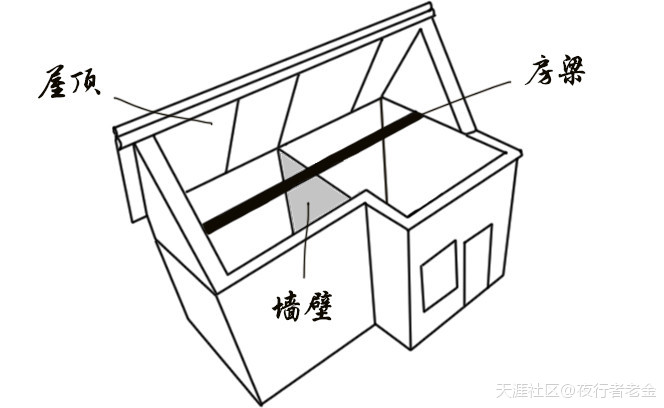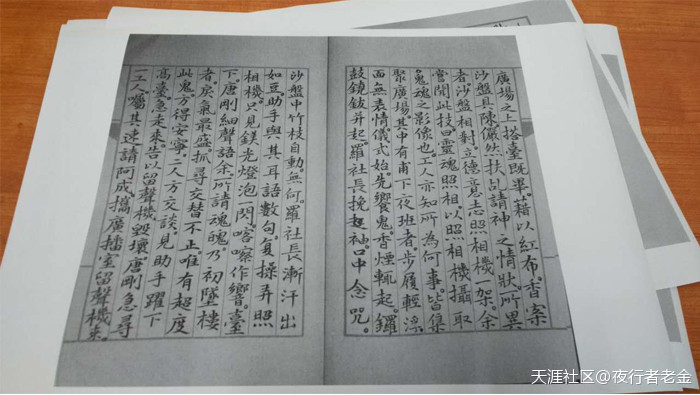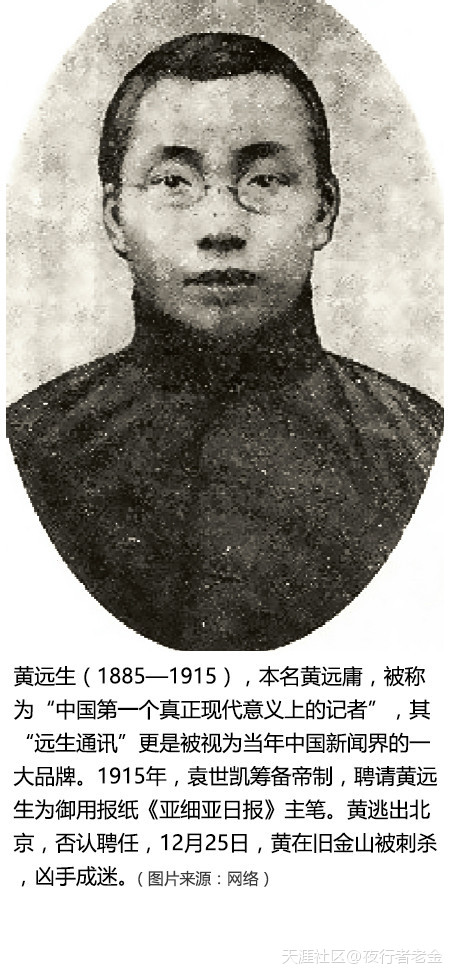走到新街口,碰见老杜带着一群警察来了。我和戴戴出发前,他就去了警署,好说歹说搬来了警察,到马家审问仆人,打听了我们的去处。
我和带队的侦探说了情况,让戴戴我俩做了笔录。那侦探说:“金先生,这事儿大了,马旅长死了,我们不好办啊。”
我让他按流程办,给他写了地址,说:“知道你们警察厅和军队一向不对付,但马昭雄是杀人,你们有证据,怕什么?”
侦探愁眉苦脸,带警察进了胡同。
我问老杜,怎么知道会出事。他皱起眉头,说:“前天跟你说了,我早就知道马昭雄不是好人。”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报上揭露马昭雄杀人的文章。我说当然记得,马昭雄想杀的,就是那个非文。
老杜砸吧砸吧嘴,说:“那是我写的,非文,就是我。”
我瞪了他一眼:“操,是你小子,早就知道马昭雄杀人,怎么不说?差点玩死我!”
老杜使劲摇手:“没有没有!我确实悄悄跟踪过他,但就知道他虐待丫头,哪知道他真杀人?那文章半真半假写,是想让警察注意。 你可以说我是半虚构的。”
我说,老杜你真是怪,不知道该说你胆大还是胆小。老杜呵呵一笑,给我讲个件事。
我和带队的侦探说了情况,让戴戴我俩做了笔录。那侦探说:“金先生,这事儿大了,马旅长死了,我们不好办啊。”
我让他按流程办,给他写了地址,说:“知道你们警察厅和军队一向不对付,但马昭雄是杀人,你们有证据,怕什么?”
侦探愁眉苦脸,带警察进了胡同。
我问老杜,怎么知道会出事。他皱起眉头,说:“前天跟你说了,我早就知道马昭雄不是好人。”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报上揭露马昭雄杀人的文章。我说当然记得,马昭雄想杀的,就是那个非文。
老杜砸吧砸吧嘴,说:“那是我写的,非文,就是我。”
我瞪了他一眼:“操,是你小子,早就知道马昭雄杀人,怎么不说?差点玩死我!”
老杜使劲摇手:“没有没有!我确实悄悄跟踪过他,但就知道他虐待丫头,哪知道他真杀人?那文章半真半假写,是想让警察注意。 你可以说我是半虚构的。”
我说,老杜你真是怪,不知道该说你胆大还是胆小。老杜呵呵一笑,给我讲个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