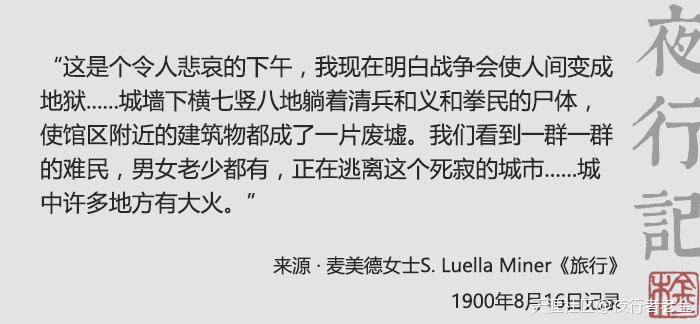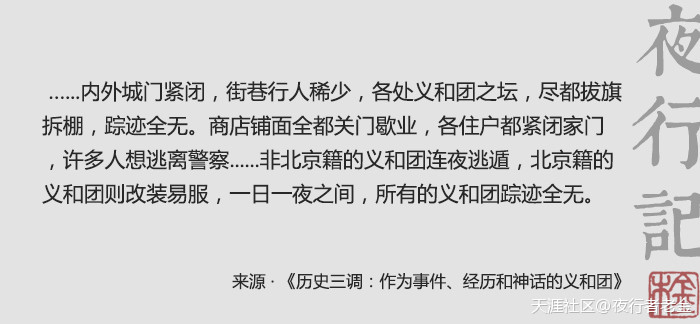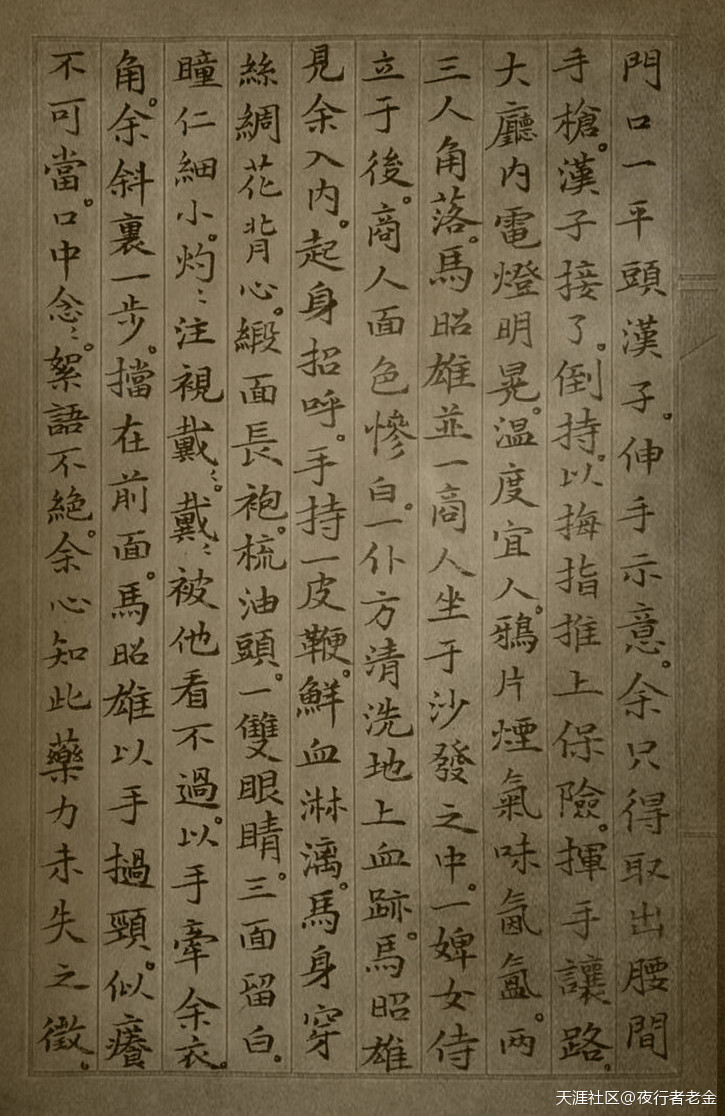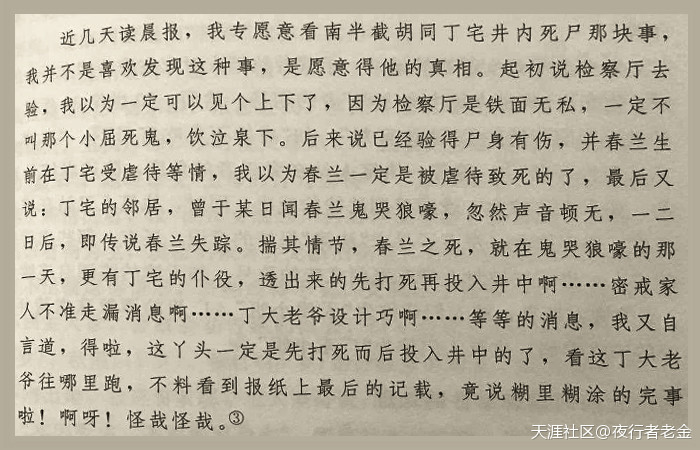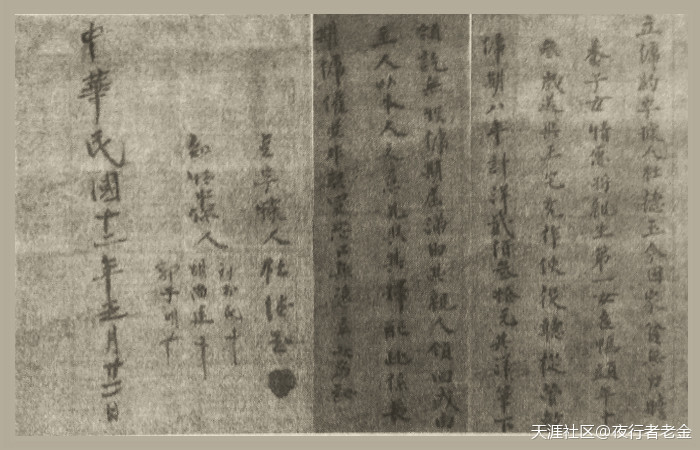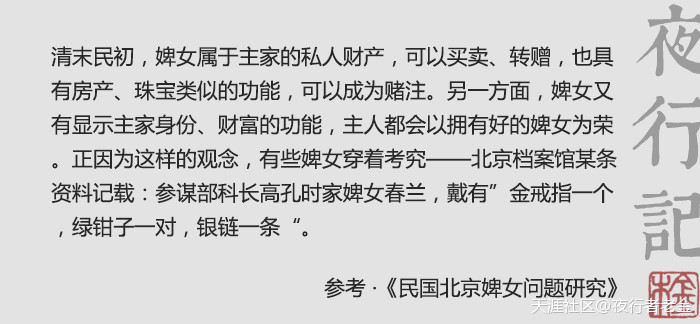我就抬头看,天上全是烟,飘满了灰,什么都没有——也可能有红灯照,我没看见。

【1966年,文革初期绘画的中国民俗画,内容是红灯照协助攻打北堂。可以看到,左后的一个红灯照,在义和团和洋人之间舞动一条魔绳,保护中间的红灯照女孩不被火枪打中——这是为了宣传需要,将历史神话的典型。图片拍摄自《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原图为The Chinese folk picture: The spiriual life of old China in folk graphic art。】
见我俩跑,其他人也扭头往回跑,跑着跑着,又都喊着转回来了,一片乱,有往前冲的,有往后跑的。
为什么转回来?因为清兵也开枪了。洋人在前面开枪,不让义和团往前冲,清兵在后面开枪,不让义和团往后退。
幸好,我们突然被一队斜插过来的人马冲散了,捡回了条命。
那队人马,领头的是个秃头和尚,他骑着白马,身披青袍,舞着一把青龙偃月刀。后面跟着的义和团,全都右手拿到,左手捏着一把香——这是大学士刚毅请来的五台山和尚,关公附体。
这和尚的关公,比我表哥威风多了。他一杀过来,前门的义和团一下就勇猛了,一排一排杀上去,洋人排成排放枪,(义和团)一排一排倒。
我们人多,就这么轮番冲,轮番倒,打了一个时辰。我当然没上去!我俩趴地上了,装死,看着。曾老师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到了北堂,就再没见到他。
那个和尚,就冲了一下,退到西安门的一个空店铺里坐下了,不知道做什么。一直坐到半下午,他起来了,喝了杯酒,对着义和团喊:“时辰到了,可以杀了!”
喊完,他就跨上赤兔马(金醉注:原文如此,讲述者记忆有误,或当时确实进入了表演状态),扛上偃月刀,向北堂冲去。

【1966年,文革初期绘画的中国民俗画,内容是红灯照协助攻打北堂。可以看到,左后的一个红灯照,在义和团和洋人之间舞动一条魔绳,保护中间的红灯照女孩不被火枪打中——这是为了宣传需要,将历史神话的典型。图片拍摄自《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原图为The Chinese folk picture: The spiriual life of old China in folk graphic art。】
见我俩跑,其他人也扭头往回跑,跑着跑着,又都喊着转回来了,一片乱,有往前冲的,有往后跑的。
为什么转回来?因为清兵也开枪了。洋人在前面开枪,不让义和团往前冲,清兵在后面开枪,不让义和团往后退。
幸好,我们突然被一队斜插过来的人马冲散了,捡回了条命。
那队人马,领头的是个秃头和尚,他骑着白马,身披青袍,舞着一把青龙偃月刀。后面跟着的义和团,全都右手拿到,左手捏着一把香——这是大学士刚毅请来的五台山和尚,关公附体。
这和尚的关公,比我表哥威风多了。他一杀过来,前门的义和团一下就勇猛了,一排一排杀上去,洋人排成排放枪,(义和团)一排一排倒。
我们人多,就这么轮番冲,轮番倒,打了一个时辰。我当然没上去!我俩趴地上了,装死,看着。曾老师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到了北堂,就再没见到他。
那个和尚,就冲了一下,退到西安门的一个空店铺里坐下了,不知道做什么。一直坐到半下午,他起来了,喝了杯酒,对着义和团喊:“时辰到了,可以杀了!”
喊完,他就跨上赤兔马(金醉注:原文如此,讲述者记忆有误,或当时确实进入了表演状态),扛上偃月刀,向北堂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