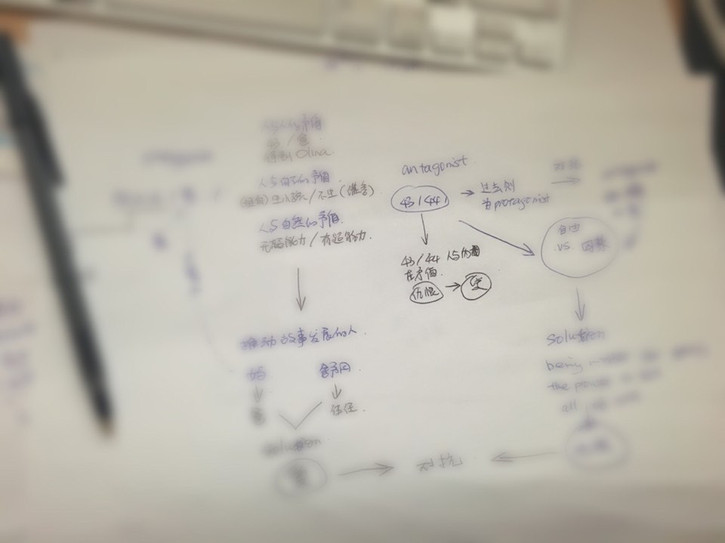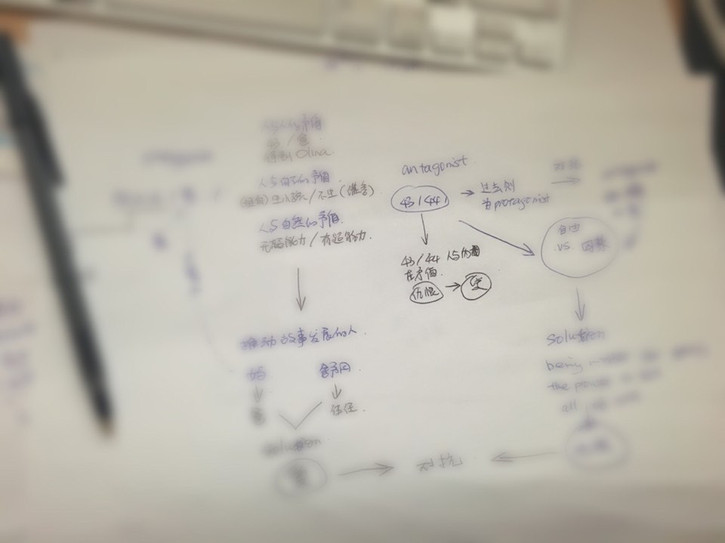“别打了,你不会想进监狱的,你听我说,”阿尔法异常的冷静:“你现在是私闯民宅,在美国私闯民宅是重罪,而且你还携带了武器。你会进监狱的。”
“不….我看到玛丽亚把你拖进房间,我想去救你,”琳娜拼命摇头:“她突然发了狂,她拿刀攻击我,我才….”
“即使警察来了,他也会问你为什么当时看到玛丽亚拖着我的时候不报警,你擅闯民宅,而且手里拿着枪,玛丽亚即使把你当长杀了也是完全合法的正当防卫。你现在是举枪射击屋主!而且你不是美国公民,你是拿着签证的留学生,即使被判防卫过当杀人你也至少要做五年牢。你有保释金吗?有钱打官司吗?”阿尔法说道。
“不…你是当事人,你可以帮我作证呀!”琳娜说:“你可以告诉法官,是因为玛丽亚虐待你…”
“哪怕我去作证控告我的祖母,你的判决和这一点关系没有。我可以去控告玛丽亚虐待我,但是这不能作为抵消你杀人的理由,而且联邦法律规定八岁以下的小孩是不能做刑事案件的证人的,就算我去了,法官会听我说吗?”阿尔法看着琳娜:“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逃走吧。”
“你说什么?”琳娜睁大了眼睛。
“琳娜,我们走吧,好不好,求你了。”阿尔法又变回那个跟琳娜撒娇的小孩,拉着她的手轻轻的说。
“不,不可能....Shin还没回来,我要等我老公….”
“为什么要等他呢?他爱你吗?他不是骗了你吗?我知道你们在吵架,虽然你们说中文,我听不懂——但我能感觉到你对他的失望,为什么不离开他呢?我们在一起不开心吗?”
“你什么意思?”琳娜松开阿尔法的手。
“为什么要跟伤害你的人在一起呢?Shin伤害了你,你不恨他吗?你怎么会爱你恨的人呢?阿尔法永远不会伤害你呀。”阿尔法用他天真无邪的蓝眼睛看着琳娜。
琳娜摇头:“你不懂,你还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
“我已经够大了。”阿尔法转过身去,恰好正对我面朝镜子的方向。
“因为你爱一个人所以你会原谅他——爱的对立面不是恨。”琳娜神情复杂的摸着肚子:“而且,我有了宝宝。”
“你不会想和伤害你的人生孩子。”阿尔法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冰冷。
“你说什么?”
“我可以回去拿我的护照,我们去英国也行,法国也行。没有人知道我和玛丽亚住在这,我们把枪毁掉,然后直接出国。老实说也许玛丽亚在这里烂掉十年八年都不会有人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会追究到我们头上来,你知道楼下的保安吗?玛丽亚前两天把他杀了,他现在正躺在这层楼的某个房间呢——”阿尔法微笑着说:“我们把枪放到他的手上,他还拿着玛丽亚的支票和信,即使说他想抢劫孤寡老人也未必不能说过去——”
琳娜的脸上渐渐浮现出不解和恐惧,慢慢的向后退:“——你不是阿尔法,你一个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些,你不是他…..你是谁?”
阿尔法突然收起了笑容,转头看着琳娜,但他的眼神却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做我弟弟的母亲吗?”
“琳娜!!!!!!!”我举起凳子奋力向镜子砸去!一下一下!
“琳娜!!快跑!!”
厚重的水泥墙终于有了些许反应,单项玻璃轻微震动起来。
琳娜和阿尔法朝我这边看过来,阿尔法看着我,他轻轻的用嘴做了几个口型,嘴里没有发出声音。
但他的声音像响雷一样在我脑子里炸开:
“去,死,吧。”
我猛然听到脚步声,刚转过头,就看到玛丽亚面无表情的朝我扑过来!
她竟然在数秒之内从地上爬起来,并且飞扑到我面前,行动之快就像燃尽了她剩余的最后一点生命。
什么东西在控制她!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把刀直挺挺的从我肩膀上扎下去。
我最后看到的画面,是那面镜子旁边挂着的一张照片。
黑白照,一个军官,穿着军服,站在一面纳粹的旗子下。
他自豪的笑着。我忽然觉得他的身影竟然有点熟悉,那是瓦多玛死之前给我的全家福上军官的身影。
他的手搭在两个两个孩子肩膀上。
两个孩子,一样的头发,一样的身高,一样的眼睛。
一样的脸。
我眼前一黑。
——————————————分楼层——————————————————
老哥今天给我拍了一堆论文资料,让我好好研究不要丢他生物博士的脸。
老板下午跟我吃火锅,说她注册了小号来支持我,不要给公司丢脸否则饭碗就没了。(楼主不是专业写手,老板也和文学行业没半毛钱关系)
我今天晚上连饭都没吃,资料也没看,使劲研究了一下到底哪个是老板的小号。
————————————分楼层————————————————————
@xushuanguu 2017-03-13 23:29:00
很好看,支持下
-----------------------------
谢谢你~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为了大家我也不挖坑,今天开始第一章|六十年前的回忆|大揭秘~
@东德周 2017-03-14 10:55:00
随便瞎猜一下~~
六十年的纳粹实验已经在西藏密宗和欧洲黑魔法的混合使用体系上获得了突破,在魔法的帮助下,他们能够将一个人的灵魂注入另一个人的躯壳里——当然,实验还没有完全炉火纯青,所以,灵魂置换只能在拥有相同基因的双胞胎之间进行。
纳粹军官实验的两个孩子之中,有一个被弄死了,死去的灵魂被注入到另一个孩子的身体里。
阿尔法是一个躯体里寄生着两个灵魂,就是传说中失传已久的人格分裂,两个......
-----------------------------
好一个钢之炼金术师!!我喜欢!
然而好像有点不对。
好黑。
我再度站在那扇地狱之门面前。
地狱之门的中间,雕刻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脏,它被无数双来自地狱的恶灵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一双双枯竭的手,是骑着七角海兽的愤怒、剥光衣服的伪善、张着血盆大口的贪婪。
我推开了门,那是一间产房。
一个瘦弱的女人正在生产。她漆黑的头发蒙住了脸,医生并没有因为她的嚎叫而心生怜悯,反而粗鲁的掰开她的双脚。
“胎儿头太大了。”医生的声音很冷漠:“三分钟之后还没生出来,就直接刨腹吧。”
我向窗外望去,外面的正在下雪,一群衣衫褴褛的人面无表情的在大雪里挖洞,隔壁站着一排纳粹士兵。
“停!”一个军人的声音。
那些劳工扔下锄头,中间有包着女人和没穿鞋的小孩,小孩们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女人开始哭泣,男人们的表情却是漠然。
“开枪!”一排士兵叩响了步枪,随着噼里啪啦的枪响,这群人无声无息的倒进了之前挖的洞里。
“长官,您能再想我透露一点西藏之行的收获吗?您究竟有没有找到日耳曼民族的祖先吗?我实在是太好奇,太激动了!”
我转过头,才发现产床隔壁竟然有两个人坐在一只圆桌旁喝茶,他们对那个孕妇发出来的惨叫视若无睹,就像习惯了一样。
说话的是其中一个穿着白大褂身材瘦小的医生。他把他的头发用发蜡一丝不苟的梳在脑后,白大褂下面是一套纳粹军服,他似乎有点洁癖,连吃蛋糕也要带着白手套。
“门格勒,我能告诉你的已经全告诉你了,伟大的雅利安民族毫无意外是神的子孙,这是已经被证实的了。哎,可惜了,我们身体里流淌的它的血液,已经在数千年的异族通婚中被稀释得所剩无几了。”另一坐做着的是一个竖着寸头的军官,脸上架着一副金丝圆眼镜。
“长官,请您一定要帮我带话给元首大人,请他一定要相信我,”医生搓着双手,脸因为激动涨的通红:“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在慕尼黑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就是人种种族学,如果情报可靠,雅利安的祖先真的来自西藏,那我有十分的把握这些吉普赛人也从那里来——”
医生喝了一口茶:“——您带回来的西藏人的头骨尺寸和发型样本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他们和这些吉普赛人有80%的特征是匹配的,尤其是这一支,他们从来没有和外族通过婚,他们的基因从理论上来说高度保持了最初的品质。”
医生说着,侧头看了看床上还在嚎叫的孕妇。
我全身一震,这个医生难道是“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
约瑟夫.门格勒是德国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杀人犯之一,他迷信人种优等学说,是个不折不扣的雅利安种族至上的拥护者。战时集中营里面最惨绝人寰的实验,包括活体实验和芥子气实验,都是他一手操办的。门格勒接管的第一个集中营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是专门关押吉普赛人的集中营,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然而让我深感震惊的,是当他们说[吉普赛人也是神的子孙]的时候!
瓦多玛,瓦多玛,难道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吗?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都从从西藏而来?
“可是你到目前为止的实验都是失败的,”寸头军官皱着眉头的表情有点阴郁:“你让我们日耳曼民族的高等军官去和这些肮脏的吉普赛女人睡觉,可到目前为止,生下来的孩子没一个是健康的——”
“尊敬的希姆莱将军,请允许我为自己辩解,人种杂交本来就存在着风险,”门格勒还没等寸头军官说完,就急急忙忙的抢白:“几个月来我一直致力于解剖那些畸形婴儿,我的结论是,雅利安人血液里神的基因已经相当稀薄,一旦和浓度高的基因相融合,就容易产生变异——但这种变异我把它归结于返祖现象。请您一定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相信这一次——”
门格勒突然神秘的笑了笑:“——这一次不会失败的。”
“生了!生了!”护士兴奋的叫了出来:“长官!是双胞胎!健康的双胞胎!”
“元首保佑!日耳曼民族万岁!希特勒!”门格勒激动忘情地跳起来,在胸口划着十字。
“希姆莱将军,元首的电话!”一个德国士兵推门进来,敬了个礼。
“我先走了,你的实验成果我会向元首大人回报的,”寸头长官放下茶杯站起来,推了推眼镜:“只是——他们可是你的亲生儿子,你能保证你对他们没有感情吗?”
门格勒扬起了下巴。笔直的站直身体,敬了一个纳粹礼。
“长官,他们不是我的孩子,他们只是试验品而已。”
在两个孩子的哭声中,门格勒笑了,笑得那么人畜无害。
这个笑容,我在阿尔法脸上见过。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门格勒让我觉得分外眼熟,他就是瓦多玛的照片和镜子旁边的相框里那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希姆莱满意的点点头,走了出去。
“长官,这个女人怎么办?”负责接生的医生转头问门格勒:“扔到毒气室还是埋掉?”
“啪!”门格勒一个巴掌扇到这个医生的脸上。
“保住她的性命!她可是我们雅利安种族复兴的功臣!”门格勒咧开了嘴角:“和我重要的实验对象。”
门格勒离我只有不到两米,他的笑容让我遍体生寒,同样身为男人,我对他的恐惧就像看见了豺狼野兽。
回过神来的时候,我面前是两个三四岁的小孩,一个躲在另一个的后面,站在前面那个看起来大一点的,怯生生的叫了一句:
“爸爸.....”
“我说了多少次不要叫我爸爸!叫我门格勒医生!”门格勒不耐烦的转过头来,对他们俩吼道。
“门格勒医生…我们能去睡觉了吗?”两个小孩被吓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再等等。”门格勒放下报告,打开办公室的门,外面站了几个衣衫褴褛的犹太孩子。
“门格勒叔叔。”这些孩子轻声的、奶声奶气的叫了一句。
“真乖。”门格勒露出了一个温暖的笑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糖果和饼干递给这些孩子:
“吃吧,吃完了就跟这个叔叔去楼下坐汽车。”
门格勒指了指站在后面的一个纳粹士兵,摸了摸孩子们的头:“晚安了。”
门格勒的笑容在关上门那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一边透过玻璃看着那几个小孩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卡车,一边拨通了电话:
“那些小畜生已经被送往实验室了,解剖资料下礼拜拿到我办公室来。”
说完,他转过身皱着眉头看着那两个双胞胎:“哎,你们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也不是蓝色的,元首下个月就来视察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两个小孩跟着门格勒出了门往地下室走,穿过一排排低矮的铁笼,铁笼里面关着被剜去眼睛或截肢的吉普赛人。
“把最新的研发成果拿出来给他俩注射吧。”门格勒对另一个医生模样的人说。
“但是....这个研发成果的成功率还没超过50%…”那个医生犹豫了一下。
“行了,就算失败了也不会致命。”门格勒不耐烦起来。
“呀啊啊啊————————”
一声孩子的惨叫,在地下室里回荡着。
两个孩子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卧室里,虽然不是笼子但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的头发已经变成了金色,眼睛是海水一样的浅蓝。
可是其中一个在地上痛苦的滚来滚去。
“哥哥,哥哥!好黑,我看不见了!”那个孩子的眼泪向断了线的水晶从蓝色的眼睛里流出来。
“不要怕!不要叫!爸爸会杀了我们的!”哥哥急忙捂住弟弟的嘴。
“呜呜…..”弟弟在地上抽搐着。
我全身发抖,跌坐在地上。
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失去光明,而是你最亲的人故意让你失去光明。
不是失去希望,而是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希望。
不知道过了多久,黑暗和沉默中响起一个轻轻的声音。
“哥哥,你说我们有名字吗?”弟弟蜷缩在仅有的小床上:“我听到外面的军官说,他们的孩子都有名字。他们的孩子都会由爸爸妈妈起名字。”
“门格勒医生说我们不需要有名字,我们也不需要有妈妈。”
“哥哥,可是我很想有个名字。我能给你取名字吗?”
“我不需要名字。”
一晃之间,光线刺的我睁不开眼睛。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房子,红色的砖墙,外面是森林和草坪,空气里弥漫着樟木的香气。
我认得这里,我在梦里见过一次,这么美丽的地方,却有一个与之不相称的残酷名字:
生命之泉农场。
门格勒牵着哥哥,哥哥牵着弟弟,从一部豪华的小轿车上下来。
门格勒把他们送到门口,摸了摸两兄弟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和一口洁白的牙齿:
“进去吧,下次我再来看你们。”
“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二楼,”领头的护士说,她扭着臃肿的身体向前面走着:“二楼的孩子是门格勒医生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和你们一样,大部分都是双胞胎——你们以后会成为最强的雅利安战士。”
弟弟因为看不见,惊恐的听着周围的声音,跌跌绊绊的拉着哥哥的衣服。
哥哥的脸上没有表情。
“听说你们的母亲是吉普赛人?”坐在办公室里的医生看了看档案,和身边的另一个医生说道:
“根据我们的研究,吉普赛人最早混迹欧洲时,一直以占卜术维持生计——可是根据我们的脑解剖资料看来,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预言能力,那只是这些劣等流氓的小把戏,他们的中枢神经非常发达,比普通人的脑波更强。所以他们能或多或少的读到问询者的思想,再把问询者想的事情准确的说出来——把他们俩分到B区吧,每天注射四次利多卡因何氨茶碱,配合电击,看看会不会影响大脑颞叶部分的神经元。”
我没听过利多卡因,但氨茶碱是一种呼吸系统药物,通常禁止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服用,过量时会引发癫痫。
“带他们下去吧,别忘了把编号刻在手臂上,现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我都快分不过来了,”医生翻了个白眼:“哥哥就是43号吧,弟弟44号。”
我记得刚搬家维修天花板电路的时候,我被电了一下。
美国的电压是110伏特,一秒钟我已经呲牙裂嘴。
我不知道每天被电击半小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永无止境的药物注射,和注射后的抽搐。
我能听到他内心的哀嚎,就像一只跌入井里未成年的困兽。
能看到天,能看到云,能看到树叶在外面随风摇摆。
可永远都无法出去。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天,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一年。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那间白色的审讯室。
穿着短袖的兄弟俩,手臂上有两个醒目的数字,哥哥是43,弟弟是44.
哥哥坐在左边,盯着对面的军事罪犯,弟弟睁着那双空洞的眼睛,手边是一张纸和一支笔。
“你们9月份的作战计划是什么?”隔壁的纳粹军官问了一句军事罪犯。
哥哥头上的汗留下来,弟弟开始颤抖。
数分钟后,弟弟张开了嘴:
“主力,部,署,在,法比边界,北,端,和,其,他,在,南部,马其诺防线….”
一边在纸上画着草图,草图上是同盟国的战略部署图。
“很好!Marvellous!!” 纳粹军官情不自禁的喊出了一句法语:“这两个孩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他们是日耳曼的骄傲!”
“恭喜你们合格了!”玛丽亚,我认出了她,她穿着高跟鞋走过来搂了搂着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面无表情。
游戏室。
“你们知道游戏室的规矩吧?挑选自己的玩具吧。”玛丽亚向隔壁的护士招了招手,护士推了一个装满武器的车过来。
哥哥拿了一把枪。弟弟什么都看不见,颤抖的躲在哥哥后面。
“你们出去吧。”哥哥说道。
游戏室的大门缓缓关上。
“你蹲在这里,不要说话就行了。”哥哥把弟弟领到墙角。
我努力闭上眼睛,但根本逃不过那些画面,我是在他的回忆里啊。
这个夜晚没有星星,夜空像墨水一样漆黑。
“哥哥,外面的小孩也是这么玩游戏的吗?”弟弟问。
“我不知道。”哥哥躺在床上看着越来越瘦的弟弟。
“他们的玩具也是这些…”
“你别说这些废话了,最重要的是我们俩活下去。”哥哥不耐烦的打断弟弟:“我们表现越好,他们就越不会杀我们,你看到隔壁几间房已经空了吗?算了,你什么也看不到。”
“……”弟弟沉默了。
“….你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哥哥觉得说得有点过分,换了个话题。他发现弟弟的脸越来越苍白。
“我最近总是睡不好,每到夜里这里就会难受….”弟弟摸了摸胸口。
第二天,又是审讯室。
“你们潜伏在党委队里的间谍是谁?”纳粹军官问。
对面坐着一个英国女人,她的脸已经毁容了,头发湿答答的挂在脸前面,伤口还在流着血。
哥哥盯着她的眼睛,汗水流下来。
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弟弟并没有说话。
哥哥实在忍不住了,他擦了擦汗,回头问弟弟:“......44号,你怎么回事?”
弟弟的眼睛里缓缓流出了两行血泪,血滴在纸上,溅出了两朵好看的红色小花。
弟弟笔下画的,是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微笑着坐在草坪上。
弟弟直愣愣的仰面倒了下去。
“快点叫人进来!快点!”玛丽亚也慌了神,她不明白一直表现优异的双胞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44号床。
弟弟躺在床上抽搐着,脸色苍白。
“你们怎么回事?我说了要控制药量!怎么能给他一天注射500cc的利多卡因!这是急性心梗!哎,这活不长了….”
“现在战争已经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了…我们要解读的情报太多,我这不也是担心….”
啪!一个耳光的声音。
“你还有脸给自己辩护?快打电话给门格勒医生吧!这小子还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哥哥握着弟弟的手。
“….是不是爸爸要来了?”弟弟虚弱的问。
“不是爸爸,是门格勒医生….”哥哥握紧了拳头。
“是爸爸…是爸爸,我听见他们说,孩子们应该叫爸爸作爸爸,妈妈作妈妈….”
“…..”
哥哥沉默了。
“你说….爸爸想我们吗?”弟弟昏睡了一会,醒来又问。
然后是蹬蹬蹬蹬的脚步声,门格勒医生一头大汗,出现在走廊上。
还没等那两个医生说话,门格勒劈头盖脸的给了他们两个耳光。
“你们知道你们干了什么吗?!你知道他们两个是多宝贵的试验品吗!!”门格勒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暴跳如雷:“开门!给我开门进去!”
门格勒拿着一只金属的小箱子走进监仓,他把小箱子小心的放在地上,然后查看了一下弟弟。
门格勒流下了一滴眼泪。
紧接着,门格勒大声叫着:“来人啊!把他送进手术室!”
一群医生护士冲进来,七手八脚抬起弟弟。
哥哥使劲抓住弟弟的手,无论如何也掰不开,其他医生没一点办法,又不敢伤了哥哥,只好把哥哥也带进了手术室。
门格勒把小箱子交给了一个医生:
“这是希姆莱长官从西藏带回来的’它的遗体’中提取出来的,现在还在试验阶段。这一对孩子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之一,让他为德意志民族作出最后一点奉献吧!”
哥哥在进手术室的最后一秒,看到门格勒笑了,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他不解的看了门格勒一眼,他是要救弟弟吗?
弟弟被放在手术台上,医生从金属箱子里取出了一支注射器,里面漂浮着一种蓝色的液体。他们小心翼翼的把它插进了弟弟的动脉。
一秒,两秒,三十秒。
躺在床上的弟弟突然睁大了眼睛。
弟弟活了!哥哥马上跑过去紧紧拉住弟弟的手。
然后他看到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幕。
弟弟背上迅速隆起了一坨肿块,把弟弟从床上顶起来,然后那一坨东西撑开了皮肤,变成了几只触手。弟弟的下身猛的一下裂开,一个沾满黏液的头从两腿中间长出来。
弟弟抽搐了两下,再也不动了。
弟弟变成了怪物。
时间好像静止了。
我突然感觉的我的内心有一股深不见底的黑暗蔓延了上来,在数秒之内吞噬了我所有理智和情感,这一片黑暗像地狱之门上的无数双手撕扯着我,愤怒,冤屈,暴戾,痛苦,把我切割再拼凑,撕裂在融合。
我也变成了一个怪物。
“啊!!!!!!!”哥哥叫出来。
“把他拖下去!把他拖下去!”哥哥在医生的叫嚣中和护士的簇拥下被拖出手术室。
黑夜深不见底,没有灯光,四周一片黑暗。
“弟弟,你不用怕.....你会在我身体里活下去。”
“我会成为你的眼睛。”
我听到了哥哥心底的声音。
医生在监仓外的声音若有若无的传来,大意是双胞胎的弟弟死了,就无法再配合完成读心术。失去了一半手脚的人,只能算残疾人。
哥哥不需要再去审讯室和游戏室,却成了彻头彻尾的医学试验品。
器官移植,抽取胆汁,提取睾丸素,皮试和抽血,日复一日。
哥哥的身体上满是深深浅浅的伤痕和术后创口。
只有在漆黑的午夜,哥哥的身体里的弟弟才会出来和他说话。
“哥哥,我给你取个名字好吗?”
又是那一夜,数以百计的轰炸机在生命之泉农场的顶上飞过。
医生们仓皇逃窜,一个医生撞撞跌跌的摔倒在监仓门口。
他爬起来时,才发现43号正盯着他的眼睛,数十秒后,他机械的从口袋里掏出了监仓的钥匙。
43号并没有急着逃走,他去了游戏室,选择了几样熟悉的玩具。
来到大厅,一堆军官和护士正不知所措的奔走忙碌着,地上躺满了和他弟弟一样的怪物。地上有一些注射器,里面是熟悉的蓝色液体。
43号笑了,笑的很好看,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他安静的关上了门,外面战火纷飞,没人发现他。
“我们来玩吧,弟弟。”
哥哥举起了枪。
大厅的大理石地板雕刻着非常古典的花纹,被血染得红红的。地上躺满了尸体。
所有人都死了,弟弟也死了。
哥哥安静的和一堆怪物坐在大厅中央。
他捡起一只注射器,往自己的动脉扎去。随即闭上了眼睛。
数分钟后,他睁开眼睛,看了看自己的手和脚,又看了看周围的怪物。
“你们不想我和你们一样吗?”哥哥问:“你们想让我替你们活下去?”
大厅空空荡荡,除了哥哥的回音,无人回答任何问题。
“我收下你们的仇恨了。”
“好吧,那我走了。”
好疼。
“喜欢这个梦吗?”
忽然肩膀上的巨疼刺激了我的神经,恍惚中我睁开了眼睛。
最先看到的,是一双脚,一个孩子的脚,穿着精致的皮鞋,一只皮鞋的鞋尖上有血迹。
“醒了吗?嘻嘻。还是要再来一下?”
那只皮鞋突然发力,又在我的肩膀上使劲踹了一脚。
“呃…..”我疼得冷汗直冒,睁大了眼睛,我看到了阿尔法站在镜子边上。旁边地上倒着的是玛丽亚。
“死了吗?”阿尔法又踹了一脚玛丽亚。玛丽亚的身体软绵绵的翻了过来,瞳孔已经放大了。
“哎,死透了。”阿尔法有点遗憾的说。
“她的身体太老了,已经经不起这么大的折腾。坏掉啦。”阿尔法看了看屋子里堆积如山的玩具,叹了口气:“修不好了。”
“琳娜呢?!”我咬着牙从地上撑起身体。
“她在睡觉呀。”阿尔法冲我笑笑,指了指我的身后。
“琳娜!琳娜!”我爬过去,使劲摇着琳娜,可无论我怎么叫,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对她做了什么??!”
“不要怕,她在做一个美梦。”阿尔法蹲下来,摸了摸琳娜的头发:“她正在和我弟弟玩游戏,那个梦里没有你,也没有伤害,她会很开心——她醒来时就会把你忘掉了。”
“谁不愿意发一个永远不会醒的美梦呢?你不是也看到了我的梦吗——看吧,反正你对我而言已经是死人了。”这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轻轻的说。
我突然发现,枪还在琳娜手里!我立刻用身体挡在琳娜的前面,慢慢的向琳娜的方向退过去,我必须先把枪拿到。
“阿尔法在哪里?你究竟想要什么?!”我一边问他,企图分散阿尔法的注意力。
“阿尔法?谁是阿尔法?阿尔法又是谁?”阿尔法笑着问我:“我对阿尔法这个名字已经腻了。”
“你看了我的过去,我没有名字,我弟弟也没有。名字不过就是一个代号罢了,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我杰克,也可以叫我汤姆,迈克尔,保罗,理查德…..人总是很愚蠢的以为,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就等于知道他是谁,就能给他下定义。”
“猫咪有它的名字,小狗也有名字,连一栋房子也有名字——似乎人类表达’爱’和’重要’最原始的方式,就是命名——可是名字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没有名字就代表从来没有存在过呢?嘻嘻,”阿尔法回到凳子上面,玩着手指,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我正在往琳娜的手边移动。
“我呀,就不喜欢名字,我讨厌被定义。可是我弟弟总是想要一个名字,他自己没有名字,就去偷别人的名字,他第一个名字叫凯文,他很喜欢这个名字,用了十一年,可是凯文的’爸爸’还是坏掉了;后来他又成了泰特,可是泰特的’妈妈’也坏掉了…..我忘了他偷了多少个名字,他呀,总是很天真的以为偷了别人的名字,就能成为那个人了。”
‘阿尔法’,不,是43号,他抱歉的对我笑笑,就像在替他淘气的弟弟赔礼一样。
“你看到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的玩具,它们都是我玩腻的,你也是——”凳子上的人看着我:“其实如果你没有逃过融合,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你变成我的玩具,我弟弟也可以有一个新妈妈。哎,真可惜,我已经没办法跟你融合了,我弟弟喜欢琳娜,你只能去死了。”
“融合…..!!”看着地上玛丽亚的尸体,突然恍然大悟!
“哈哈,你很聪明,”似乎猜到了我在想什么,43号开心的拍了拍手掌。
“在你睡觉的时候我会先给你的潜意识开一扇门,偷偷绕开你大脑里的自我防御,再把你心里那只肮脏的小怪物放进去。我对这个小把戏已经相当熟练啦,但是再熟练也很难一步到位,所以前几次我也只能在你做梦的时候控制你,你醒来之后我可就无能为力啦。因为前几次对你的大脑来说,我就像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它可不信任我——如果我一开始就被它发现了,它可是会排斥我的,哎呀那种感觉真难受。”43号说着似乎回忆起什么不好的事,打了个寒颤:
“可是我每天都去的话,你的大脑可就会慢慢对我放松警惕了,就像看门的狗儿不会伤害总是登门的熟人一样,慢慢的,慢慢的,它就会听我的话,对我摇尾巴,最后我就会变成它的主人——那时候你可就不是你啦!”
瓦多玛的话又浮现在我脑海:擦亮你的眼睛吧孩子,三次机会你失去了两次,下一次就再也醒不来了!
三次机会,正是因为两个意识需要至少三次磨合才能融为一体!
“所以你必须要至少三次潜入我的梦境,才能实现最后控制我的目的!你也是这样操纵约翰森的!”
“你以为控制一个大脑是很简单的事吗?三次磨合已经非常短了。但是他们选择自杀可怨不得我,我只负责把他们那点龌龊的小秘密放进梦里,至于他们为什么接受不了自杀了,这可不是我能控制的。”阿尔法无辜的摊了摊手:“我心情好的时候,就让他们死得利落点——跳楼也好吞枪也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慢慢折磨他们:就像约翰森一样,他竟然和这个该死的女人结婚,这个贱人在战后逃到美国改头换面,一下就跻身了上流社会,但我还是把她认出来了——隔多少年我也能认出来!她身边所有的人都应该承受比死亡痛苦一千倍的折磨。”
43的眼睛里充满戾气,但也就是一秒钟的功夫,他又笑了,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
“所以呀,我为他设计了一个循环播放的电影。只要他闭上眼睛,就会一遍一遍看到这个女人被割喉,放血,截肢,切成一块一块的,蒸成肉饼哦。——我不但让他睡觉,还让他醒来——我其实可以不让他醒来的。但是如果他不醒来很快就疯了,毕竟这些养尊处优的有钱人可不比我们从小训练出来的意志。他死了那可就不好玩了。他要一直活着,长命百岁,日复一日的遭受折磨。”
“你最初并不想融合我吧,你是想我死的。”我想起了我差点跳楼的经历。
“哎,怎么说呢,毕竟你太普通,不在我选择融合的范畴——没有钱也没有权利,你不能为我和我弟弟带来什么。所以我最开始为你安排了一个轻松的死法,你真该感谢我的仁慈。”阿尔法说道:“可是我弟弟他真的很想有个所谓的家,他就是这样,永远都长不大。”
“你不用去拿枪了,你在伸出手的瞬间我就能让你爆头。”43号笑了笑:“但我今天心情不错,所以我想跟你玩一个游戏——”
“——当年我离开生命之泉农场的时候,把剩下的注射器都带出来了。”
————————————————分楼层————————————————
各位可爱的美丽的英俊的读者们,我今天又迟到了半小时,一会发个红包,默默的把这个锅背了:)
门格勒和希姆莱,历史上确有其人,至于他们的实验我不能说太多,该写的我会写进小说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谷歌一下。
与其说当时的实验无比残忍,不如说战争本身就很残忍。但因为这个疮疤太丑恶,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揭开它。所以哪怕现在在国外和欧洲,大家都会对那段回忆避而不谈。
然后,慢慢的就忘掉了。
露珠没有办法去写一篇改变世界的文,但是露珠希望通过自己幼稚的文笔,让更多人了解战争可怕,和它对无辜的人有多大的伤害。也希望看我文章的读者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每个人都能了解到战争的可怕,就会对别人有更多的包容。正义,金钱,权利,都没有生命来得重要。
么么哒~
——————————————分楼层——————————————
是我在梦里见过的那只金属箱子,边缘已经凹凸不平,上面刻着双闪电的标志。
43把箱子打开,里面装着两只金属注射器,中间的凹槽有一块透明玻璃能看见里面的蓝色液体在黑暗中闪着诡异的光芒。
43冷漠的看了看地上的玛丽亚。
“本来这一支是要留给她的。这个女人就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要不是你捣乱,我还能再折磨她十年。”
说着他蹲在我的面前,他身高还没有一米四,语调平静缓慢,但我却像听到了野兽的磨牙声一样,身体无法遏制的发抖。即使我的大脑正在强迫自己冷静,但是还是身体本能的往后退。
“我今天心情不错,我允许你选择一种死法:在梦里和你的小杂种一起玩十年再死,或者现在来上一针。但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我给你三秒吧:3,2,1.”
我还没反应过来,43就笑了:“那就怪物好啦——”
他抬起手向我扎过来,突然一个趔趄,琳娜动了动身体。
43再抬起脸的时候,竟然有一滴眼泪从眼睛里落下来。悲伤,是阿尔法才会有的表情。
“你就不能再坚持一会吗!没用鬼!”
阿尔法又迅速翻了一个白眼,脸上的悲伤迅速褪去——说话的是43.
同一张脸,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情快速交换着。
“那不是她要的….”
阿尔法失望的垂下了眼睛,擦了擦眼泪:“哥哥,够了….”
“不要打扰我!”43的瞳孔一下紧缩,随即恢复了那张没有情感的冷漠脸孔。
我连忙扶起琳娜,琳娜的眼睛里盈满泪水。
“琳娜!你怎么样?是不是做噩梦了?你梦到什么了?”
“我做了一个很美的梦,梦到我的dream house,大花园.......”琳娜一边哭一边摇头。
“你为什么要醒来?” 阿尔法低头看着琳娜,声音低沉。
“是很美…我在梦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我很平静,很安逸,可是我总觉得少了什么....….我想不起来,我一直想,很努力的想,”
琳娜按着胸口,拉紧了我的手:“我想起了你,你不在那里….所以我知道那不是真实的。”
43拍起了手。
“不恨欺骗你的人,反而爱他,我该说什么呢….”
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下一瞬间,他收起所有笑容:“我只能为你的愚蠢感到惋惜!”
说着,他把针朝琳娜扎过去!
“不!”我下意识的用整个身体护住琳娜,背后随即传来一阵刺痛。
时间在一瞬间变得很慢,很慢。
世界在我眼里,变成了从宏观,到微观,无穷无尽。
我看见地上的一颗灰尘因为冲击飞扬起来,飘落到了琳娜的发丝上。
发丝在空中打了个转,粘上了我没干的一滴血。
血滴被发丝反弹到皮肤的细纹上,就像干涸的黄土高原忽然多出了一片红色的湖泊。
湖泊里浮动着一颗颗红血球,细胞在快速的裂变、融合。
细胞的内核,转动着一条螺旋形的基因链,里面包裹着无数染色体。
染色体里面,是一个浩瀚无垠的宇宙,那么近,那么远。
在宇宙中心,突然多了一颗蓝色的液体。
它越涨越大,开始吞噬周围的星球。
它就像一个吃不饱的孩子,最终吃掉了一个宇宙,吃掉了染色体,吃掉了基因链,吃掉细胞和红血球,吃掉了我和琳娜,和整个世界。
它越吃就变得越大。
然后它就毫无预兆的爆炸了,爆炸所及之处一片黑暗。
我又来到了那扇门面前。
不过几分钟没见,却像过了数亿年。门上的黄铜早已化为沉泥,连花岗岩都成了化石。
没有地狱的使者,也没有撕裂的心脏。门上剩下的只有斑驳模糊的纹路。
就好像它曾在无数世纪之前被层层雕刻,又在无数世纪之后腐朽剥落。
门仍然紧闭着。
我忽然有种熟悉的感觉。
就像一生飘零异乡的旅人,在万里跋涉后,站在山岗上看到彼岸朦胧的家的灯光。
我的大脑里,这种感觉像羽毛一样轻盈的划过,又像暮鼓晨钟一样回荡。它并不是在语言,而是在用一种情感对我诉说:
回家吧,我的孩子。
温柔,就像是被妈妈抱在手里轻轻的摇晃。
从出生,到死亡。我一生的记忆都涌了上来,然后又在模糊中淡去。
身体催促着我往前走,我推开了一个门缝。
门缝后面,是两颗彼此相连的星球,链接他们的是一条银色的河,在寂静的宇宙中发出蓝色的光。
像一对双生子一样。
我把门一点点推开,门的那边,有一股力量在吸收我的身体。
从我的血液,到骨骼,到器官....我感到从没有过的放松和舒服。
我慢慢的往门的另一边走去….
谁在说话?
好像是个女人,她好像在哭。
“磊…..”
磊是谁…..
琳娜!
我一瞬间清醒过来,拼命用手撑住了马上就要关住的门!
我不能过去!琳娜在叫我!
“你是谁?”
这一次换成43问我了。他不解的看着我,手上还拿着注射器,里面蓝色的液体已经消失了。
我怀里抱着的是琳娜,我摸了摸我的背,刚才的刺痛已经没有了。
我看了看我的手脚,又摸了摸自己的脸。没有变化。
刚才的一切都发生在几秒之间。
我和43对视着。
他突然哈哈大笑。
“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我没碰到过这么好玩的玩具!我要你!我要你!”
他兴奋的说:“我怎么没想到呢,你的梦里那个小怪物和生命之泉农场的长得这么像!我太粗心了,中国人,你也从西藏来!”
“我们是一类人,”他忽然盯着我的眼睛:“让我看看你的记忆!”
“你很痛苦吧?”我打断他的话。
“哼,”43愣了一下,随即不屑的哼了一声:“该杀的我都杀了,该报仇的我也报了,我是被选上的人,低等生物拥有的情感在进化的过程中已经被我排泄掉了。你以为我是我弟弟吗?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
“不,我是说你很痛苦吧,”我说:“和阿尔法生活在同一个身体里很痛苦吧。”
“你骗了阿尔法,你从来没想过要让琳娜维持自己的意识成为阿尔法的妈妈。琳娜是下一个玛丽亚。你们两个,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无法生活在同一个身体里了吧。”
大家这两天给点耐心啊 露珠是一个智商很低很没逻辑的人 为了能把故事写好要很仔细的过一遍整个故事的逻辑有没有bug,除了填坑以外,露珠更希望任何人之间的情感不会有什么大bug^_^所以陷入了永恒的逻辑脑洞中(头要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