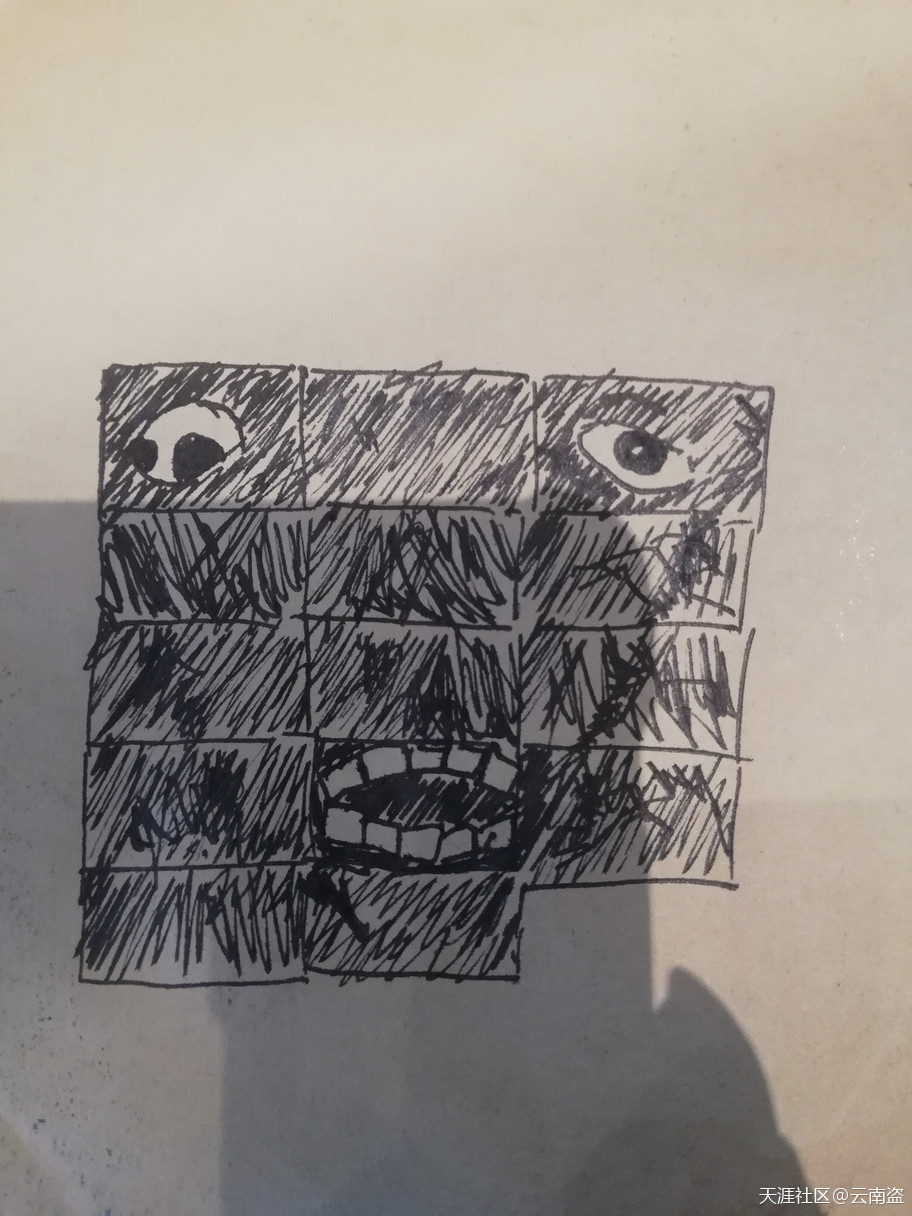老眼一愣,随即瞟了日求一眼,站立不动。
“才嘎!”日求命令那个手下:“看看啥东西。”
那人20多岁,瘦瘦的,捡起铁板,来回看了看:“就是个板板。刻了字。”
日求走过去,接过铁板,看了看,问老眼:“啥东西?”
老眼嘿嘿一笑,不吭声。
日求回过头,问我:“啥东西?”
我瞟了老眼一眼,他也盯着我,有些狰狞,我赶紧摇摇头:“不知道。”
日求狐疑看了老眼一眼,把铁板递给那瘦子:“放好。”
瘦子接过,摆弄了几下,掀开衣服,插进腰间。
“小铜钱!”日求道:“你手里啥东西?”
我一看,小铜钱手里有一个土黄色,像小瓶子的东西,他正拿着看。
日求几步过去,一把抓住那东西,看了一眼,忽然脸色大变。
“你哪里来的!”他厉声问。
所有人都吃一惊,小铜钱张口结舌:“我——我也不知道的嘛。”
“有人给他的。”旁边,一人忽道,声音有气无力。
我一喜:是陈舜年,他醒了!
“舜年!”黎兰高兴得不行,几步跑过去:“你怎么样?”
“死不了。”陈舜年挣扎两下:“日求叔叔是吧。”
日求警惕看他:“是。”
“先回营地吧。”陈舜年瞟了一眼小铜钱:“有个事,我要单独给你说。”
又走了10多分钟,在一个山坳处,我发现了我们的帐篷。
顿时身体像散架,靠在石壁上,动也不想动,老眼蹲在一边,被那个叫“才嘎”的瘦子用枪指着,“迷彩服”则坐在旁边抽烟,小铜钱跑进帐篷,找了两张馕饼,出来分给我一张,挨着我,大口吃,我早饿得不行,三两下吃了大半进去。
这时注意到帐篷里头,黎兰,陈舜年,还有日求,一直在里头说话,半天不出来,我瞟了一眼小铜钱,他一脸满不在乎的模样,我不由暗自狐疑:一定跟那个“小瓶子”的东西有关,听陈舜年语气,似乎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待会儿得问问他。
忽然想起一件事,一个激灵,一下坐起来!
对了,冯华!
这才是最最最重要的事,一分钟耽误不得!得马上找陈舜年商量,看看他的意见!
赶紧三两下吃了东西,这时帐篷掀开,日求钻出来,向小铜钱招手:“过来!”
小铜钱马上跑过去,边跑边啃馕饼,跑近,日求摸摸他脑袋,一脸怜惜。
“喝不喝水?”
他边说,边解下身上的一个行军水壶。
小铜钱拿过,“咕嘟咕嘟”猛喝几口,日求摸着他脑袋:“慢点!噎死了!”
我暗暗狐疑:他表情突然变得奇怪,一定出了事!
这时黎兰也钻出来,朝我招手:“你进来!”
我早就等得不耐烦,赶紧跑进去,陈舜年正斜躺在一个包裹上,脸上缠了一圈纱布,把右眼遮住。
我赶紧压低声音:“那个日求怎么回事!”
陈舜年惨笑了一下:“我见到一个人。在神庙里头。”
“谁?”
“像是小铜钱父亲。”
我一惊:“他爸?”
“应该是。”陈舜年道:“当时我正好醒过来,看见有个人正把小铜钱丢下来,是个坨人。”
我一凛:“男的女的?”
“像是个男的。”陈舜年道:“当时太乱,没看清楚,那人丢下来,看了我一眼就走了,我当时也起不来,好在小铜钱一会儿就醒了,这小孩,男子汉,我叫他跑,他不跑,坚持把我拖出来,好!孺子可教!”
我不由脸发烫:“那,刚才他手里啥东西,就那个小瓶子?”
“是个鼻烟壶。”陈舜年道:“日求说,是他父亲家里祖传的,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说是87年他们失踪,那个东西就在他父亲身上。”
“87年!”我一凛:“那个地质大队?”
“对。”陈舜年点头:“他们当时进了那个队伍,是背夫。”
我点点头:“他居然没死。”
“唉——”陈舜年摇摇头:“跟死没有区别。”
“日求想进去找?”
陈舜年惨笑一下:“找到了又如何。”
我一下想起一事:“对了!有她的消息!”
“谁?”
“冯华!”
陈舜年一惊:“怎么回事?”
黎兰也一下凑过来:“冯华!在哪里?”
陈舜年挥挥手:“女人出去!”
黎兰一愣,哼一声,钻出去,蹲在门口扯帐篷。
我赶紧道:“我碰到安青了!”
“安青!在哪里?”
我心说在墙壁里头,你信不信。
“反正我碰到她了。”我道:“她居然问我信的事情!”
“信!”陈舜年眼睛一亮:“冯穆人的那封!”
“应该是!”我道:“我就问她!她说是个女人给她的!我估计就是冯华!”
陈舜年点点头:“人在哪里说没有?”
“她只比了个手势。”
“怎么比?”
我伸出左手食指,指了指左眼珠:“她指着左眼珠,然后,右手比出一个‘二’。”
“二?”
陈舜年一愣:“什么意思?左眼珠,二?”
“挖眼睛!”外面,黎兰忽道。
陈舜年一皱眉:“什么乱七八糟!”
黎兰钻进来,右手食指中指伸出来:“是不是挖的手势嘛!挖左眼?”
我一下呼吸急促。
“不对。”陈舜年道:“不是这意思。小关问的是人在哪里,怎么会比出挖眼珠?不对。”
我赶紧点头:“对对!应该不是挖眼睛!二,眼珠......”
陈舜年一皱眉:“我觉得应该跳出眼珠的思维范畴。”
我一愣:“怎么说?”
“我感觉安青说出的是一个地址,不是眼珠。”
黎兰不解:“那她指自己眼睛怎么解释?”
陈舜年皱起眉:“眼珠......会不会,是一个类似眼珠的地理位置?”
我一凛,忽然想起一事:“对了,瞳——”
“瞳图!”陈舜年也同时说出。
我顿时一股恶寒:眼珠!二!莫非是——
“双瞳。”陈舜年忽道。
双瞳图!
我也一下反应过来:“笔记!”
陈舜年伸手一摸,摸出一物,正是他父亲的那本笔记,他飞快一翻,翻到一页,上面赫然出现一只诡异“人眼”,里头两颗黑色“眼球”,周围则被画成一片漆黑,正是那幅《双瞳图》!
陈舜年点点头:“说不定,是指湖。”
我一愣:“你说这只眼睛?”
“对!”
他翻了翻,翻出那张“瞳图”,一指:“这只人眼已经证实就是那座盐湖——”
他马上翻回“双瞳图”那一页:“那这只人眼——”
“也是一座湖!”我点点头:“那,这两颗眼球,又代表什么?”
“会不会——”陈舜年一皱眉:“也代表那种鱼?”
“麻扎神鱼!”黎兰忽道。
陈舜年一愣:“什么?”
“你是不是说那种大鱼?”黎兰道:“我听他们说,那个叫麻扎神鱼,是从麻扎雪山里头孵出来的。”
陈舜年没听懂,看我一眼:“什么意思?”
“是个传说。”我赶紧道:“是日求他们说的,说这儿的两排雪山,一座公,一座母,然后母山里头有一个子宫,对了!你昨晚看见没有,那个子宫!”
“就那座巨石?”
“你看见了?”
陈舜年点点头:“那是子宫?”
“对。”我道:“他们说那种神鱼就是从里头孵出来的,对了——”
我压低声音:“说还孵出来一只铁羊。”
“铁羊!”
“是。说是个羊头人身的怪物!说还没孵出来,就把子宫咬烂了,最后被砍成三段。”
“铁羊......”陈舜年点点头:“羊鬼沟沟!”
我不语,跟他对视。
“那,分成三段之后呢,是埋了,还是怎么?”
“他们没说。”我道:“但我当时忽然想起一个东西,跟你父亲有关。”
“什么?”
“就那座古坟。”我道:“乐山锣场村那座。徐万忠不是很肯定那里头那具棺材,说你父亲曾经埋在那里,他很肯定这点,这个先不说,就是棺材里头有一幅画,我给你说过,你还记不记得?”
陈舜年一皱眉,一下想起:“毒兰坨?”
“对!”我道:“画上画出了毒兰坨,然后从那里头伸出三根曲线,现在左边那根确定,是指怒江,中间那根是岷江,就是右边那根现在搞不清楚是哪条河流,我刚才就一直在想,三条河流!最后末端的三个点!神木岭!锣场村!还有另外一个目前不明的点!最后关键是,那具铁羊,被分成三段——”
“——分成三段!”陈舜年立马接口道:“分别埋在三个点!”
“对!”我点头:“有没有这种可能!”
陈舜年双眼露出怪光。
“还有那种黑沙!”我突然感觉无比兴奋:“羊鬼沟沟!锣场村!都有!全部都是!还有!羊鬼沟沟的黑沙,最后变得像一只羊脸!锣场村!最后冒出一个怪物!是黑沙形成的!没有肉,没有骨头!就全是黑沙!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是个羊怪!羊头!人的身!就站在我旁边,就在那儿疯了一样,卷!最后,缩下去!消失!徐万忠!跟疯了一下,就下去了!你说!底下会不会就埋的是——”
陈舜年深深吸一口气。
旁边,黎兰明显也被我吓住,一脸惊恐,抓住陈舜年胳膊。
一时帐篷陷入死寂。
我重重喘息一口,只感觉口干舌燥。
陈舜年也沉沉呼出一口气,死死盯住那幅《双瞳图》。
“父亲。”他忽然喃喃道:“你画这些画,想告诉我什么......”
黎兰忽然身子一抖:“哇!”
我跟陈舜年都一愣:“怎么?”
黎兰猛一下蒙住眼睛,指着图案:“那个眼珠——”
“怎么?”
“就里头那个小眼珠!”黎兰蒙住眼:“”好像——刚才动了一下!”
我一凛,一看,图上“眼眶”里头,两颗“眼球”一左一右,左边那颗小的是多出来的“怪瞳”,露出一半,剩下一半“隐藏”在眼眶里头,似乎没有异常。
“别闹。”陈舜年没在意,对我道:“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幅‘石碟图’,我父亲是从哪里看到的?”
我一愣:“鱼腹上?”
“我感觉不是。”陈舜年摇头:“我发现我们之前忽略了一件事。”
“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父亲不画出那只鱼?”
我一愣,隐隐感觉异常。
“我们设想一下。”陈舜年道:“32年我父亲跟随冯穆人进了底下那个山洞,就算神庙吧,他们进了那座神庙里头,发现了倒头祭司,还有一只神鱼,神鱼腹部出现了一幅图案,就是‘石碟图’,他们就把它画下来,这很正常,但是他们为何没有画出那只鱼?”
我一皱眉:“为什么?”
“搞不懂。”陈舜年摇头:“照理说,突然看见头顶出现一座盐湖,里头还出现如此神奇的一条鱼,无论是谁,都要被震骇住,不可能不画出来!就算不画出来,笔记本里头居然对‘鱼’的事情只字不提,这点就非常不合理。”
他顿了顿:“只能这样解释,他不画出来,一定有一个不画出来的理由。”
这时我注意到旁边,黎兰身子忽然抖了一下。
一看,她正死死盯住那幅《双瞳图》,嘴巴张开,露出惊骇神色。
“怎么了?”
我问了一句,立马去看那幅图案,顿时一股恶寒:“眼眶”里,那颗“怪瞳”很恐怖的,突然变小了,似乎往眼眶里“缩”了一部分进去。
陈舜年也同时发现了:“嚯!怎么回事!”
我也头皮发麻:“褪色了?”
陈舜年伸出手指,在那“怪瞳”上摸了一下:“不对!是自动变小了!”
我只感觉喘不过气:闯鬼了!
只感觉旁边,黎兰无声无息,不由瞟她一眼,不由一震:她仍死死“盯”住那幅图案,但很恐怖的,两只眼睛里头,两个眼珠都往上翻,就像在“翻白眼”,睫毛剧烈抖动,感觉两个眼珠都快完全翻进上眼眶里头去了,只剩两道黑色边缘在外面。
“黎兰!”我吼了一声。
陈舜年也一下看见了,一惊:“黎兰!”
边说,边“啪”的给了她一耳光。
黎兰忽然一伸手,一把抓住笔记本,一下扯过来,只见她两个眼眶里头,眼珠已经基本没入眼眶里头,剩下两道眼白。
“你干什么?”陈舜年吼了一声,去抢。
黎兰却忽然倒退几下,一下退出帐篷,同时双手在笔记本上一阵乱撕,三两下就撕下好几页,散在周围。
那头,日求,小铜钱他们也发现异常,都站起身,很紧张朝这头张望。
“放手!”
我吼了一声,扑过去,双手抓住笔记本,只感觉被黎兰抓得死死,兀自还在撕。
“放!”
我死命一扯,一下把笔记扯脱,一屁股坐回帐篷,顺势给了她肚皮一脚。
黎兰一下仰面倒在地上,双手兀自在半空乱抓,就像在“撕”东西。
帐篷里头,陈舜年坐起来,想爬出来,却一屁股坐下,明显伤口很疼。
我赶紧站起来,就见黎兰倒在那儿,已经放下手,不住剧烈喘气,再一看她眼睛,两个眼珠已经翻出来,恢复正常,但看表情,很茫然,就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周围,胡乱散落了七八张撕下来的纸。
这时日求跟小铜钱都跑过来,日求问:“她咋了?”
陈舜年也挣扎几下,慢吞吞移动出来,我把笔记本丢给他,赶紧去捡那几张纸。
“等一等!”他忽道。
我一愣:“怎么?”
他不语,爬出来,捡起两张纸,正是那张《双瞳图》,还有一张《牙图》,《双瞳图》中央已经被拦腰撕开一道口子。
只见陈舜年看了看两张纸,两眼忽然发出怪光,他随即放下,放在地面,把两幅图一上一下,拼在一起。
我不解:“怎么了?”
陈舜年不语,翻开本子,一撕,把那张《瞳图》也撕下来,拼在《双瞳图》右边,然后盯着看。
我隐隐感觉出问题,也凑过去看。
只见左边是一个恐怖“双瞳”,右边是一只普通人眼,底下,赫然出现一排“白牙”,感觉就像一张被毁容的脸。
“像不像脸。”陈舜年道。
我顿时呼吸急促:“像!”
陈舜年不语,三两下把笔记本后面那10多页全部撕下来,那上面全是用钢笔涂成的不明图案,绝大部分都是一团漆黑。
这时日求,小铜钱,迷彩服都围过来,黎兰也坐起来,披头散发,一脸迷茫看着我们。
陈舜年把所有撕下来的纸平铺开来,仔细观察一阵,开始拼。
我们都一声不吭,站在旁边,那头,那个才嘎也伸长脖子,凑过来看,老眼则躺在石壁下,双眼闭上,已经睡着了。
这时陈舜年站起来:“差不多了。”
我赶紧一看,地面上拼出了一张怪异“人脸”,在两只“眼睛”中间又多加了一张纸,而跟“牙齿”之间,多加了好几张纸,显露出一张比较完整的“怪脸”,黑森森,露出两个眼睛,下面,就像“嘴唇”被烧掉了,露出一排恐怖“白牙”,整个看起来就像一张刚刚被大火“毁容”的人脸。
而旁边还有八九张纸,陈舜年没有拼上去,应该是不知道拼在什么位置。
陈舜年又蹲下去,指了指那只“瞳图”。
“这个是那座盐湖。”
他又指了指那只“双瞳”:“她,莫非就在这里?”
我心头“突”一跳:冯华!
赶紧蹲下去:“你是说,这是一幅地图?”
陈舜年盯了几秒,忽然抬起头,问日求:“这儿附近有没有一座像眼睛的湖?”
日求也蹲下来:“怎么?”
陈舜年指着那只“双瞳眼”:“我是说麻扎雪山周围,就这一带吧,有没有一座盐湖,形状像人眼?”
日求盯着“双瞳眼”看,一脸狐疑,不答。
“这是人的眼睛嘛?”小铜钱好奇问:“有两个的眼珠珠?”
“小孩子闭嘴!”日求喝道。
这时我注意到“迷彩服”露出一个疑惑神色。
“他好像知道。”我指了指他。
陈舜年一愣,赶紧问:“怎么,兄弟知道?”
迷彩服迟疑道:“好像听人说过的嘛,那头有两座古盐湖......”
“古盐湖?”陈舜年问:“古代的盐湖?”
“是的嘛。”迷彩服朝我们左方一指:“好像在祁曼塔格山那边。”
“祁曼塔格山!”陈舜年一愣:“这么大一个范围,具体呢,具体在什么位置?”
迷彩服摇头:“这就不知道了嘛,我也是听说的嘛......”
我想起一个问题,赶紧问:“你怎么突然想起那两座盐湖?”
“哦。”迷彩服朝《双瞳图》一指:“我只是看里头这两个眼珠珠有点像的嘛。”
我一凛:“怎么个像法?”
“那两个盐湖也是一大一小的嘛。”
迷彩服像想起什么,补充道:“你们就算找到也没用了的嘛,那两座盐湖早就没了的嘛,好多年前就干没了......”
我跟陈舜年对视一眼,心头都是一个想法:莫非,这两颗“眼球”,是代表两座湖?
正想继续问迷彩服,“砰”一声巨响。
声音来自我们左边,远远的传到对面雪山上。
我一个激灵:有人开枪!
扭头一看,只见那个“才嘎”正歪倒在地上,老眼坐在他旁边,手里举着之前才嘎手里的步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们,兀自有青烟冒出来。
“都不要动。”老眼阴森道。
这下猝不及防,我们全部僵住。
只见才嘎蜷缩在地上,不住呻吟,双手抱住左腰间,有血正涌出来。
日求忍不住,往前走了一步。
“不要动。”老眼道:“再动,老子一枪打死你。”
日求哼一声:“我不信你敢开枪。”
“早十年。老子也不信。”老眼一脸狞笑:“把钥匙丢过来。”
日求一脸铁青,不动。
“我数三声。”老眼道:“不丢,我打死你,一!”
日求不动。
“二!”
日求还是不动。
“三!”
日求右手忽然抽动一下,几乎同时,“砰”一声,老眼开枪了。
我只感觉耳朵“嗡——”一声,下意识扑倒,旁边,黎兰尖叫了一声。
抬起头,只见老眼仍坐那儿,一脸阴笑,枪口兀自在冒烟,再一看旁边,日求已经跪在雪地上,脑袋耷拉,左手摁住左下腿,那儿正在冒烟。
“钥匙!”老眼阴阴一笑:“我再数三声。三声完了,就是脑袋。一!”
日求身子忽然动了动。
“二!”
日求右手一下扯出一个东西,丢过去,是一串钥匙,落在他跟老眼中间。
老眼移动了一下,却够不着,突然朝我阴笑:“你!过来捡。”
我一愣,一时不知所措。
“别过去!”身后,陈舜年道。
“陈老板,不要不识抬举。”老眼嘿嘿一笑:“我之前放过你两次,事不过三,你不要惹我。过来!”
他最后一句是对我说,我迟疑一下,慢慢走过去,捡起钥匙,就要丢给他。
“你过来。”老眼道。
我一凛:他要把我当人质!
咬咬牙,站住不动。
老眼瞟了一眼我身后,忽然压低声音:“你是不是在找一个人?”
我一愣:“什么?”
“那个‘双瞳’——”老眼从牙缝里头挤字:“我知道在哪里。我带你去。”
“什么双瞳!”我还是不动。
“你少给老子装!”老眼道:“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地方,有两座盐湖,一大一小像两个眼珠?”
“你知道?”
老眼点点头:“我带你去。”
我咬咬牙:“在哪里?”
“嘿嘿!”老眼阴阴一笑:“你信我,就跟我走。不信,滚回去。”
我重重呼出一口气,回头看了陈舜年一眼,他正一脸严峻盯我。
冯华!
我拿定主意:“好!”
老眼咧嘴一笑:“识抬举。过来,先把手铐打开!”
我咬咬牙,几步过去,找到手铐钥匙,三两下打开。
老眼右手举枪,左手一把扯过钥匙,瞟了一眼,嘿嘿一笑:“好!居然给老子留了一辆车。谢了,日求队长。”
日求仍跪在地上,左腿上的血已经把雪地浸红,一张脸疼得完全扭曲。
“来。背老子。”老眼道。
我一愣。老眼嘿嘿一笑:“你不背。老子怎么带你去?”
我没办法,只好把他背上,只感觉沉重无比,他不停粗声哈气,热乎乎的口臭哈在我后脖子上,异常难受。
“都不要动!”老眼朝他们喝道:“哪个动,我打死哪个。走!”
我不由看了陈舜年一年,他也正看着我,摇摇头,叹口气。
这时小铜钱忽然冲过来几步:“我的钱!还给我!”
“别过去!”陈舜年厉声道。
老眼嘿嘿一笑:“来,小朋友,过来拿你的钱。”
“过来!”陈舜年吼道。
小铜钱站那儿,盯着我,大口喘气,忽然就跑过来,手一伸:“还给我!”
“嘿嘿!”老眼狞笑道:“你胆子大。不像他们几个脓包。跟我下去,我有办法还你钱。”
“什么办法?”小铜钱不动。
“下面有刀。”老眼笑道:“一刀把这个叔叔的手砍下来,不就还给你了,嘿嘿嘿!”
“阿西贡!给老子过来!”日求忽然咬牙吼。
我一凛:小铜钱原来叫“阿西贡”!
“走!”背上,老眼喝道。
我再不犹豫,转身就走。
“阿西贡!”日求声嘶力竭吼。
“我要拿我的钱!”小铜钱叫道:“尼塞爷爷说了,钱丢了我要短命!”
“尼塞爷爷骗你的!”日求吼。
“他不会骗我!”
小铜钱叫一声,疾步跟上来。
“几位放心!”老眼忽然大声道:“我范春龙不会杀小孩子,借用一下,到时候包退!嘿嘿!”
“阿西贡!”
日求还在吼,声音已经远了。
我不由回头一看,小铜钱已经匆匆跟上来,50多米远的山坳里头,所有人都直愣愣望着这边,如同一群石雕。
沿着雪山“脊背”,我们三个快速逃离,我只感觉心头一阵阵“空”,好像已经成了一个逃犯,正亡命天涯。
不由咬牙暗骂:妈的死老眼,等老子缓过劲,要你好看!
咬牙背了他半小时,实在背不动,只好放下,扶住走,后面,小铜钱不紧不慢跟着,一声不吭。
我忽然感觉不对:小铜钱明显是个负担,老眼怎么突然要他跟我们去?
莫非有什么图谋!
一时想不通,又走了一个多少时,太阳已经悬在了头顶,前方雪山望过去,是一块青黑色荒漠,直通天际。
我不由有些恍然:昨天就是从那儿过来的,这才一天不到,险象环生,九死一生,恍惚间就像重生一般。
到了山口,往下一看,底下出现三个黑点,正是那三头骆驼,旁边停了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应该就是日求他们开来的那辆。
于是扶住老眼,小心下山。
一路无话,很快下到山底,那三头骆驼正悠闲吃粮草,旁边是一辆“北京”吉普,开门进去,一股柴油味,老眼坐上副驾,小铜钱犹豫了一下,爬上来,手一伸:
“钱!”
老眼回头嘿嘿笑:“你跟我们走。等办完事,一定还给你。”
“要多久的嘛?”
老眼脸一沉:“第一听话。第二不要多嘴。我保证把铜钱还你。”
小铜钱不吭声。
我发动汽车:“哪个方向?”
老眼辨认了一下,手朝西南方一指:“开车!”
车子摇晃两下,启动,我不由问:“去哪里?”
“老子想一下。”老眼翻眼一想:“大概70多公里,狗日的就是名字有点长,亚达他哥西里古村。”
我一愣:“什么村?”
“不好记?嘿嘿。”老眼阴笑道:“翻译成中文,叫吞鬼村。”
吞鬼村!
我只感觉一股寒意。
“吞鬼村!我听说过的嘛!”后面,小铜钱忽道。
老眼点点头:“嗯。怎么说的?”
“说那个村子住的全是通什么族的人!”
“通古斯族。”老眼点头。
“对对对!”小铜钱道:“就是通古斯族人!”
通古斯!
我忽然想到一事:通古斯体!
那种神秘的“盐”,就叫“奥陶纪通古斯体三阶碳酸盐”!莫非......
“还怎么说?”老眼继续问。
“说那个村子专门出‘僵布’。”
“对。”老眼咧嘴一笑:“谁告诉你的?”
“尼塞爷爷。”
我一愣:“‘僵布’是什么?”
老眼一指小铜钱:“你问他。”
“是一种画的嘛。”小铜钱道:“人皮做的画。”
“人皮!”我一凛。
“是的嘛。”小铜钱倒满不在乎:“尼塞爷爷就要做僵布,偷偷做的嘛,卖给外面来的大老板,要卖几千块钱一张的嘛。”
“尼塞爷爷......”老眼若有所思:“等办完事,你带我去见他。”
“我不带你去!”小铜钱摇头。
“嘿嘿。”老眼阴笑:“由不得你。”
小铜钱不吭声。
一时车内很沉默,车窗外面全是荒漠,看不到边。
这时老眼伸手一摸,摸出那块黑色铁板,上面竟然有血,应该是那个“才嘎”的,老眼伸手擦了擦,盯着看,看了一阵,我注意到他嘴巴急速翻动,似乎在念。
我不由瞟了一眼铁板,上面密密麻麻,赫然刻的是“西夏鬼字”!
我猛的一股恶寒:老眼——他认识这种字!
我的个天!
我顿时浑身燥热,握方向盘的手也禁不住抖动。
老眼却没注意,仍盯着铁板看,边看边无声念。
我实在忍不住:“什么东西?”
老眼不理我,一直默念,念完,翻到背面,我瞟了一眼,一凛:上面空空荡荡,就在中央刻了一只“鱼”。
那种神鱼!
“神册。”老眼道。
我没听懂:“什么册?”
老眼又翻到正面,盯着看,忽然倒吸一口凉气。
“那张纸给我!”他忽然道。
我一愣:“什么?”
“就那张!说了瞿婆那张!”
我暗暗狐疑,没时间想,赶紧摸出那张纸,已经皱皱巴巴,老眼一把扯过。
他展开,开始念:“......半载后暴毙,面如陌鬼!陌鬼!陌鬼!陌鬼!”
他忽然嘿嘿一笑;“你猜一下,陌鬼是什么意思?”
我一皱眉:“陌鬼......陌生的鬼?或者,他们那地方的一种鬼?”
“嘿嘿!陌鬼!”
老眼指了指铁板:“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你说的什么神册?”
“嗯。”老眼点头:“是放在棺材里头,一般都放在尸体的背上,写给神灵看的东西,里头是尸体的身份,生辰八字,还有死亡原因。”
我一凛:“你是说,这块铁板上,写的那具石俑的身份?”
“不是那个石俑。”老眼道:“是那个女人。跟李德明一起下葬,进棺材的那个女人。”
“对对!”我赶紧道:“应该是她!你之前说了,她当时没死,没有进棺材,放了一具石俑来以假乱真!”
老眼点点头,指着铁板:“这上头写了这个女人的名字。”
我一凛:“她叫什么?”
“‘半载后暴毙,面如陌鬼’”老眼忽然嘿嘿一笑,扬了扬那张纸:“写这段文字的人,看来是个高人,深不可测。”
我没听懂:“这么说?”
“陌鬼。嘿嘿。”老眼阴笑道:“这个女人,照神册上说,叫魏陌氏。”
“魏陌氏!”
我缓缓重复一遍:“陌鬼!魏陌!”
“那就全对上了!”老眼嘿嘿笑道:“瞿宗寅最后果然把这个女人身上的覆疰转移到自己身上,果然!”
我一凛:“使用那种移疰?”
“应该是。”老眼道:“事情再清楚不过,995年,瞿宗寅从甲底乡出发,带走了那部《食血经》,996年,她见到了李继迁,然后使用经书,让李德明感染上覆疰。”
我想到一事:“为什么也让这个魏陌氏感染上?”
“估计是陪葬。”老眼道:“这个魏陌氏看来不是一般人,多半是李德明的妃子之类,绝对很得李德明的宠,男的死了,女的跟着陪葬。”
“所以就也一起被感染。一起下葬!”
“只是没想到她最后没有进棺材。”老眼道:“肯定中间出了什么问题,最后结果就是她没有跟李德明一起放进那座古墓。”
“你估计什么问题?”
“这谁知道?”老眼道:“但有一点很肯定,她当时一定使用了一些手段,让瞿宗寅使用了移疰之术,转移了覆疰,之后,1009年,瞿宗寅回到甲底乡,当时她已经病发,属于第二阶段,半年后死了,死之前脸变成了魏陌氏的脸,不过这里头有点说不通——”
老眼顿了顿:“照理说,这种事情本来应该属于绝密,怎么最后居然被记录成册?”
“出篓子了。”我道。
老眼点头:“对,出了篓子,走漏了风声,被传出去,不过这个记录的人也很隐晦,不敢直接写她变成了魏陌氏的脸,记录成陌鬼,嘿嘿,让你们慢慢猜。”
我摇摇头:“陌鬼。魏陌氏。这很容易就看得出来,有什么好猜?”
“你懂个屁!”老眼道:“‘魏陌氏’这三个字是直到老子拿到这块铁板神册,老子告诉你才知道的,我实话给你说,92年老子第一次进那座墓,就发现那个女人很神秘,感觉有问题,后来进了劳改营,我也问过几个人,但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估计‘魏陌氏’这三个字,多半是这个女人本来的名字,乳名之类,之后,她变成李德明的妃子,又另外取了一个名字,所以一直查不出来,对了说起名字——”
老眼扬了扬那张纸:“这人叫什么名字。”
“谁?”
“这张纸一看就是从哪本医学古籍上撕下来的,写书的是谁?”
我摇头:“不知道。当时吴兴禄没说。”
“吴兴禄。”老眼沉沉点头:“等这件事完了,得去会会他。”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么说。37年也是这样,瞿荣民也是使用那种移疰,从夏文衡身上转移了覆疰。”
“差不多。”
“我就有点搞不懂。”我道:“她为什么非要选自己?”
老眼点点头:“你说?”
“我的意思是,这毕竟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关系到自己的命,好,你说60年后,可以复活,谁见过?他们为什么不找其他人,进行转移,为什么要选自己?”
“问的好。”老眼笑道:“十年前,我也问过她同样一个问题。”
“她?”我一愣:“谁?”
老眼嘿嘿一笑:“我老婆。”
“你老婆!”我愣住。
“嗯。”老眼点点头:“她是瞿荣民干女儿。”
“什么!”
我厉声问。这个信息太震撼了!
老眼笑了一下,没吭声。
60年后!
我一个激灵:“懂了!瞿荣民!说把她挖出来,在60年后!就是你老婆说的!”
老眼不置可否,双眼盯着车窗前方,看眼神,开始变得迷蒙。
我一头雾水,一时不好再问,只好继续开车,前方依然是青黑色的荒漠,天地交际,隐隐出现了一道奇怪的轮廓,像是山。
“其实我老婆是童养媳。”老眼忽道。
我一愣:“嗯。童养媳……”
“我是重庆彭水县人。”老眼道:“她是那头巫山县的,比我大18岁,我两岁那年她进了我家门,我21岁娶了她。瞿荣民的事情是10年前,她要死的时候说给我听的。”
我一凛:“她……她死了?”
“嘿嘿。被活活折磨死的。”
我一惊,瞟了一眼老眼,他仍死死盯着前方,一脸狰狞,眼里头似乎有泪水。
我点点头:“怎么回事?”
“我88年出去,在成都打了一年的工。”老眼道:“接到电话,说她要死了,赶紧回老家,她当时关在一间猪圈里头,拿铁链锁起,瘦的不成人形,地上有一个盆子,里头是半个馒头,还有点泡萝卜,我就问咋回事,他们说她给村头一个小娃娃取名字,没取对,结果那个娃娃死了,那家人就怪到她脑袋上,天天找人来整她,活活就折磨疯了,我们屋头人怕她出去惹事,就关在猪圈,关了两个月,嘿嘿!”
老眼抽了抽鼻子,狞笑一下:“都十年了。她当时在猪圈里头突然见到我,她当时哭的那个样子,老子范春龙这辈子都记得到。”
我点点头,不知道说什么话。
“那件事是她死之前躺在床板上给我说的。”老眼忽道。
“就瞿荣民的事?”
“嗯。”老眼道:“叫我60年后去怒江州那桶镇,那儿有个入口,进去后把瞿荣民从棺材里头挖出来,说有神异现世,就是我给你说的那四句话。”
我一愣:“六十年后——”
“六十年后——”老眼道:“开棺出尸,寒衣崩裂,神异北行,嗯,就这四句。”
“寒衣崩裂,神异北行……”我重复一遍:“说的什么意思?”
“估计跟覆疰有关。”
我一愣:“怎么说?”
“其实关于覆疰——”老眼道:“我知道的,是一个意外。”
“意外?”
“嗯。其实那本《食血经》本身是毕扒三经其中一本,本来是一种驱尸术,就是在送棺时候念给尸体听的,目的按照毕扒宣传的,主要是驱赶尸体身上的恶鬼,当然这个说起来有点荒唐,尸体本身都死了,听得见个锤子!至于鬼神之类,也多半是毕扒弄出来骗钱的,但是哪个也想不到,本来是一本装神弄鬼,毕扒用来骗钱的书,里头居然隐藏了一个恶物。”
“覆疰!”
“嗯。”老眼道:“具体是哪一年被发现的,按我老婆说的,没人说得清楚,但是过程她基本知道,就是活人不能听。”
我点点头:“必须处于活僵状态。”
“但其实这里头有个疑问。”
我一愣:“什么?”
“我老婆当时也没说清楚,好像是……要感染上覆疰,除了活人,还有一个必要条件。”
我一凛:“是什么?”
“不清楚。”老眼嘿嘿一笑:“反正不会这么容易就感染上,覆疰这东西,嘿嘿,它还是要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