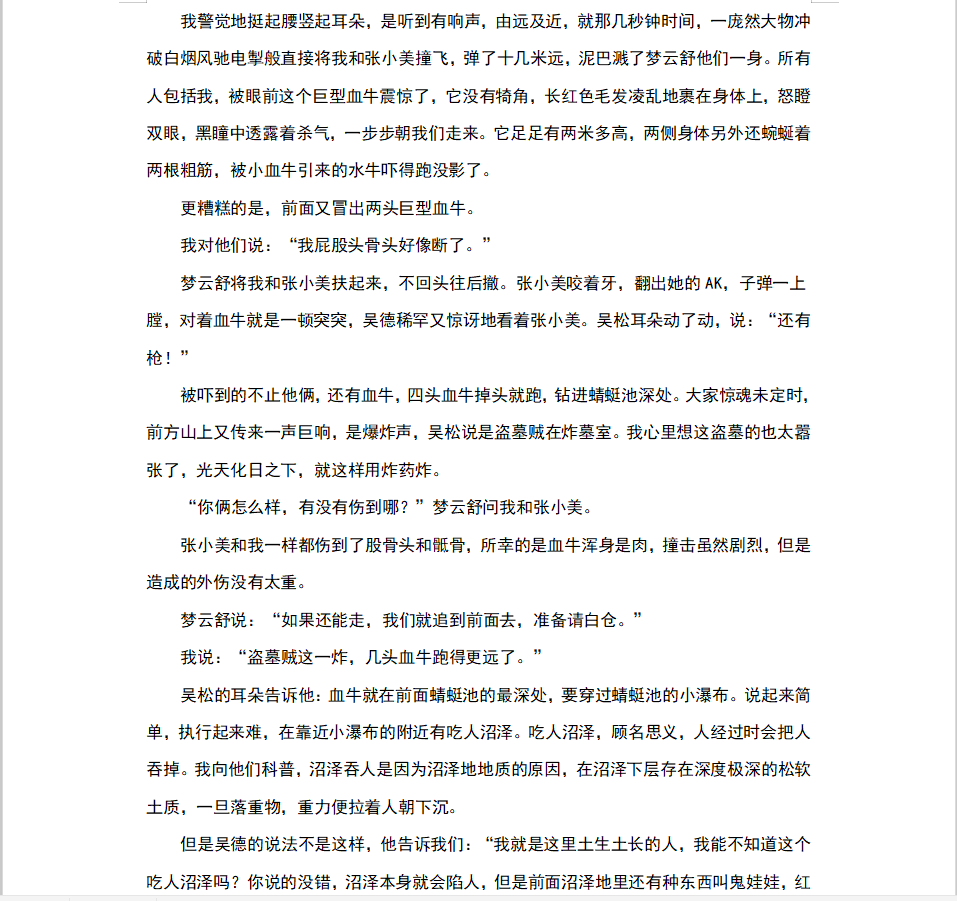
《成精记》:界门纲目科属种,怪力乱神人鬼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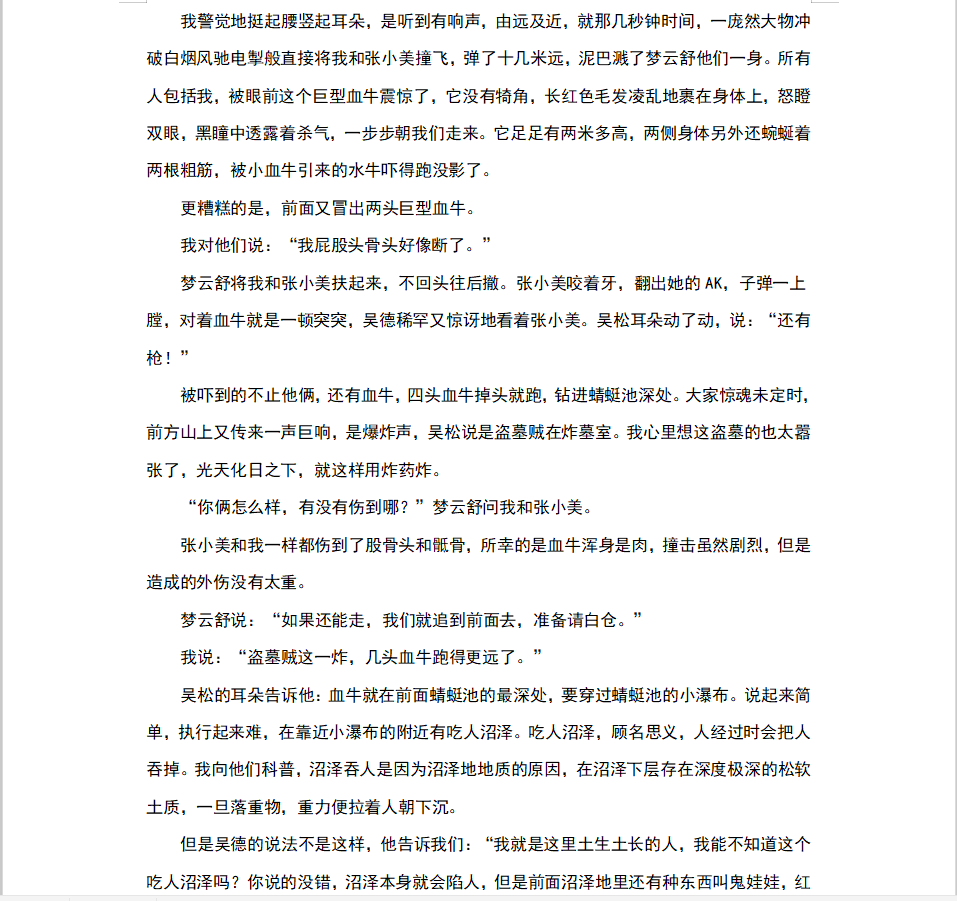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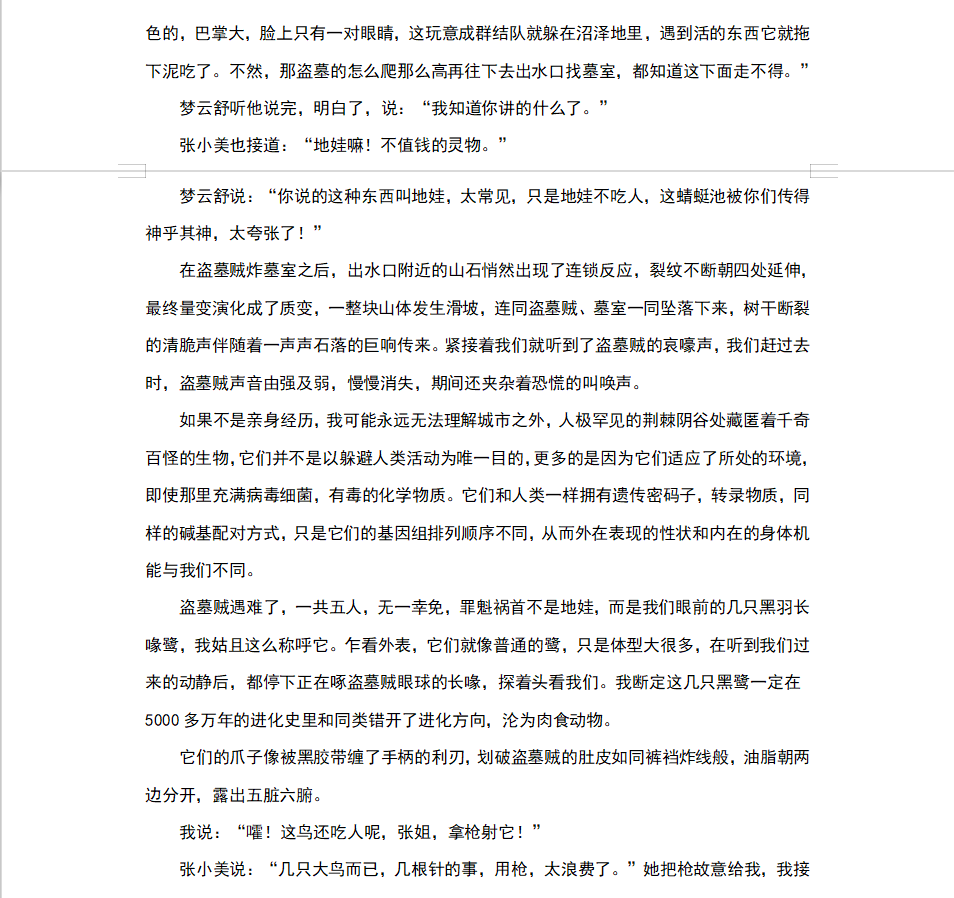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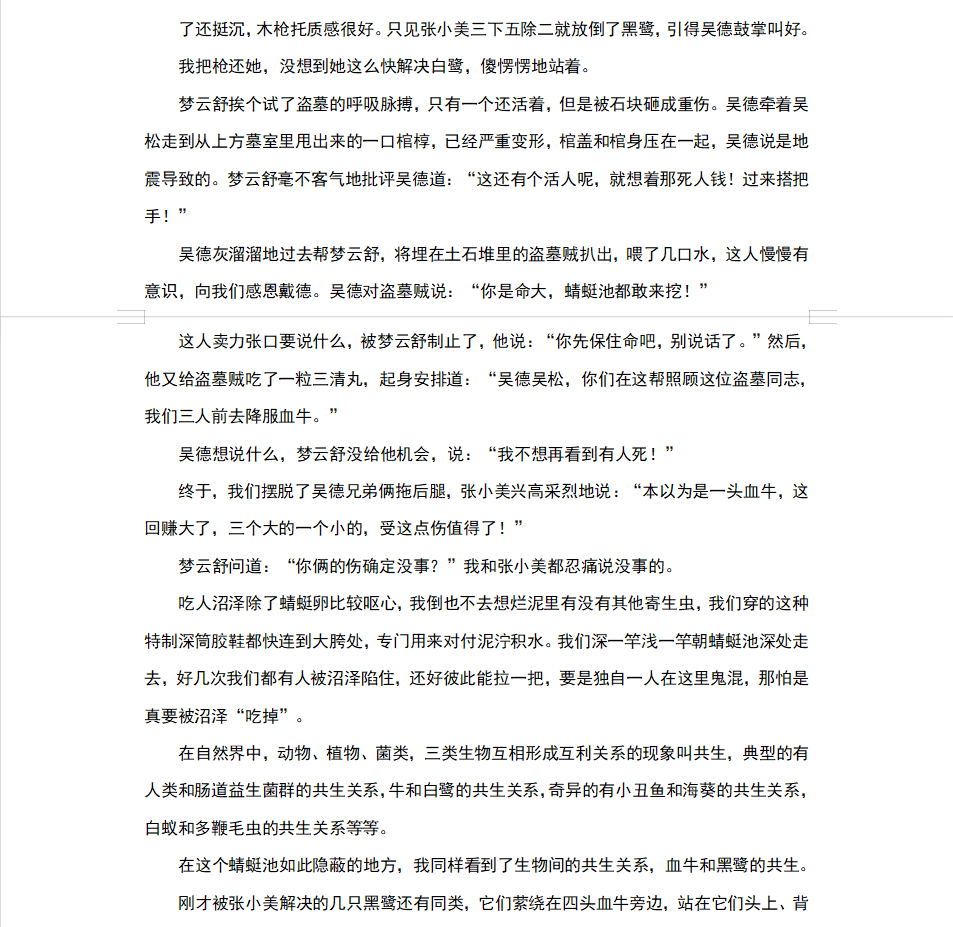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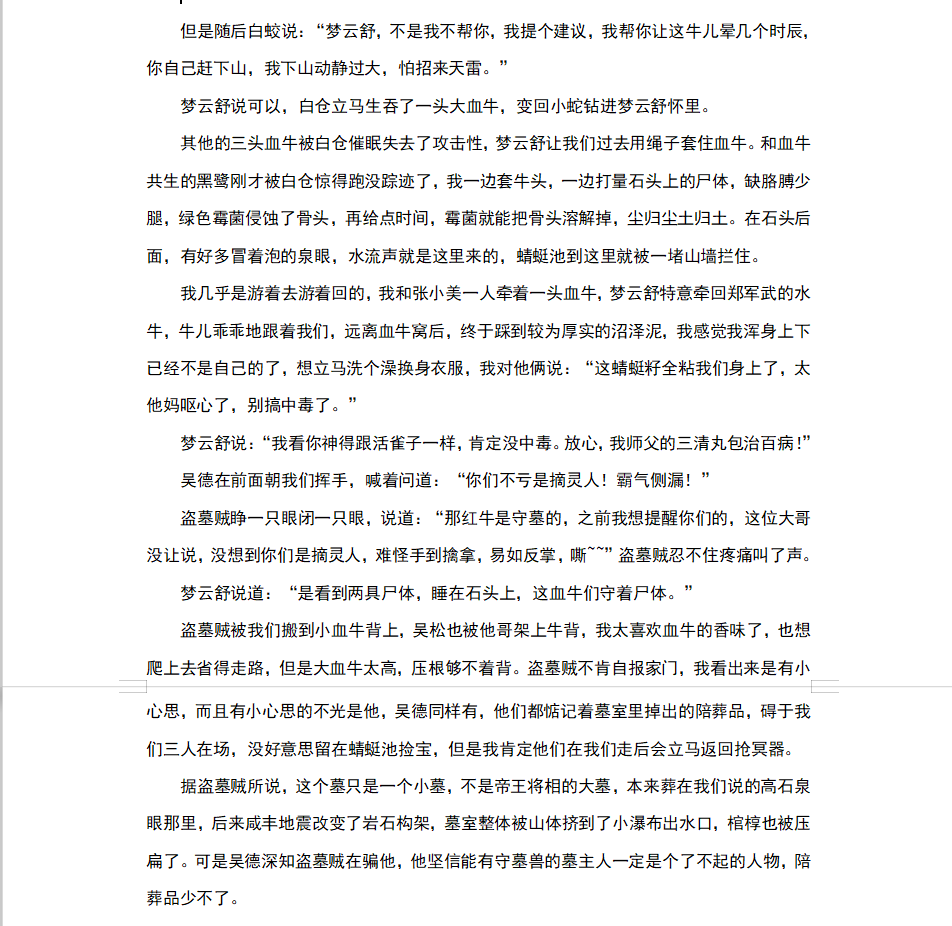
我们回老洼寨并没有从原路返回,那盘山小道也根本容不下血牛这么大体积。半路上,吴德向我们仨透露了些话,听完,我觉得后怕。他说:“我有些话说了,你们千万别动怒啊!”
我们困惑地看着他,洗耳恭听。
吴德接着说道:“一开始,我就往你们身上下了蛊,不过不过,能解,蛊毒能解,听我说完。”
我刚瞪起来眼睛,又缩回去了。他说:“我有私心,想着你们抓到血牛后,蛊毒发作,把你们害了,我和我弟渔翁得利,但是我真心感谢你们在蜻蜓池,帮我救我弟,我请你们原谅我,这血牛我现在是真的只需要一碗血,治疗我弟的眼疾。”
虽然吴德很诚恳地向我们道歉,但在我眼里,他依旧是个老油子。如果不是梦云舒降服血牛如探囊取物,吴德未必会这么好心向我们坦白并在后面帮我们解了蛊毒。吴德下的蛊毒他是帮我们解了,但是林娜月的蛊毒还在我们仨身上种着。
半路上,盗墓贼从血牛背上掉下,梦云舒把了脉搏后,说人死了。大家都惋惜地叹气,虽然不想把他丢尸荒野,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在老洼山里耽搁,一旦血牛苏醒,麻烦就大了。我做了很久的心理斗争后,终于向吴德提了林娜月放寄生虫在我们身体里一事,询问吴德有没有解蛊的办法,梦云舒和张小美都默许了我的请求。
吴德就这事,说了些话,他说:“按照你的说法,如果这个给你们下蛊的人不是苗族人也不是土家族人,那么很有可能他下的不是蛊毒,是降头术,那是一种东南亚的邪术,比蛊毒还要邪恶,它区别于我们的蛊,解毒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不瞒你们说,我的这点小伎俩,也不过是人人皆会的雕虫小技,防身用的。”
我皱着眉头说:“你这还叫小伎俩,刚才硬从我眼睛里引出那么多一堆白虫子,以前见人家赶眼虫,也没这么多量,你是要对我们仨下死手啊!”
吴德赶紧朝我作揖,说道:“哎呦哎呦,不敢不敢,小兄弟啊,确实是防身的小伎俩,可不敢害人,可不敢。”
我说:“你和吴松同志都各有绝技,做些什么不都可以糊口饭吃,以后千万不要往人身上下蛊害人。”
吴德连忙点头说:“是是是。我刚才想了一想,云舒同志的祛毒三清丸对蛊毒应该是有作用的,或许你们中了降头术也没事。”
我问梦云舒:“你师父的三清丸到底是不是真的包治百病啊?”
梦云舒说:“包治百病是玩笑话,世上哪有这样的药。三清丸有清热解毒作用,是能驱蛊,也不是什么蛊都包办在内。吴德同志的雕虫小技不就没防住。”
吴德捣了下梦云舒,说:“嗐!又拿我说笑了。说句实在话,不管是蛊还是降头,都很危险,你们还是要慎重点。”
我问吴德,“我们很够慎重了,就是像你们这些人没事搞什么蛊毒,才搞得天下大乱,这蛊解又不知怎么解,哎,我说,你会下蛊,你不会解我们蛊吗,啊?”
吴德说:“小同志,我也想给你们把蛊解了啊,但是我确实不会,我只会点祖传的偏方,不过。”
他顿了下,说:“不过,我认识有会解蛊的人,但是那几个人都不怎么友善。”
我问他,“不友善是什么意思,黑社会还是什么?”
吴德说:“那倒不是,我意思是这几个人都比较黑。”他搓着手指头,意思是要钱多。
我直言:“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说的这解蛊的人靠不靠谱?别坑人。”
吴德说:“给了钱肯定靠谱,这些人专职干这个的,给人解蛊,跟做生意一样,也需要回头客。坑人不会坑人。”梦云舒让吴德写了地址,吴德给了三个人联系方式,两个分别在湖南湖北,一个在云南。
吴德一直将我们带到老洼寨附近的林子,梦云舒说不进村,待到天擦黑直接下山,并且特意交待我去和郑军武打个招呼。我问梦云舒郑军武的钱还要不要给,梦云舒说正常给。我揣着一包钱,路上在想郑军武两头拿钱的事,越想越觉得可气。
等我走到郑军武家时,他女儿说他爹早上一早就上山,还没回来。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下,看着趴在椅子上背诗的她,十分心疼。我在想郑军武一定是因为牛跑了,还在山里找牛,我得立马告诉梦云舒。
但是就在我离开时,郑军武牵着牛从昨天我们上山的路下来了,我脸色立马变掉,等他走近后,我质问他道:“郑军武同志,你有点不厚道吧?”
他无辜地看着我,说:“你说什么啊?你们今天跑哪去了,我在青草岭山头上蹲了一天,也不见你们。”
我被他也搞糊涂了,我问他:“你今天在山上待了一天?你没找牛吗,你这牛谁的?”
郑军武和我都知道肯定哪里误会了,他急得不得了,说:“这牛我的啊,你们昨天不说让我今早带头牛上山,要是你们逮到血牛了就算了,逮不到血牛拿我牛儿去引吗?”
我急着问他:“那,那怎么有个吴德吴松的兄弟俩,说你也给他们报消息了,他们也要找血牛,说你两头拿钱,是这样吗?”
郑军武破口大骂道:“放他妈狗屁,这兄弟俩出了名的狡猾坏,他俩人呢,我和他们当面对质!血牛,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是给在咸丰厂里上班的侄子说了我见到血牛的事,有人通过他又找到我,说你们要来找这东西,找到还能有钱拿!”
我们困惑地看着他,洗耳恭听。
吴德接着说道:“一开始,我就往你们身上下了蛊,不过不过,能解,蛊毒能解,听我说完。”
我刚瞪起来眼睛,又缩回去了。他说:“我有私心,想着你们抓到血牛后,蛊毒发作,把你们害了,我和我弟渔翁得利,但是我真心感谢你们在蜻蜓池,帮我救我弟,我请你们原谅我,这血牛我现在是真的只需要一碗血,治疗我弟的眼疾。”
虽然吴德很诚恳地向我们道歉,但在我眼里,他依旧是个老油子。如果不是梦云舒降服血牛如探囊取物,吴德未必会这么好心向我们坦白并在后面帮我们解了蛊毒。吴德下的蛊毒他是帮我们解了,但是林娜月的蛊毒还在我们仨身上种着。
半路上,盗墓贼从血牛背上掉下,梦云舒把了脉搏后,说人死了。大家都惋惜地叹气,虽然不想把他丢尸荒野,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在老洼山里耽搁,一旦血牛苏醒,麻烦就大了。我做了很久的心理斗争后,终于向吴德提了林娜月放寄生虫在我们身体里一事,询问吴德有没有解蛊的办法,梦云舒和张小美都默许了我的请求。
吴德就这事,说了些话,他说:“按照你的说法,如果这个给你们下蛊的人不是苗族人也不是土家族人,那么很有可能他下的不是蛊毒,是降头术,那是一种东南亚的邪术,比蛊毒还要邪恶,它区别于我们的蛊,解毒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不瞒你们说,我的这点小伎俩,也不过是人人皆会的雕虫小技,防身用的。”
我皱着眉头说:“你这还叫小伎俩,刚才硬从我眼睛里引出那么多一堆白虫子,以前见人家赶眼虫,也没这么多量,你是要对我们仨下死手啊!”
吴德赶紧朝我作揖,说道:“哎呦哎呦,不敢不敢,小兄弟啊,确实是防身的小伎俩,可不敢害人,可不敢。”
我说:“你和吴松同志都各有绝技,做些什么不都可以糊口饭吃,以后千万不要往人身上下蛊害人。”
吴德连忙点头说:“是是是。我刚才想了一想,云舒同志的祛毒三清丸对蛊毒应该是有作用的,或许你们中了降头术也没事。”
我问梦云舒:“你师父的三清丸到底是不是真的包治百病啊?”
梦云舒说:“包治百病是玩笑话,世上哪有这样的药。三清丸有清热解毒作用,是能驱蛊,也不是什么蛊都包办在内。吴德同志的雕虫小技不就没防住。”
吴德捣了下梦云舒,说:“嗐!又拿我说笑了。说句实在话,不管是蛊还是降头,都很危险,你们还是要慎重点。”
我问吴德,“我们很够慎重了,就是像你们这些人没事搞什么蛊毒,才搞得天下大乱,这蛊解又不知怎么解,哎,我说,你会下蛊,你不会解我们蛊吗,啊?”
吴德说:“小同志,我也想给你们把蛊解了啊,但是我确实不会,我只会点祖传的偏方,不过。”
他顿了下,说:“不过,我认识有会解蛊的人,但是那几个人都不怎么友善。”
我问他,“不友善是什么意思,黑社会还是什么?”
吴德说:“那倒不是,我意思是这几个人都比较黑。”他搓着手指头,意思是要钱多。
我直言:“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说的这解蛊的人靠不靠谱?别坑人。”
吴德说:“给了钱肯定靠谱,这些人专职干这个的,给人解蛊,跟做生意一样,也需要回头客。坑人不会坑人。”梦云舒让吴德写了地址,吴德给了三个人联系方式,两个分别在湖南湖北,一个在云南。
吴德一直将我们带到老洼寨附近的林子,梦云舒说不进村,待到天擦黑直接下山,并且特意交待我去和郑军武打个招呼。我问梦云舒郑军武的钱还要不要给,梦云舒说正常给。我揣着一包钱,路上在想郑军武两头拿钱的事,越想越觉得可气。
等我走到郑军武家时,他女儿说他爹早上一早就上山,还没回来。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下,看着趴在椅子上背诗的她,十分心疼。我在想郑军武一定是因为牛跑了,还在山里找牛,我得立马告诉梦云舒。
但是就在我离开时,郑军武牵着牛从昨天我们上山的路下来了,我脸色立马变掉,等他走近后,我质问他道:“郑军武同志,你有点不厚道吧?”
他无辜地看着我,说:“你说什么啊?你们今天跑哪去了,我在青草岭山头上蹲了一天,也不见你们。”
我被他也搞糊涂了,我问他:“你今天在山上待了一天?你没找牛吗,你这牛谁的?”
郑军武和我都知道肯定哪里误会了,他急得不得了,说:“这牛我的啊,你们昨天不说让我今早带头牛上山,要是你们逮到血牛了就算了,逮不到血牛拿我牛儿去引吗?”
我急着问他:“那,那怎么有个吴德吴松的兄弟俩,说你也给他们报消息了,他们也要找血牛,说你两头拿钱,是这样吗?”
郑军武破口大骂道:“放他妈狗屁,这兄弟俩出了名的狡猾坏,他俩人呢,我和他们当面对质!血牛,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是给在咸丰厂里上班的侄子说了我见到血牛的事,有人通过他又找到我,说你们要来找这东西,找到还能有钱拿!”
防和谐楼
正在这时候,有几个村民火急火燎地跑来,嘀嘀咕咕说着方言,我也没听懂,还拿手指着我。郑军武把他们拦住,问我:“你刚才牵着牛去我家了?”
我说:“我们从山上带下来一头牛,是被血牛引去的,以为是你家的,特意来送给你。”
郑军武赶紧向旁边的人解释,这几个人便冲向郑军武家,原来牛是这些人的。我把装钱的信封递给郑军武,说:“血牛我们已经抓到了,这是给你的报酬,我们误会你了,向你道歉。”
郑军武接钱的时候故意身子一低,意在夸张钱袋很重,说道:“我的娘,我不知道怎么答谢你们好啊!”我和他握了手,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答谢你好,保重!”
当我回到林子时,吴德和吴松已经走了,我把郑军武的事一说,梦云舒立马把吴德写的纸条子撕了,说道:“就知道吴德吴松这两人不靠谱!”
我看见一头大血牛前足上方开了口子,应该是被吴德接了血。
那天傍晚我们赶黑出山,朝毛坝快速进发。进山时觉得老洼寨遥遥无期,很远,出山时,却很快就赶到毛坝了。我们一路上担心血牛会中途苏醒,好在没有。我们将血牛牢牢捆住,连夜运出利川,赶回武汉交货。
上次姑获鸟是由王帅负责运到指定地方交货的,这次王帅负伤,我和梦云舒第一次参与了灵物交货。交货地不便透露,华东分舵的灵物都会由组织运往清城。这些负责运输的同事都戴着黑纱布,特意不让人看到他们的真面目,讲话也都是惜字如金,冰冷冰冷,没有丝毫情商可言。
我们只在武汉简单逗留休息了晚,次日立马赶回合肥,我们心里都一直惦记着林娜月的事。这个酉西山究竟是什么山,有什么重大秘密在里面。我很想搞清楚,梦云舒和张小美更想搞清楚。我们三个在火车上再次确定,回到合肥第一件事就是向J哥坦白林娜月要挟我们一事,张小美斩钉截铁地说:“一定不能给粘杆处丢脸,让那个外国佬失算!”
1989年那会,中苏关系慢慢走上正常化,其实在几年前,已经有明显好转迹象,所以林娜月这样的做法,让我们对苏联抱有的友好态度和幻想立马大打折扣,这种感觉往大了说,就像五几年苏联专家帮中国修好武汉长江大桥,准备再协助中国建南京长江大桥时,突然全撤走了。
踏上合肥的土地,我感到莫名的亲切。读安大时,我对合肥没有什么感情,心里时常挂念家乡全椒,但是现在渐渐认可了合肥,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时隔多日,范山人已经出院,王帅还在省立医院住院,伤势好转很多。在见到我们三个后,J哥和范山人十分激动。J哥三连赞道:“好!好!好!你们这支队伍非常优秀,三头血牛!一次把全年任务完成了!今天什么都别说,晚上我请客喝酒!”
范山人见我们三个闷闷不乐,疑惑道:“怎么回事,都板着脸干嘛,J总难得请人下馆子啊!”
我们强颜欢笑,显得非常不自然。J哥误解道:“难不成是担心你们的分成,放心吧,清城那边收到货会给我发来评估,这次外派分成按照三只血牛总价值结算,不可能给你们按照一头来算,另外,我给你们每人批半个月假!”
我听了心里直痒痒,打起小算盘。
张小美这时候开口说话,道:“J哥,你误会了,钱的事我们都听组织安排,绝对没有二心。是有一件不好的事,一直堵在我们三个心里,还有王帅。”
J哥听了突然正襟危坐,范山人也严肃起来,气氛像极了审讯犯人。张小美把此前林娜月借要去神农架考察长潭水怪,给我们下毒一事全盘托出。J哥听完大为吃惊,他以为我们上次回来交差,事情办得很顺利。他说:“我没想到这个苏联佬藏得这么深,还把游总搬出来,搞得我那么慎重,安排你们四人同去!这个事,你们做得很对,而且应该早点告诉我,她竟然打酉西山的主意,这里面有很多蹊跷!”
我十分好奇,问道:“J哥,这个酉西山到底是什么山,你们知道吗?”
J哥板着脸不开笑脸,没有正面回答我,说:“你们不用管这个酉西山的事,后面也不要和其他同事提及。你们身上的虫子我认识个朋友叫宫里佛会治,我今天和他通个电话。你们先下楼休息会,老范,你留一下。”
我们出来后立马围在一起商议,我担心道:“J哥这么轻描淡写的,到底能不能把我们身上的寄生虫给搞掉啊?”
张小美说:“他既然开口说可以,应该就没问题,这件事闹大了,搞不好会惊动粘杆处上层,而且这林娜月还是游子善游总介绍来的。”
梦云舒倒是洒脱,他说:“林娜月的事他们自会处理,看样子是触及到组织利益了,我们先搞好自己吧!”
那天J哥的确请我们下馆子喝酒了,张小美说他来粘杆处几年了,的确很少见J哥主动请人喝酒。第二天,J哥要我们出发去江西鹰潭找宫里佛。到此,我们都不知道J哥身怀什么绝技,甚至连张小美也不知道,直到和宫里佛碰面后。
我说:“我们从山上带下来一头牛,是被血牛引去的,以为是你家的,特意来送给你。”
郑军武赶紧向旁边的人解释,这几个人便冲向郑军武家,原来牛是这些人的。我把装钱的信封递给郑军武,说:“血牛我们已经抓到了,这是给你的报酬,我们误会你了,向你道歉。”
郑军武接钱的时候故意身子一低,意在夸张钱袋很重,说道:“我的娘,我不知道怎么答谢你们好啊!”我和他握了手,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答谢你好,保重!”
当我回到林子时,吴德和吴松已经走了,我把郑军武的事一说,梦云舒立马把吴德写的纸条子撕了,说道:“就知道吴德吴松这两人不靠谱!”
我看见一头大血牛前足上方开了口子,应该是被吴德接了血。
那天傍晚我们赶黑出山,朝毛坝快速进发。进山时觉得老洼寨遥遥无期,很远,出山时,却很快就赶到毛坝了。我们一路上担心血牛会中途苏醒,好在没有。我们将血牛牢牢捆住,连夜运出利川,赶回武汉交货。
上次姑获鸟是由王帅负责运到指定地方交货的,这次王帅负伤,我和梦云舒第一次参与了灵物交货。交货地不便透露,华东分舵的灵物都会由组织运往清城。这些负责运输的同事都戴着黑纱布,特意不让人看到他们的真面目,讲话也都是惜字如金,冰冷冰冷,没有丝毫情商可言。
我们只在武汉简单逗留休息了晚,次日立马赶回合肥,我们心里都一直惦记着林娜月的事。这个酉西山究竟是什么山,有什么重大秘密在里面。我很想搞清楚,梦云舒和张小美更想搞清楚。我们三个在火车上再次确定,回到合肥第一件事就是向J哥坦白林娜月要挟我们一事,张小美斩钉截铁地说:“一定不能给粘杆处丢脸,让那个外国佬失算!”
1989年那会,中苏关系慢慢走上正常化,其实在几年前,已经有明显好转迹象,所以林娜月这样的做法,让我们对苏联抱有的友好态度和幻想立马大打折扣,这种感觉往大了说,就像五几年苏联专家帮中国修好武汉长江大桥,准备再协助中国建南京长江大桥时,突然全撤走了。
踏上合肥的土地,我感到莫名的亲切。读安大时,我对合肥没有什么感情,心里时常挂念家乡全椒,但是现在渐渐认可了合肥,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时隔多日,范山人已经出院,王帅还在省立医院住院,伤势好转很多。在见到我们三个后,J哥和范山人十分激动。J哥三连赞道:“好!好!好!你们这支队伍非常优秀,三头血牛!一次把全年任务完成了!今天什么都别说,晚上我请客喝酒!”
范山人见我们三个闷闷不乐,疑惑道:“怎么回事,都板着脸干嘛,J总难得请人下馆子啊!”
我们强颜欢笑,显得非常不自然。J哥误解道:“难不成是担心你们的分成,放心吧,清城那边收到货会给我发来评估,这次外派分成按照三只血牛总价值结算,不可能给你们按照一头来算,另外,我给你们每人批半个月假!”
我听了心里直痒痒,打起小算盘。
张小美这时候开口说话,道:“J哥,你误会了,钱的事我们都听组织安排,绝对没有二心。是有一件不好的事,一直堵在我们三个心里,还有王帅。”
J哥听了突然正襟危坐,范山人也严肃起来,气氛像极了审讯犯人。张小美把此前林娜月借要去神农架考察长潭水怪,给我们下毒一事全盘托出。J哥听完大为吃惊,他以为我们上次回来交差,事情办得很顺利。他说:“我没想到这个苏联佬藏得这么深,还把游总搬出来,搞得我那么慎重,安排你们四人同去!这个事,你们做得很对,而且应该早点告诉我,她竟然打酉西山的主意,这里面有很多蹊跷!”
我十分好奇,问道:“J哥,这个酉西山到底是什么山,你们知道吗?”
J哥板着脸不开笑脸,没有正面回答我,说:“你们不用管这个酉西山的事,后面也不要和其他同事提及。你们身上的虫子我认识个朋友叫宫里佛会治,我今天和他通个电话。你们先下楼休息会,老范,你留一下。”
我们出来后立马围在一起商议,我担心道:“J哥这么轻描淡写的,到底能不能把我们身上的寄生虫给搞掉啊?”
张小美说:“他既然开口说可以,应该就没问题,这件事闹大了,搞不好会惊动粘杆处上层,而且这林娜月还是游子善游总介绍来的。”
梦云舒倒是洒脱,他说:“林娜月的事他们自会处理,看样子是触及到组织利益了,我们先搞好自己吧!”
那天J哥的确请我们下馆子喝酒了,张小美说他来粘杆处几年了,的确很少见J哥主动请人喝酒。第二天,J哥要我们出发去江西鹰潭找宫里佛。到此,我们都不知道J哥身怀什么绝技,甚至连张小美也不知道,直到和宫里佛碰面后。
怎么又被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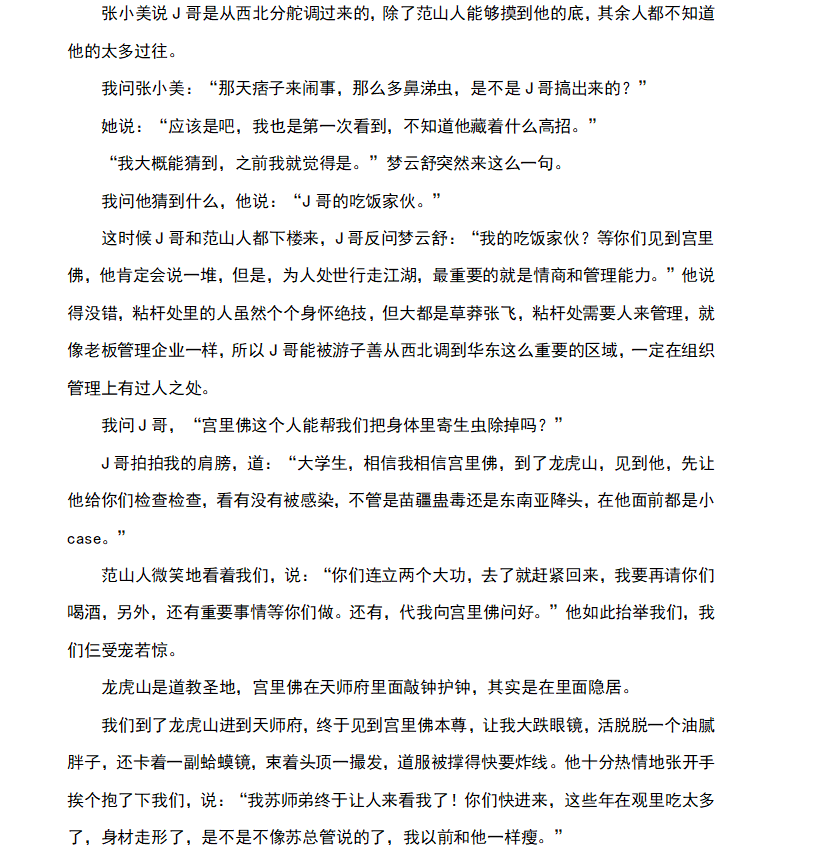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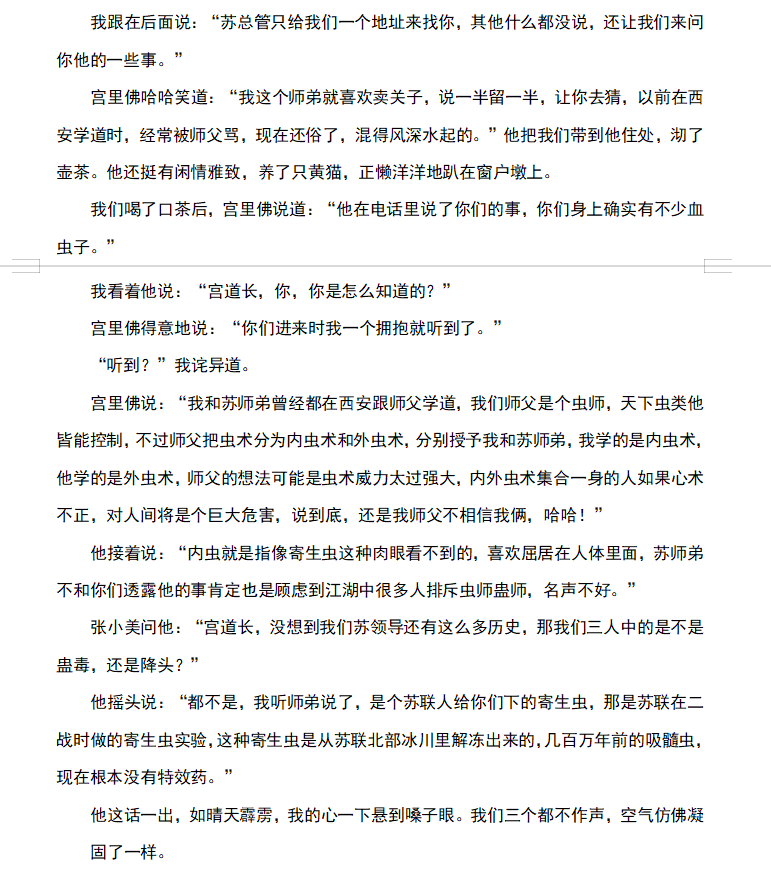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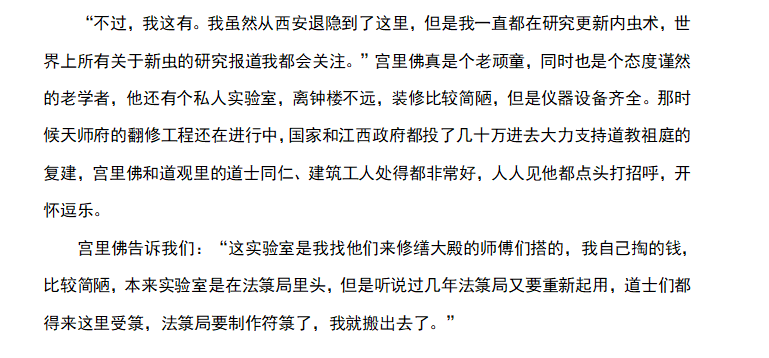
![[xyc:打卡]](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xyc/dk.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