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更新的7280楼被系统删除,补发图片。
《成精记》:界门纲目科属种,怪力乱神人鬼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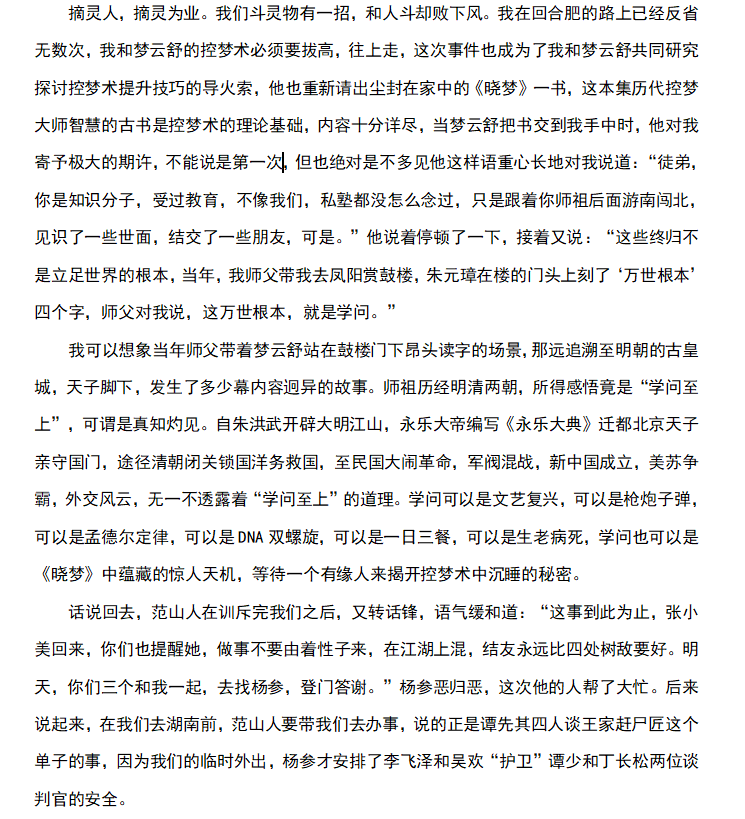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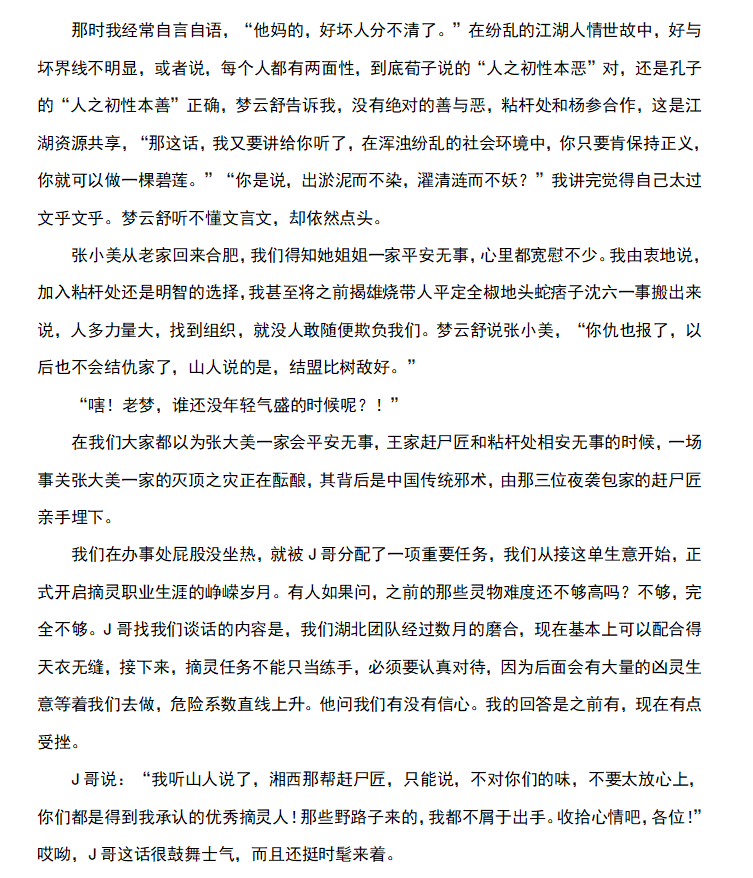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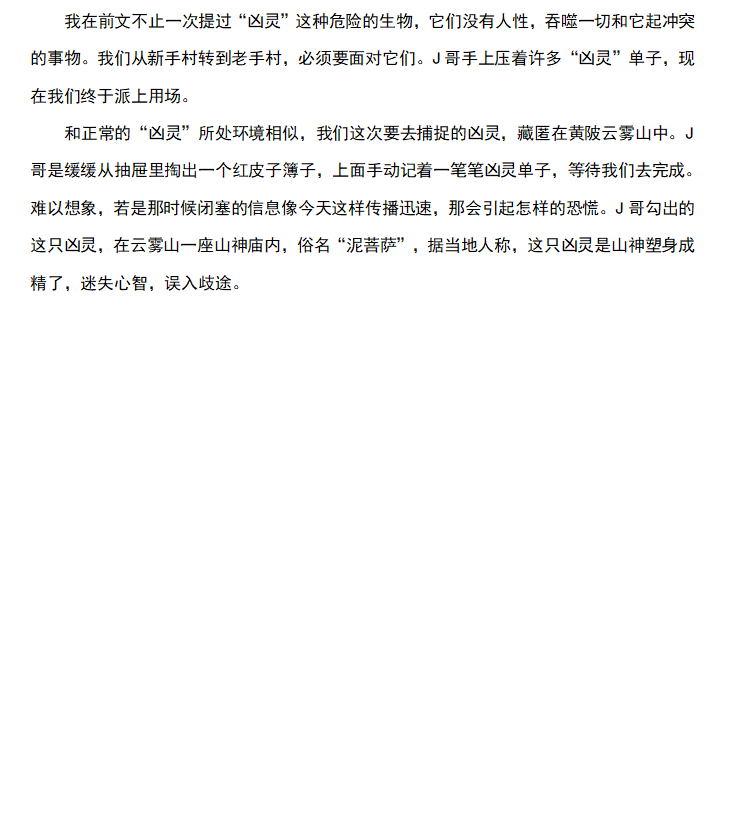
大家周末好,谢谢大家的热情顶贴。
凶灵,对于张小美来说,不是新鲜事,她说,在我和梦云舒加入粘杆处之前,当时她们的团队就已经经手许多凶灵生意了。除了王帅和她,还有其他两个同仁,一个燕柳庆,一个曾千帆,两人就是死于凶灵手中。
在之前我们已经见识了千年鲎精的厉害,这次前往云雾山降服这位“泥菩萨”,胜算又有多大呢?这谁都不敢保证。我们虽然被J哥鼓舞了一番士气,可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对手可是一只凶灵。“打不打得过,只有去了才知道!”刘宝童如是说,不能讲她冲动,起码她有这个胆量。
我投她一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挂在招待所房间里换洗的衣服还没有干透,附着着一股猪骚味,我又要捡起行囊,拾掇好行李,从合肥前往武汉。汉地祖山云雾山在黄陂县西北部,过多的形容词我就不多赘述了,天下奇山皆出中华。
和以往一样,我们需要找到线人,但是这次,线人不给我们带路到目的地了,甚至目的地附近也不行。这个叫林晶的线人说“泥菩萨”万分危险,不敢冒犯,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准信的地点,接下来就需要我们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地方。
我假装警告林晶说:“大家都是实在人,你别骗我们,这钱你先拿一半,后面的一半,等我们搞定了,再给你。”
林晶耸了耸鼻子,嘿嘿笑道:“冇事冇事!这就够了!”他话的意思可不简单,他不是知足常乐,觉得钱不少了,林晶是怀疑我们不能从云雾山“泥菩萨”手中走出来。
我们按图索骥,这个图就是林晶画的地图,张小美可以识别,毕竟她在湖北混了几年,但是这些路线都是些山路,我们还需要沿路问对人才可以准确到达。
走在路上,我就说这个林晶老封建,不过是个灵物罢了,还这不带路那不带路的,等把这只凶灵收了,剩下那一半好处费就不给他,别想不劳而获!
张小美陪着笑脸心不在焉点头赞成我,心里却憋着其他话,终于说出来:“老梦,要不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吧!我不想像王帅一样,当个司机只负责拉货!”当初王帅失踪,J哥决定安排张小美充当王帅的角色,做个接应我们的卡车司机,张小美不想干这个活,她说:“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现在需要我!”
她的话让大家都笑起来,我忽然觉得张小美充满魅力,情不自禁地搂住她的肩膀,说道:“张姐,我们没有你的确不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走了,就剩我刘姐一个女同志了,这分配不均匀了!哈哈!”张小美回眸深情地望着我,说:“你姐身上香不香?”
“啊?”我一愣,翘翘鼻头,说:“香香,是香。”
“逗你玩的!以往老有小年轻往姐身上凑,想揩姐的油,都说‘姐姐,你身上有股难以形容的香味耶’,哎呦,呕!南方来的油头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张小美故意模仿她口中的某些油头小子轻佻的动作,逗笑我们。
梦云舒突发奇想,说:“你们看这天,这山色,丝丝凉意。当年,刘备张飞关羽桃园三结义,我看,今天我们四个来个山林四结义。”
“老梦你突然文绉绉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张小美戏谑道。
那个天气是即将入暑的天气,不是天凉好个秋的感觉,不过,人在山间走,的确没有暑气,一阵阵氲凉使人心旷神怡。我们挑了一棵上些年纪的大树,好不容易把白金请出来,让它做个见证,我们四人当场结了生死结。在一旁观看的白金,深受感动。这是一项笼络人心的行为,使得我们四人搭档更加团结。我讲过,梦云舒在王帅失踪后反思过自己,他告诫自己以后为了团队成员必须要舍得付出,而不只是只为了我和他女儿才可以做出牺牲。
我们精神抖擞地重新上路,逢到人便问通往林晶给的山神庙位置的路怎么走,这些居家在云雾山外的人大多知道泥菩萨的故事,他们都劝我们不要靠近那里,凶多吉少。在中国民间,类似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多如牛毛,很多如鹅毛沉水般,封在“乡下人”的肚中,绝口不谈。
这就像我们全椒当地人一样,视“狐狸”二字为不祥,谈及狐狸,皆是用“那东西”代替,仿佛说了“狐狸”两字后,成精的狐狸就会找上门一样。在过去,狐狸喜欢在人家里做窝,家主子还不能赶,迷信说赶走土狐狸,家里就会倒霉。我一个同村的远亲表叔,名叫陈伟宇,个子不高,1米60左右,是个土律师(就是没什么文化,但是会写状纸),人挺狠的。他家里70年代住过一条土狐狸,狐狸是老狐狸了,毛都有些发白,睡他家厨房一角堆着的稻草上,陈表叔性情耿直,担心老狐狸撒尿尿草上面,把稻草闷坏了,后面不好扎秧苗,他就赶走老狐狸,不让它住厨房。当天晚上,这老狐狸就溜到陈表叔房间里,蹲在床尾处,一根根抽他床单下垫的草,陈表叔半夜醒了听见床尾有声音,蹬着脚大吼,把土狐狸吓跑了,睡着后,它又来了,不紧不慢地一根根抽着草,陈表叔说他还真有点怕,但他还是没让狐狸住家里。
在之前我们已经见识了千年鲎精的厉害,这次前往云雾山降服这位“泥菩萨”,胜算又有多大呢?这谁都不敢保证。我们虽然被J哥鼓舞了一番士气,可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对手可是一只凶灵。“打不打得过,只有去了才知道!”刘宝童如是说,不能讲她冲动,起码她有这个胆量。
我投她一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挂在招待所房间里换洗的衣服还没有干透,附着着一股猪骚味,我又要捡起行囊,拾掇好行李,从合肥前往武汉。汉地祖山云雾山在黄陂县西北部,过多的形容词我就不多赘述了,天下奇山皆出中华。
和以往一样,我们需要找到线人,但是这次,线人不给我们带路到目的地了,甚至目的地附近也不行。这个叫林晶的线人说“泥菩萨”万分危险,不敢冒犯,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准信的地点,接下来就需要我们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地方。
我假装警告林晶说:“大家都是实在人,你别骗我们,这钱你先拿一半,后面的一半,等我们搞定了,再给你。”
林晶耸了耸鼻子,嘿嘿笑道:“冇事冇事!这就够了!”他话的意思可不简单,他不是知足常乐,觉得钱不少了,林晶是怀疑我们不能从云雾山“泥菩萨”手中走出来。
我们按图索骥,这个图就是林晶画的地图,张小美可以识别,毕竟她在湖北混了几年,但是这些路线都是些山路,我们还需要沿路问对人才可以准确到达。
走在路上,我就说这个林晶老封建,不过是个灵物罢了,还这不带路那不带路的,等把这只凶灵收了,剩下那一半好处费就不给他,别想不劳而获!
张小美陪着笑脸心不在焉点头赞成我,心里却憋着其他话,终于说出来:“老梦,要不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吧!我不想像王帅一样,当个司机只负责拉货!”当初王帅失踪,J哥决定安排张小美充当王帅的角色,做个接应我们的卡车司机,张小美不想干这个活,她说:“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现在需要我!”
她的话让大家都笑起来,我忽然觉得张小美充满魅力,情不自禁地搂住她的肩膀,说道:“张姐,我们没有你的确不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走了,就剩我刘姐一个女同志了,这分配不均匀了!哈哈!”张小美回眸深情地望着我,说:“你姐身上香不香?”
“啊?”我一愣,翘翘鼻头,说:“香香,是香。”
“逗你玩的!以往老有小年轻往姐身上凑,想揩姐的油,都说‘姐姐,你身上有股难以形容的香味耶’,哎呦,呕!南方来的油头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张小美故意模仿她口中的某些油头小子轻佻的动作,逗笑我们。
梦云舒突发奇想,说:“你们看这天,这山色,丝丝凉意。当年,刘备张飞关羽桃园三结义,我看,今天我们四个来个山林四结义。”
“老梦你突然文绉绉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张小美戏谑道。
那个天气是即将入暑的天气,不是天凉好个秋的感觉,不过,人在山间走,的确没有暑气,一阵阵氲凉使人心旷神怡。我们挑了一棵上些年纪的大树,好不容易把白金请出来,让它做个见证,我们四人当场结了生死结。在一旁观看的白金,深受感动。这是一项笼络人心的行为,使得我们四人搭档更加团结。我讲过,梦云舒在王帅失踪后反思过自己,他告诫自己以后为了团队成员必须要舍得付出,而不只是只为了我和他女儿才可以做出牺牲。
我们精神抖擞地重新上路,逢到人便问通往林晶给的山神庙位置的路怎么走,这些居家在云雾山外的人大多知道泥菩萨的故事,他们都劝我们不要靠近那里,凶多吉少。在中国民间,类似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多如牛毛,很多如鹅毛沉水般,封在“乡下人”的肚中,绝口不谈。
这就像我们全椒当地人一样,视“狐狸”二字为不祥,谈及狐狸,皆是用“那东西”代替,仿佛说了“狐狸”两字后,成精的狐狸就会找上门一样。在过去,狐狸喜欢在人家里做窝,家主子还不能赶,迷信说赶走土狐狸,家里就会倒霉。我一个同村的远亲表叔,名叫陈伟宇,个子不高,1米60左右,是个土律师(就是没什么文化,但是会写状纸),人挺狠的。他家里70年代住过一条土狐狸,狐狸是老狐狸了,毛都有些发白,睡他家厨房一角堆着的稻草上,陈表叔性情耿直,担心老狐狸撒尿尿草上面,把稻草闷坏了,后面不好扎秧苗,他就赶走老狐狸,不让它住厨房。当天晚上,这老狐狸就溜到陈表叔房间里,蹲在床尾处,一根根抽他床单下垫的草,陈表叔半夜醒了听见床尾有声音,蹬着脚大吼,把土狐狸吓跑了,睡着后,它又来了,不紧不慢地一根根抽着草,陈表叔说他还真有点怕,但他还是没让狐狸住家里。
秋凉了,有种诗意大发的感觉。合肥早晚温度非常舒服。
问一下大家,你们的阅读速度,一天多少字够看
谢谢大家热情顶贴。
一天,他去村前田里瞧水(农村种田人,需要经常扛着铁锹去田里通渠,看水位,防止缺水干旱或者水多淹庄稼),路过一棵老柳树(这柳树我读小学时见过,后来五年级时,树被砍了),陈表叔的腿突发疾病,一阵刺痛,他撸起裤袖看到,腿上的筋鼓起,一层层地叠起,似一堆蚯蚓聚盘在腿部,密集而恐惧。其实,这只是下肢静脉曲张,但是陈表叔家人认为这是土狐狸所为,后来请人来送,说是把土狐狸送走了。可我见陈表叔腿上的静脉曲张病一直没有痊愈。
我们还是按照当地人的指引找到了图上的这条穿过云雾山的内山溪,宽约丈把,当地的山里人叫它饮犬湾,来自山间暗河的清凉溪水流淌于此,水至清,还有小鱼虾,掏一掌水喝,像咽化冻的冰块。沿着饮犬湾走,大概二十里路,就可以到达位于两山夹脚间的山神庙。
林深怪事多。半路上,我们遇见一个捡柴火的“娃娃”,其实是个有侏儒症的成年男人,头大身子小,黝黑黝黑的,他正从背上将自己的柴火卸下来,看见我们,也不吃惊,缓缓坐到溪水边一块石头上,抄水洗了把脸,往身上揩揩水,默默掏出半支卷烟,擦火柴点着,冲着我们吐一片白烟。
我礼貌地试探着问他泥菩萨的事,他呲着一嘴大黄牙,说了一通黄陂话,我没听懂,张小美能听懂,她说这人极力劝我们不要再往里走了,望望太阳落山,就麻烦了。张小美问他怎么个麻烦。这人说泥菩萨专挑夜间出来,水里,树上,土里,它都有可能藏着,见人就杀,当问到泥菩萨长什么样,这人说就是一般庙里菩萨的模样,是菩萨泥身成精变成的。
“他意思说很危险!山神庙那块没人敢靠近,以前旁边有个村子,山神庙是这个村供奉的,后来泥菩萨杀人,这个村集体搬走了。”张小美帮我们翻译着,这话让人听着不寒而栗。西边的落日已然擦过树头,照这个样子,我们晚上需要在树林里过夜了,这位好心大哥告诫我们最好就在这或者往来时的地方走一走过个夜,离山神庙远一点,不安全。
我们后来商量结果是,先在这里扎个营,休息一晚,明天趁白天时候先去山神庙探探情况,把路线摸清楚。我们找了一处地势偏高的石头堆作为扎营的地方,放下背包,拉拉腰筋,我负责码石头,就是用石头围着我们一圈码过来,随身带的石灰,洒在这一圈石头上,这可以从心理上防止野虫子爬进来。接着,我和刘宝童去砍粗细树枝,用来晚上生火。她的唐刀化身砍柴刀,断柴锋利,用来顺手。
她教我怎么握刀,怎么发力,怎么避免卷刀刃,我挥舞着唐刀,自己觉得还真像回事,圆了我小时候的武功梦。她似玩笑非玩笑地让我多练习练习,以后好保护她,我笑我自己达不到那么快的运刀手法。刘宝童说:“经纬,凶灵是不是很难搞?我们四个是它对手吗?”我笑着问她:“你怕了吧?”“当然怕了,我又不是挂帅的穆桂英!”
我望着她美好的脸庞,认真道:“刘姐你放心,我肯定保护好你。”她莞尔一笑,弯腰抱起一摞柴火,我将唐刀插入她的刀鞘,搂搂剩下的柴木,一把抱走。梦云舒在溪水边打水漂,看见我们来了,帮忙刘宝童把柴火抬回去,此时,张小美已经支起两顶军用折叠帐篷。梦云舒说这样还不行,得用火烤下地面,祛祛湿气,除除寄生虫。张小美笑着说:“老梦还挺讲究的嘛!”
“我以前和我师父云游时,没有这个布帐篷,都是睡席子,烂被单,打露天地铺前,就得拿火燎下地,我师父说,这也可驱邪。”
“哎对了!师父,刚才那个砍柴的同志,不就说,泥菩萨会到处藏吗,我的妈,那赶紧拿火烧下地,别就躲这里了哦!”我故作慌张,被张小美推开,说:“你别乌鸦嘴!别这就把它招来了!”我立马捂住嘴。
梦云舒在白圈外生了一小堆火,用粗树枝一头“咝咝”吐出的火舌将白圈内的石头地熏烤了一番,留下一块块黑色的炭斑痕迹,我们这才放心地把帐篷重新搭上。张小美和刘宝童准备好待加热的事物,比如腊肠,腌制的咸肉,大馍馒头,简简单单的晚宴。我和梦云舒结伴去溪边舀水,这里的下游水依旧清澈,石子常年被水冲刷,有些成了鹅卵石,我不放心地问他:“这里靠近泥菩萨,水能喝吗?”
梦云舒扭头看向我,说:“不能喝,我们喝什么?你看那还有灰虾子,要是有毒,早毒死这些东西了。”灰虾子就是米虾,水里的米虾活蹦乱跳。我说:“要是有网,我们还能抓点鱼啊虾的烤烤。”梦云舒说:“你以为你出来游山逛水呢?徒弟?钓鱼休闲下。”
“可没那心情!师父!”
我望着已经见不到落日的远方,只有散射天边的红黄色余晖,感慨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梦云舒踢我一脚,说:“快走吧,别动不动吟诗作对的,欺负我这个粗人!”
我“嘿嘿”笑着,说:“我哪敢欺负你呀!”
我们盛水的瓷缸可以直接放在火架上烧,烤的咸货异常香,我都怕把狼引来。大馍夹着腊肠,既填饱肚子,又犒赏了味蕾,瓷缸煮出来的溪涧水喝起来好像味道是不一样,难道是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原因?天色黑下来,这堆火照亮黑夜,火苗跳跃,白灰扶摇。这些炙热的炭火灰烬,铲一些到白圈四角,加上柴火,夜晚起防狼的作用,给我一种厚厚的安全感,人躺在帐篷里面,享受着山林间流淌的风,敲着二郎腿,很惬意。
我们还是按照当地人的指引找到了图上的这条穿过云雾山的内山溪,宽约丈把,当地的山里人叫它饮犬湾,来自山间暗河的清凉溪水流淌于此,水至清,还有小鱼虾,掏一掌水喝,像咽化冻的冰块。沿着饮犬湾走,大概二十里路,就可以到达位于两山夹脚间的山神庙。
林深怪事多。半路上,我们遇见一个捡柴火的“娃娃”,其实是个有侏儒症的成年男人,头大身子小,黝黑黝黑的,他正从背上将自己的柴火卸下来,看见我们,也不吃惊,缓缓坐到溪水边一块石头上,抄水洗了把脸,往身上揩揩水,默默掏出半支卷烟,擦火柴点着,冲着我们吐一片白烟。
我礼貌地试探着问他泥菩萨的事,他呲着一嘴大黄牙,说了一通黄陂话,我没听懂,张小美能听懂,她说这人极力劝我们不要再往里走了,望望太阳落山,就麻烦了。张小美问他怎么个麻烦。这人说泥菩萨专挑夜间出来,水里,树上,土里,它都有可能藏着,见人就杀,当问到泥菩萨长什么样,这人说就是一般庙里菩萨的模样,是菩萨泥身成精变成的。
“他意思说很危险!山神庙那块没人敢靠近,以前旁边有个村子,山神庙是这个村供奉的,后来泥菩萨杀人,这个村集体搬走了。”张小美帮我们翻译着,这话让人听着不寒而栗。西边的落日已然擦过树头,照这个样子,我们晚上需要在树林里过夜了,这位好心大哥告诫我们最好就在这或者往来时的地方走一走过个夜,离山神庙远一点,不安全。
我们后来商量结果是,先在这里扎个营,休息一晚,明天趁白天时候先去山神庙探探情况,把路线摸清楚。我们找了一处地势偏高的石头堆作为扎营的地方,放下背包,拉拉腰筋,我负责码石头,就是用石头围着我们一圈码过来,随身带的石灰,洒在这一圈石头上,这可以从心理上防止野虫子爬进来。接着,我和刘宝童去砍粗细树枝,用来晚上生火。她的唐刀化身砍柴刀,断柴锋利,用来顺手。
她教我怎么握刀,怎么发力,怎么避免卷刀刃,我挥舞着唐刀,自己觉得还真像回事,圆了我小时候的武功梦。她似玩笑非玩笑地让我多练习练习,以后好保护她,我笑我自己达不到那么快的运刀手法。刘宝童说:“经纬,凶灵是不是很难搞?我们四个是它对手吗?”我笑着问她:“你怕了吧?”“当然怕了,我又不是挂帅的穆桂英!”
我望着她美好的脸庞,认真道:“刘姐你放心,我肯定保护好你。”她莞尔一笑,弯腰抱起一摞柴火,我将唐刀插入她的刀鞘,搂搂剩下的柴木,一把抱走。梦云舒在溪水边打水漂,看见我们来了,帮忙刘宝童把柴火抬回去,此时,张小美已经支起两顶军用折叠帐篷。梦云舒说这样还不行,得用火烤下地面,祛祛湿气,除除寄生虫。张小美笑着说:“老梦还挺讲究的嘛!”
“我以前和我师父云游时,没有这个布帐篷,都是睡席子,烂被单,打露天地铺前,就得拿火燎下地,我师父说,这也可驱邪。”
“哎对了!师父,刚才那个砍柴的同志,不就说,泥菩萨会到处藏吗,我的妈,那赶紧拿火烧下地,别就躲这里了哦!”我故作慌张,被张小美推开,说:“你别乌鸦嘴!别这就把它招来了!”我立马捂住嘴。
梦云舒在白圈外生了一小堆火,用粗树枝一头“咝咝”吐出的火舌将白圈内的石头地熏烤了一番,留下一块块黑色的炭斑痕迹,我们这才放心地把帐篷重新搭上。张小美和刘宝童准备好待加热的事物,比如腊肠,腌制的咸肉,大馍馒头,简简单单的晚宴。我和梦云舒结伴去溪边舀水,这里的下游水依旧清澈,石子常年被水冲刷,有些成了鹅卵石,我不放心地问他:“这里靠近泥菩萨,水能喝吗?”
梦云舒扭头看向我,说:“不能喝,我们喝什么?你看那还有灰虾子,要是有毒,早毒死这些东西了。”灰虾子就是米虾,水里的米虾活蹦乱跳。我说:“要是有网,我们还能抓点鱼啊虾的烤烤。”梦云舒说:“你以为你出来游山逛水呢?徒弟?钓鱼休闲下。”
“可没那心情!师父!”
我望着已经见不到落日的远方,只有散射天边的红黄色余晖,感慨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梦云舒踢我一脚,说:“快走吧,别动不动吟诗作对的,欺负我这个粗人!”
我“嘿嘿”笑着,说:“我哪敢欺负你呀!”
我们盛水的瓷缸可以直接放在火架上烧,烤的咸货异常香,我都怕把狼引来。大馍夹着腊肠,既填饱肚子,又犒赏了味蕾,瓷缸煮出来的溪涧水喝起来好像味道是不一样,难道是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原因?天色黑下来,这堆火照亮黑夜,火苗跳跃,白灰扶摇。这些炙热的炭火灰烬,铲一些到白圈四角,加上柴火,夜晚起防狼的作用,给我一种厚厚的安全感,人躺在帐篷里面,享受着山林间流淌的风,敲着二郎腿,很惬意。
谢谢大家的顶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