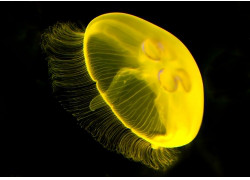耿六在小镇住了下来,每天寻思探听三哥的消息,观察山上山下的往来人。这天午后,一队高头大马的匪兵从镇上驰骋而过,那种横行霸道,招摇而过的气势,让人头皮发紧。他不敢表现的太过专注,心中早已经想好了,只要那秃子三爷路过,豁上一条命,先放嗓子喊叫,再磕头祷告,好问出三哥的死活来。
耿光祖被安排在那间小房子里,最多只让他到院子里,跟店家的两个小孙子耍。留他在店里,还承担着一个任务,便是照看那些没了驴驮,丢了又可惜的行头和那双烂鞋。外人不知,
就在鞋子加厚的鞋底中间,藏着三十多枚大洋,表面上看不出来,穿在脚上感觉却很明显。还有十几枚银洋,耿六是藏在驴鞍子里,这些钱是老爹要他带回后套买田盖房娶媳妇的费用。
十多天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和头续,耿六有点焦燥,决定到更近的地方去打听一下。为了安全起见,出门的时候,他把那鞋和别的几样东西捆成一搭,还有那套驴鞍子,一起寄放在了和屈三强老汉有老交情的店老板处。
到了山下,还没等耿六看清情况,就被山上拉枪栓的响声给吓得跑了回来。不过冒险让他近距离感觉了一下那山势的险峻。这时的耿六开始熟悉了当地,也认识了几个人,还参加了一家人为儿子办的婚礼,领上耿光祖吃了一顿喜宴。他的这种大意,表现在言语上,就是忍不住探听秃三爷和山上的事情。
十五这一天,镇上突然来了一些做小买卖的货郎挑子,自然也多出了许多的山汉和闲人,而且从四面八方的沟沟和圪梁上,还不断有人赶过来。这一变化引发了耿六的注意,在一个饭滩子前坐下,要了碗油泼荞面,边吃边与卖饭的聊天,知道这是本镇每月一次赶集的日子。
赶集是山里人忙中偷闲,走出大山沟,汇聚在平时很少光临的集镇上,看亲戚,吃风味,卖多余,买必需,交流信息,恰谈生意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日子。人多是最大的特色。这样的日子里,秃三爷会不会也来露面?屈三强老汉会不会也来镇上走动呢?在这个有太多可能的日子,耿六四处走动,腿勤嘴多,加倍注意,想着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中间,耿六回到了小旅馆,耿光祖还在睡觉,这个大头侄儿经常是醒过来不睡,睡着了不想醒。耿六没去打扰,自管坐在一把烂凳子上吸旱烟。店东家过来攀谈了几句,也没个正经内容。歇了一会,他再一次来到镇子最中心的地方,登到一处高台子上,看着越来越多的山民身穿各种布衫,背了背篓,领了孩子,西边的往东边蠕动,东边的往西边挪移,南边的一块开阔地上,骡马牲畜就形成了一处特殊的市场。
想起了大灰驴,耿六抱着一线希望快步到牲口市场,走了两圈也没发现什么,心情失望的有点郁闷。市场边上,有两个老汉头上罩了变了色的白毛巾,互相伸了手在一个皮筒子里讨价还价。两人谈不拢,一个摇头,一个不屑,牵着牲畜走开了,耿六看着忘记了心事,不由的笑了。
人流攒动的镇街上,远远的有两乘二人抬的遮帘轿子,在开路人的吆喝声中,软颤颤地颠着过来。耿六赶紧围了过去,听人们议论说,怕是哪位奶奶下山来了。他跟了一段路后,轿子并没有停留,径直往西南方向走了。
赶集的日子里并没有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等到太阳西斜,山民四散,一切又都重归以往。耿六一直在土街上来来回回地走,最后怅然若失,麻木而回。吃过了晚饭后,他躺到炕上睡觉,脑子却不由自主翻腾开来。他已经想不起究竟在镇上住了多长时间,开始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有点欠妥,毕竟三哥失踪近五年了,要是人还活着,他一定会自己和家里联系的,现在没消息,怕是……。
白天睡够了的耿光祖,和店家的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捉迷藏。到后来就剩他一人了,百无聊赖回到屋里,学了耿六的样子,也躺在炕上盯了黑黢黢的屋顶看。突然想起了那双烂鞋,他一时情急,把刚刚进入了梦乡的耿六给摇了醒来。耿六听明白后,也没有埋怨,只说自己扔掉了,翻身又睡了。
半夜时分,屋门被“嗵”的一声踹了开来,进来几个大汉,三两下就把耿六给摁倒在炕头。那一刻,耿六首先想到的是劫财,一瞬间还为自己钱不在身边而庆幸。他想起了放在炕边角的那把防身的刀子,刚才居然给忘记了,实在有点窝囊。耿光祖哭了两声,退缩到炕角落哑巴了。店老板闻声举着灯过来,任由一位长脸汉子臭骂,不停地点头哈腰,陪着笑脸。
听出来人是山上的匪徒,专门为抓自己而来,耿六忙辩解说:“几位好汉爷,我是从姚家浴来的,身上有山上的牌子,松一下我给你们找。”几个人并不理会,把炕上的行头家当提起来一通乱抖,散碎的银钱和木牌都跌了出来。借了油灯亮,店家老汉拾了零碎钱票,恭敬地交给了长脸汉子,却被一把拍落在炕上,随手给了耿六两耳光。眼冒金星的耿六,力气被怒气所点燃,一通挣扎过后,胀红了眼睛看着那汉子。
耿六嚷着说:“大爷,我只是来找亲戚的,我没有钱啊,你看那牌子,我是给咱们山上种地的,不信你看呀!”东家老汉在一旁帮着开脱说:“这人确是姚家浴的,前些天跟了斗鸡公一起来的。”那汉子厉声训说:“老温头,你个老家伙,忘了规矩了,这种货色住在你这里,四处打听山上的事,为什么不上告?等到山上问出了情况,你给我小心了。”
随后再没多话,耿六被五花大绑,嘴上塞了烂衣服,眼上蒙了一块黑布,装进了一个黑布袋里。很快,他觉得自己肚子朝下,被驮在了一头骡子身上。躲在墙角的耿光祖跟了出来,六爹六爹地哭叫着,有个家伙上来把他一抱,也放在骡子身上。按那粗声大汉的意思,这孩子一便押到山上去,说不定能套出真话。
骡子一会儿小跑,一会儿碎步而行,一会儿上山,一会儿又好象过沟。袋子里的耿六晕头转向,颠得肚子生疼,想喊又喊不出来,鼻子不停的“嗯嗯”有声。后来,他开始“哇哇”地呕吐,呕吐物少数回流,多数都从鼻孔流了出来。耿光祖爬在骡背上,紧紧地抱了布袋子,保持自己平稳的同时,尽力护着袋子里的六爹。
终于,耿六从几个人的对话中知道,自己被带到山前。再后来,他被从骡子身上推下来,头磕在一块硬石上,痛如锥扎,人就失去了知觉。等他醒过来,觉得身子在空中晃悠,细细一感觉,才知是被一根绳索提升着,搞不清高度,只听见山风劲吹,“呜呜”有声。
绳索慢慢停住,有钩子拉着耿六向一边靠了过去。身子落地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才“嗵”一声落肚。这时,一个声音说:“这个票咋这么晚了才弄到山上来?”另一个声音说:“踢一脚看看,死的还是活的?”耿六忙“嗯”了两声,以示是活着的。前一个声音打了哈欠,笑说:“这家伙倒还聪明,一听要踢他,就活过来了。”一阵铃铛声,前一个声音咕哝说:“咋又有事了,今晚上这差可真麻烦。还是你过去听话吧。”有脚步声离开,传来的话语说:“下面让放一个大吊筐,说是有个小孩。这就怪了,难道他们还绑了个小财主不成?”耿六想到了耿光祖,一份担心倏地升了起来。
耿光祖被安排在那间小房子里,最多只让他到院子里,跟店家的两个小孙子耍。留他在店里,还承担着一个任务,便是照看那些没了驴驮,丢了又可惜的行头和那双烂鞋。外人不知,
就在鞋子加厚的鞋底中间,藏着三十多枚大洋,表面上看不出来,穿在脚上感觉却很明显。还有十几枚银洋,耿六是藏在驴鞍子里,这些钱是老爹要他带回后套买田盖房娶媳妇的费用。
十多天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和头续,耿六有点焦燥,决定到更近的地方去打听一下。为了安全起见,出门的时候,他把那鞋和别的几样东西捆成一搭,还有那套驴鞍子,一起寄放在了和屈三强老汉有老交情的店老板处。
到了山下,还没等耿六看清情况,就被山上拉枪栓的响声给吓得跑了回来。不过冒险让他近距离感觉了一下那山势的险峻。这时的耿六开始熟悉了当地,也认识了几个人,还参加了一家人为儿子办的婚礼,领上耿光祖吃了一顿喜宴。他的这种大意,表现在言语上,就是忍不住探听秃三爷和山上的事情。
十五这一天,镇上突然来了一些做小买卖的货郎挑子,自然也多出了许多的山汉和闲人,而且从四面八方的沟沟和圪梁上,还不断有人赶过来。这一变化引发了耿六的注意,在一个饭滩子前坐下,要了碗油泼荞面,边吃边与卖饭的聊天,知道这是本镇每月一次赶集的日子。
赶集是山里人忙中偷闲,走出大山沟,汇聚在平时很少光临的集镇上,看亲戚,吃风味,卖多余,买必需,交流信息,恰谈生意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日子。人多是最大的特色。这样的日子里,秃三爷会不会也来露面?屈三强老汉会不会也来镇上走动呢?在这个有太多可能的日子,耿六四处走动,腿勤嘴多,加倍注意,想着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中间,耿六回到了小旅馆,耿光祖还在睡觉,这个大头侄儿经常是醒过来不睡,睡着了不想醒。耿六没去打扰,自管坐在一把烂凳子上吸旱烟。店东家过来攀谈了几句,也没个正经内容。歇了一会,他再一次来到镇子最中心的地方,登到一处高台子上,看着越来越多的山民身穿各种布衫,背了背篓,领了孩子,西边的往东边蠕动,东边的往西边挪移,南边的一块开阔地上,骡马牲畜就形成了一处特殊的市场。
想起了大灰驴,耿六抱着一线希望快步到牲口市场,走了两圈也没发现什么,心情失望的有点郁闷。市场边上,有两个老汉头上罩了变了色的白毛巾,互相伸了手在一个皮筒子里讨价还价。两人谈不拢,一个摇头,一个不屑,牵着牲畜走开了,耿六看着忘记了心事,不由的笑了。
人流攒动的镇街上,远远的有两乘二人抬的遮帘轿子,在开路人的吆喝声中,软颤颤地颠着过来。耿六赶紧围了过去,听人们议论说,怕是哪位奶奶下山来了。他跟了一段路后,轿子并没有停留,径直往西南方向走了。
赶集的日子里并没有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等到太阳西斜,山民四散,一切又都重归以往。耿六一直在土街上来来回回地走,最后怅然若失,麻木而回。吃过了晚饭后,他躺到炕上睡觉,脑子却不由自主翻腾开来。他已经想不起究竟在镇上住了多长时间,开始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有点欠妥,毕竟三哥失踪近五年了,要是人还活着,他一定会自己和家里联系的,现在没消息,怕是……。
白天睡够了的耿光祖,和店家的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捉迷藏。到后来就剩他一人了,百无聊赖回到屋里,学了耿六的样子,也躺在炕上盯了黑黢黢的屋顶看。突然想起了那双烂鞋,他一时情急,把刚刚进入了梦乡的耿六给摇了醒来。耿六听明白后,也没有埋怨,只说自己扔掉了,翻身又睡了。
半夜时分,屋门被“嗵”的一声踹了开来,进来几个大汉,三两下就把耿六给摁倒在炕头。那一刻,耿六首先想到的是劫财,一瞬间还为自己钱不在身边而庆幸。他想起了放在炕边角的那把防身的刀子,刚才居然给忘记了,实在有点窝囊。耿光祖哭了两声,退缩到炕角落哑巴了。店老板闻声举着灯过来,任由一位长脸汉子臭骂,不停地点头哈腰,陪着笑脸。
听出来人是山上的匪徒,专门为抓自己而来,耿六忙辩解说:“几位好汉爷,我是从姚家浴来的,身上有山上的牌子,松一下我给你们找。”几个人并不理会,把炕上的行头家当提起来一通乱抖,散碎的银钱和木牌都跌了出来。借了油灯亮,店家老汉拾了零碎钱票,恭敬地交给了长脸汉子,却被一把拍落在炕上,随手给了耿六两耳光。眼冒金星的耿六,力气被怒气所点燃,一通挣扎过后,胀红了眼睛看着那汉子。
耿六嚷着说:“大爷,我只是来找亲戚的,我没有钱啊,你看那牌子,我是给咱们山上种地的,不信你看呀!”东家老汉在一旁帮着开脱说:“这人确是姚家浴的,前些天跟了斗鸡公一起来的。”那汉子厉声训说:“老温头,你个老家伙,忘了规矩了,这种货色住在你这里,四处打听山上的事,为什么不上告?等到山上问出了情况,你给我小心了。”
随后再没多话,耿六被五花大绑,嘴上塞了烂衣服,眼上蒙了一块黑布,装进了一个黑布袋里。很快,他觉得自己肚子朝下,被驮在了一头骡子身上。躲在墙角的耿光祖跟了出来,六爹六爹地哭叫着,有个家伙上来把他一抱,也放在骡子身上。按那粗声大汉的意思,这孩子一便押到山上去,说不定能套出真话。
骡子一会儿小跑,一会儿碎步而行,一会儿上山,一会儿又好象过沟。袋子里的耿六晕头转向,颠得肚子生疼,想喊又喊不出来,鼻子不停的“嗯嗯”有声。后来,他开始“哇哇”地呕吐,呕吐物少数回流,多数都从鼻孔流了出来。耿光祖爬在骡背上,紧紧地抱了布袋子,保持自己平稳的同时,尽力护着袋子里的六爹。
终于,耿六从几个人的对话中知道,自己被带到山前。再后来,他被从骡子身上推下来,头磕在一块硬石上,痛如锥扎,人就失去了知觉。等他醒过来,觉得身子在空中晃悠,细细一感觉,才知是被一根绳索提升着,搞不清高度,只听见山风劲吹,“呜呜”有声。
绳索慢慢停住,有钩子拉着耿六向一边靠了过去。身子落地的那一瞬间,他的心才“嗵”一声落肚。这时,一个声音说:“这个票咋这么晚了才弄到山上来?”另一个声音说:“踢一脚看看,死的还是活的?”耿六忙“嗯”了两声,以示是活着的。前一个声音打了哈欠,笑说:“这家伙倒还聪明,一听要踢他,就活过来了。”一阵铃铛声,前一个声音咕哝说:“咋又有事了,今晚上这差可真麻烦。还是你过去听话吧。”有脚步声离开,传来的话语说:“下面让放一个大吊筐,说是有个小孩。这就怪了,难道他们还绑了个小财主不成?”耿六想到了耿光祖,一份担心倏地升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