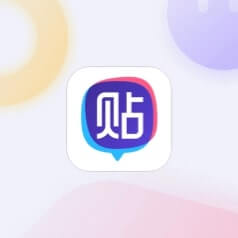当我继续观察辐背兽的时候,我注意到它的步态中有一种新的坚定,我想知道是什么引起了它的注意——又是怎么引起的。突然间,我打开了与耳机外部麦克风相连的内置扬声器,立刻就听到了一连串尖锐的砰砰声,很明显是来自辐背兽。
它在使用声纳!
这时,它的速度已提高到令人生畏的每小时四十五公里,并以巨大的跳跃在地面上行驶。从我所处的高度来看,我几乎看不清四百米开外有个小身影在高高的草丛中奔跑。当它冲出草丛来到一片平坦的地面上时,它的速度加快了,我确信追赶它的辐背兽是追不上的。我是对的。
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声纳声波,这两只动物的追逐几乎延伸了五公里,它们都在急转弯,在岩石和洼地上跳跃。尽管我测得辐背兽的时速为48公里,但它的猎物奔跑的速度几乎是这个速度的两倍,而且还在疯狂地机动。如果追逐在更近的距离开始,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这一天,辐背兽失败了。它摇晃着身子,停止了捕猎,小跑着停了下来;然后它跪下来,以我发现它时的姿势休息。
我的兴趣难以捉摸的猎物激起了我的兴趣,我把电脑设置成追踪这只还在奔跑的动物,然后加速追赶。13吨饥饿的骨头、肌肉和软骨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在我的盘旋锥中,在空调的舒适中实现了。锥体喷着气,涡轮风扇呼呼作响,我下面的草地变成了一片棕色的模糊;几分钟后,计算机的采集铃声响了。
(回旋奔兽的两米长的舌头卷起来,停在它两个心脏之间的胸腔里。它脖子末端的头上没有大脑。)

它在使用声纳!
这时,它的速度已提高到令人生畏的每小时四十五公里,并以巨大的跳跃在地面上行驶。从我所处的高度来看,我几乎看不清四百米开外有个小身影在高高的草丛中奔跑。当它冲出草丛来到一片平坦的地面上时,它的速度加快了,我确信追赶它的辐背兽是追不上的。我是对的。
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声纳声波,这两只动物的追逐几乎延伸了五公里,它们都在急转弯,在岩石和洼地上跳跃。尽管我测得辐背兽的时速为48公里,但它的猎物奔跑的速度几乎是这个速度的两倍,而且还在疯狂地机动。如果追逐在更近的距离开始,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在这一天,辐背兽失败了。它摇晃着身子,停止了捕猎,小跑着停了下来;然后它跪下来,以我发现它时的姿势休息。
我的兴趣难以捉摸的猎物激起了我的兴趣,我把电脑设置成追踪这只还在奔跑的动物,然后加速追赶。13吨饥饿的骨头、肌肉和软骨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在我的盘旋锥中,在空调的舒适中实现了。锥体喷着气,涡轮风扇呼呼作响,我下面的草地变成了一片棕色的模糊;几分钟后,计算机的采集铃声响了。
(回旋奔兽的两米长的舌头卷起来,停在它两个心脏之间的胸腔里。它脖子末端的头上没有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