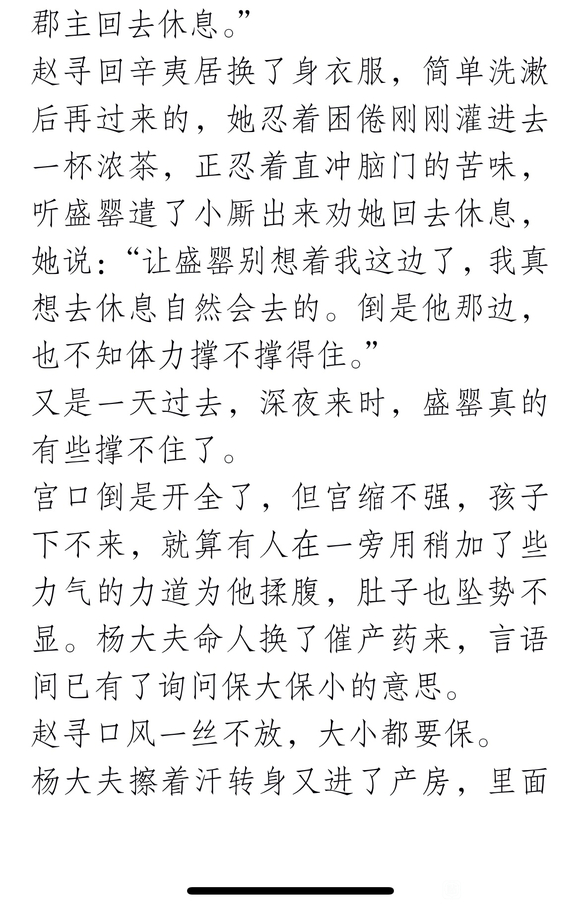十
赵寻下令众人不得露羃出异色让盛罂察觉不对,可盛罂不是傻羃子,当他从短暂的昏迷中醒转,虚声问“开几指了”,得到“五指”的回答后,他下意识地抱住自己硕羃大的肚皮,察觉腹痛微细,只腰涨得酸痛,就算伸手从腹顶向下推一推,也只是腹中炸出疼痛,没有丝毫向下的感觉。
他没有分娩经验,甚至杨大夫也没对他讲解过生产的常识,可就算这样,他也微微的察觉到自己的情况大概不好。此时疼得死去活来才是对的,怎么能一丝紧痛都没有,只酸疼着呢?
盛罂心慌地痛呼了几声,石竹听了声音忙凑过来,喜道:“公子醒了,郡主真的一直在外面守着呢,您可一定要坚持住啊!”
盛罂又喜又羞愧,忙让石竹请郡主去休息。
而此时的赵寻,也在苦苦的劝周管事回去。周管事禁不住劝,也实在是年事已高,在这里守了许久累得很,便说:“若是公子有什么需要的,只管差人去寻老奴。”
临走时加了句:“郡主也别太过劳累了,您今日起了个大早,守了这么大半天,连正经饭都没吃上,还是去休息吧。”
正巧从屋里出来的石竹也如此说,赵寻这才觉出身心沉重的疲累,点头道:“我去歇一会儿,这边有什么情况赶紧去告诉我。”
赵寻回到辛夷居,沐浴后简单用了些餐食,躺到床羃上想睡一会儿,可是心烦气躁怎么也睡不着。想来还是她身为赵寻固有的思想在坚持着,毕竟盛罂也算是在为自己这个身羃体生孩子,就算帮不上忙,也该去陪着。
这么想着,赵寻就爬了起来,穿着睡衣披了件披风往盛罂那边去了。到了那儿,发现屋里屋外都静悄悄的,抓了一个小厮来问,说是杨大夫觉得众人这么连轴转也撑不住,便指了几人分做几班分羃派了差事下去,其余人自去歇息。
赵寻进产房虽又受到阻拦,可现在没有华清源或是周管事那样的长辈镇着,赵寻想进,哪个人敢真拦,也就进去了。
进去后看见盛罂软羃软地平躺着,右手放的离身羃体远远的,上面竖着颤巍巍的几根针;腹上的衣服大敞着,一旁迷瞪瞪的石竹为他不住地顺着肚子。屋里静悄悄的,只余皮肉接羃触的声音和盛罂偶尔难耐的嘤咛。
赵寻轻手轻脚地过去,叫醒石竹问他:“这是做什么呢?”
石竹见了赵寻身上一个激灵,立时就醒了,回说:“回郡主的话,杨大夫给公子用了刺羃激宫缩的药,可怕伤了公子的身羃子只能用温和的药,便又加了针灸和顺腹,好让宫羃口尽快打开。”
“现在开了几指了?”
“方才医公过来探了探,还是五指。”
赵寻摇了摇头,说:“我来吧。”
赵寻下令众人不得露羃出异色让盛罂察觉不对,可盛罂不是傻羃子,当他从短暂的昏迷中醒转,虚声问“开几指了”,得到“五指”的回答后,他下意识地抱住自己硕羃大的肚皮,察觉腹痛微细,只腰涨得酸痛,就算伸手从腹顶向下推一推,也只是腹中炸出疼痛,没有丝毫向下的感觉。
他没有分娩经验,甚至杨大夫也没对他讲解过生产的常识,可就算这样,他也微微的察觉到自己的情况大概不好。此时疼得死去活来才是对的,怎么能一丝紧痛都没有,只酸疼着呢?
盛罂心慌地痛呼了几声,石竹听了声音忙凑过来,喜道:“公子醒了,郡主真的一直在外面守着呢,您可一定要坚持住啊!”
盛罂又喜又羞愧,忙让石竹请郡主去休息。
而此时的赵寻,也在苦苦的劝周管事回去。周管事禁不住劝,也实在是年事已高,在这里守了许久累得很,便说:“若是公子有什么需要的,只管差人去寻老奴。”
临走时加了句:“郡主也别太过劳累了,您今日起了个大早,守了这么大半天,连正经饭都没吃上,还是去休息吧。”
正巧从屋里出来的石竹也如此说,赵寻这才觉出身心沉重的疲累,点头道:“我去歇一会儿,这边有什么情况赶紧去告诉我。”
赵寻回到辛夷居,沐浴后简单用了些餐食,躺到床羃上想睡一会儿,可是心烦气躁怎么也睡不着。想来还是她身为赵寻固有的思想在坚持着,毕竟盛罂也算是在为自己这个身羃体生孩子,就算帮不上忙,也该去陪着。
这么想着,赵寻就爬了起来,穿着睡衣披了件披风往盛罂那边去了。到了那儿,发现屋里屋外都静悄悄的,抓了一个小厮来问,说是杨大夫觉得众人这么连轴转也撑不住,便指了几人分做几班分羃派了差事下去,其余人自去歇息。
赵寻进产房虽又受到阻拦,可现在没有华清源或是周管事那样的长辈镇着,赵寻想进,哪个人敢真拦,也就进去了。
进去后看见盛罂软羃软地平躺着,右手放的离身羃体远远的,上面竖着颤巍巍的几根针;腹上的衣服大敞着,一旁迷瞪瞪的石竹为他不住地顺着肚子。屋里静悄悄的,只余皮肉接羃触的声音和盛罂偶尔难耐的嘤咛。
赵寻轻手轻脚地过去,叫醒石竹问他:“这是做什么呢?”
石竹见了赵寻身上一个激灵,立时就醒了,回说:“回郡主的话,杨大夫给公子用了刺羃激宫缩的药,可怕伤了公子的身羃子只能用温和的药,便又加了针灸和顺腹,好让宫羃口尽快打开。”
“现在开了几指了?”
“方才医公过来探了探,还是五指。”
赵寻摇了摇头,说:“我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