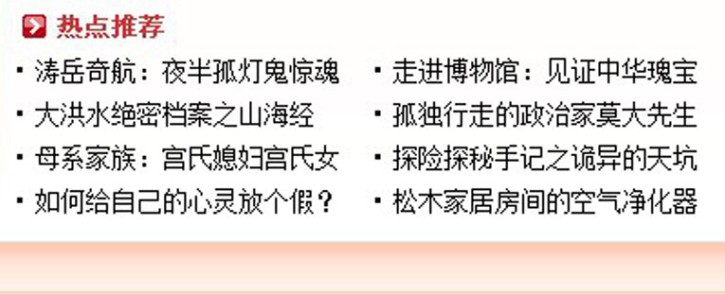43
而后,他们都在笼外站着,眼神蹊跷地看着自己。航生眯了眼正觉得怪,心灯道长缓缓说了:
“航生,今天夜里,你要一个人睡了。”
航生一怕,眼朝舅舅看。
德根舅舅一手伸进笼里,摸摸航生的脑袋说:“航生,莫怕!舅舅和道长几个虽然不在这房,可只要一有动静就会赶来。有这个笼子罩着,你不会有事的,知道不?”
看到航生快哭的模样,施先生赶紧转头对道长说:“要不,老朽夜晚还睡航生对面这床,帮航生壮个胆?老朽年事已高,身上阳气荡然无存,想必那非人也察觉不出丝毫来。”
道长摇摇头:“非人生性狡黠,昨天夜里就是楼上人多,它进了屋却没上来,楼上人越少越好,还是按说好的办吧。”说罢他朝德根点点头,德根拍拍航生后背,就带了众人鱼贯出门了,最后走出的心灯道长在门口转过身来,提起灯笼照看了下四壁,低了头,定定地看了看笼内的航生,说:
“航生,男子胆要大!莫怕!”
说罢,他碰上门,房内顿时暗下了。
航生心里凉飕飕的,门外那群大人绕着楼道走来走去,似乎在验查着什么。木笼四角都已绑死了麻绳,想自己出笼也不可能了。航生摇了摇笼杆,这大桃木笼纹丝不动,异常沉重而牢固。但航生又担心了,那东西如果真从这大人拳头宽的笼格间钻进来,不就和它关一个笼里了?
航生越想越怕,抱了膝盖,紧缩在最里面一角,不时哆嗦几下。此时,他听到了门外大人脚步向楼梯踏下去,他们一个个下楼了。
房内昏暗,航生树着耳朵倾听。起先,楼下还隐隐几句人声传来,稍后,就悄然无声了,他们到哪里去了?
屋外逐渐起风了。
夜风拂在窗纸上,哗哗作响。桌上那盏油灯的火苗开始乱颤,晃动了这昏暗的房间里所有黑色阴影,看去这房间诡谲地在动,看着头晕目眩。
大风呼啸中,楼底不时传来松动的大门碰撞声“嘭…嘭……”,或轻或重,每次撞响,都让航生揪了心,总觉得是那东西闯进门了。
航生心烦意乱,在笼里又无可奈何,他只有贴着笼子内侧躺了下来,拉上那条薄被子,强闭了眼,双手捂耳。一心想着早点入睡,醒来就是明朗朗的大白天。
前两晚房里睡着大人,均能安然入睡。此时,航生卷曲着,耳中听着夜风呼啸,越睡越清醒。他半睁了眼,凝视着暗影摇曳的房梁上空,不知多久了。
风声越来越大了,呜呜啸嗥,像是有一个山般大的长毛巨怪四肢撑在村野上空怒嗥着,狂暴地发泄着它无穷无尽的坏脾气。外面不时传来别人家窗户吹开的呯啪声,以及瓦片、盆子吹落的迸裂声,还隐约夹着一两声妇人的惊叫。
飞沙细石不时吹打在窗纸上,像是炒着爆豆。航生甚至闻到了许些硫磺味,那些屋外墙角的硫磺粉被吹得漫天飞舞了吧…
“呯”得一声暴响,航生骇得浑身一缩,窗户上打上一截被风吹落的枯枝,把窗纸戳了一个破洞,灌进的乱风瞬间把油灯火苗拂灭,房间顿时漆黑了。
航生一时方寸大乱,没有比听着野兽般嗥叫的风啸,瞪着黑黢黢的房间睡不着更可怕了。一黑下来,这遮风挡雨的房间似乎就比外面更恐怖了。那个给他带来安全感的木笼似乎也不见了。强挺了会儿,航生实在忍受不了,战战兢兢地翻起身来。
这黑太难忍了,油灯还得点亮。漆黑一片中,他双手伸出笼杆,在桌上摸索着,手指摸到了凉冰冰的火镰石和纸媒罐。航生小心翼翼拿进笼里,抽出纸媒,双手敲起火镰石。

不像舅舅敲个两三下,就能引燃纸媒,航生总要敲个二三十下,才能侥幸引燃。
噼啪敲着,黑暗中火星四溅。通常舅舅是不允许在床上敲火镰的,但这声响夹在呜呜不休的风啸中,显得极其轻微。敲到第二十九下,火星终于引燃了纸媒。
就借着这一亮,他看到近处床前霍然站着个黑糊糊的人形!
它低了颤巍巍的头部看着自己,它黑糊糊斗篷下面,有极小两点亮,那是它眼里映出的纸媒火光,闪烁着难以言传的阴鸷和诡谲。
航生石化似的呆望着,正忖着是不是幻觉,它突然张了臂扑上了,航生猛得向后一退,撞在身后的笼杆上,他闭了眼失声尖叫:“救命!它来了——”
燃着的纸媒被甩到了枕头边上,燃着了薄被子的一角。火光闪烁中,航生眼见着它的双爪抓了笼杆,使劲拉扯笼杆,喀嚓裂响着,似乎要折断这么粗的桃杆也不是件难事。
航生只有尖叫不休了。
而后,他们都在笼外站着,眼神蹊跷地看着自己。航生眯了眼正觉得怪,心灯道长缓缓说了:
“航生,今天夜里,你要一个人睡了。”
航生一怕,眼朝舅舅看。
德根舅舅一手伸进笼里,摸摸航生的脑袋说:“航生,莫怕!舅舅和道长几个虽然不在这房,可只要一有动静就会赶来。有这个笼子罩着,你不会有事的,知道不?”
看到航生快哭的模样,施先生赶紧转头对道长说:“要不,老朽夜晚还睡航生对面这床,帮航生壮个胆?老朽年事已高,身上阳气荡然无存,想必那非人也察觉不出丝毫来。”
道长摇摇头:“非人生性狡黠,昨天夜里就是楼上人多,它进了屋却没上来,楼上人越少越好,还是按说好的办吧。”说罢他朝德根点点头,德根拍拍航生后背,就带了众人鱼贯出门了,最后走出的心灯道长在门口转过身来,提起灯笼照看了下四壁,低了头,定定地看了看笼内的航生,说:
“航生,男子胆要大!莫怕!”
说罢,他碰上门,房内顿时暗下了。
航生心里凉飕飕的,门外那群大人绕着楼道走来走去,似乎在验查着什么。木笼四角都已绑死了麻绳,想自己出笼也不可能了。航生摇了摇笼杆,这大桃木笼纹丝不动,异常沉重而牢固。但航生又担心了,那东西如果真从这大人拳头宽的笼格间钻进来,不就和它关一个笼里了?
航生越想越怕,抱了膝盖,紧缩在最里面一角,不时哆嗦几下。此时,他听到了门外大人脚步向楼梯踏下去,他们一个个下楼了。
房内昏暗,航生树着耳朵倾听。起先,楼下还隐隐几句人声传来,稍后,就悄然无声了,他们到哪里去了?
屋外逐渐起风了。
夜风拂在窗纸上,哗哗作响。桌上那盏油灯的火苗开始乱颤,晃动了这昏暗的房间里所有黑色阴影,看去这房间诡谲地在动,看着头晕目眩。
大风呼啸中,楼底不时传来松动的大门碰撞声“嘭…嘭……”,或轻或重,每次撞响,都让航生揪了心,总觉得是那东西闯进门了。
航生心烦意乱,在笼里又无可奈何,他只有贴着笼子内侧躺了下来,拉上那条薄被子,强闭了眼,双手捂耳。一心想着早点入睡,醒来就是明朗朗的大白天。
前两晚房里睡着大人,均能安然入睡。此时,航生卷曲着,耳中听着夜风呼啸,越睡越清醒。他半睁了眼,凝视着暗影摇曳的房梁上空,不知多久了。
风声越来越大了,呜呜啸嗥,像是有一个山般大的长毛巨怪四肢撑在村野上空怒嗥着,狂暴地发泄着它无穷无尽的坏脾气。外面不时传来别人家窗户吹开的呯啪声,以及瓦片、盆子吹落的迸裂声,还隐约夹着一两声妇人的惊叫。
飞沙细石不时吹打在窗纸上,像是炒着爆豆。航生甚至闻到了许些硫磺味,那些屋外墙角的硫磺粉被吹得漫天飞舞了吧…
“呯”得一声暴响,航生骇得浑身一缩,窗户上打上一截被风吹落的枯枝,把窗纸戳了一个破洞,灌进的乱风瞬间把油灯火苗拂灭,房间顿时漆黑了。
航生一时方寸大乱,没有比听着野兽般嗥叫的风啸,瞪着黑黢黢的房间睡不着更可怕了。一黑下来,这遮风挡雨的房间似乎就比外面更恐怖了。那个给他带来安全感的木笼似乎也不见了。强挺了会儿,航生实在忍受不了,战战兢兢地翻起身来。
这黑太难忍了,油灯还得点亮。漆黑一片中,他双手伸出笼杆,在桌上摸索着,手指摸到了凉冰冰的火镰石和纸媒罐。航生小心翼翼拿进笼里,抽出纸媒,双手敲起火镰石。

不像舅舅敲个两三下,就能引燃纸媒,航生总要敲个二三十下,才能侥幸引燃。
噼啪敲着,黑暗中火星四溅。通常舅舅是不允许在床上敲火镰的,但这声响夹在呜呜不休的风啸中,显得极其轻微。敲到第二十九下,火星终于引燃了纸媒。
就借着这一亮,他看到近处床前霍然站着个黑糊糊的人形!
它低了颤巍巍的头部看着自己,它黑糊糊斗篷下面,有极小两点亮,那是它眼里映出的纸媒火光,闪烁着难以言传的阴鸷和诡谲。
航生石化似的呆望着,正忖着是不是幻觉,它突然张了臂扑上了,航生猛得向后一退,撞在身后的笼杆上,他闭了眼失声尖叫:“救命!它来了——”
燃着的纸媒被甩到了枕头边上,燃着了薄被子的一角。火光闪烁中,航生眼见着它的双爪抓了笼杆,使劲拉扯笼杆,喀嚓裂响着,似乎要折断这么粗的桃杆也不是件难事。
航生只有尖叫不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