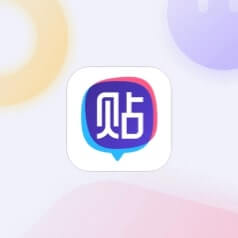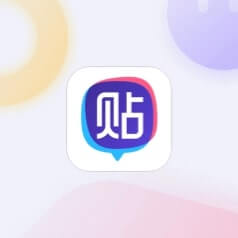Puffbird鹀(Arcosphaeracochleavenator):最小的不飞雀鸥之一,成年体重只有一磅左右,这种小型物种属于一个谱系,该谱系可能填补了大陆上被嗅探鸟占据的生态位,并且在冰河时代海平面下降使莫洛齿兽入侵子午线群岛时,它们大部分灭绝了,整个家族只有鹀幸免于难,因为它有特殊的饮食习惯;它主要吃特定种类的有毒沿海蜗牛(这些蜗牛本身从以某些种类的藻类为食中获得毒素),它从这些软体动物中摄取的毒素会积聚在它的肉和羽毛中。鹀能够隔离毒素并将其转移到羽毛中,使它们同样令人厌恶,这通过异常鲜艳的颜色来宣传。
多余的毒素通过排泄物排出,它们可以利用排泄物中的消化液进行额外的防御,瞄准眼睛或其他敏感部位喷射出去。利用钩状的喙,它们可以干净利落地将蜗牛从壳中剥开,并钩出柔软的肉。更多新来的雀鸥尚未进化出对这些有毒猎物的同等防御能力,因此鹀暂时得以生存。他们的喙是一种多功能工具,而不仅仅是蜗牛提取器,而且它们的饮食也不是那么特殊,它们还可以从木头下面挖出蛴螬,从果壳中获得可食用的种子;在冬季,它们会进一步深入内陆寻找食物,种子和蛴螬构成了它们食物的主要部分,而不是蜗牛。鹀在海岸附近的悬崖和隐蔽处筑巢,很少离开巢穴超过一两公里,因为它们每晚都必须回到巢穴躲避寒冷的黑暗。人们经常看到鹀与在海滩上休息的海燕和其他雀鸥混在一起,趁机捕食那些无休止寄生在它们身上的苍蝇和其他叮咬寄生虫,这些体型较大的海滩居民非常乐意翻身让这些小而敏捷的鸟儿把它们啄得干干净净。

多余的毒素通过排泄物排出,它们可以利用排泄物中的消化液进行额外的防御,瞄准眼睛或其他敏感部位喷射出去。利用钩状的喙,它们可以干净利落地将蜗牛从壳中剥开,并钩出柔软的肉。更多新来的雀鸥尚未进化出对这些有毒猎物的同等防御能力,因此鹀暂时得以生存。他们的喙是一种多功能工具,而不仅仅是蜗牛提取器,而且它们的饮食也不是那么特殊,它们还可以从木头下面挖出蛴螬,从果壳中获得可食用的种子;在冬季,它们会进一步深入内陆寻找食物,种子和蛴螬构成了它们食物的主要部分,而不是蜗牛。鹀在海岸附近的悬崖和隐蔽处筑巢,很少离开巢穴超过一两公里,因为它们每晚都必须回到巢穴躲避寒冷的黑暗。人们经常看到鹀与在海滩上休息的海燕和其他雀鸥混在一起,趁机捕食那些无休止寄生在它们身上的苍蝇和其他叮咬寄生虫,这些体型较大的海滩居民非常乐意翻身让这些小而敏捷的鸟儿把它们啄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