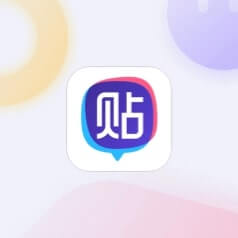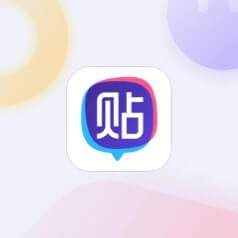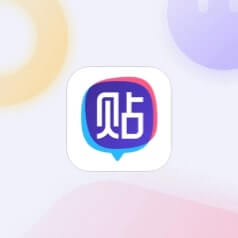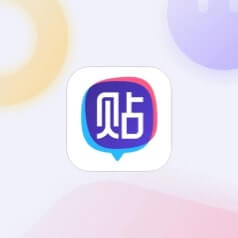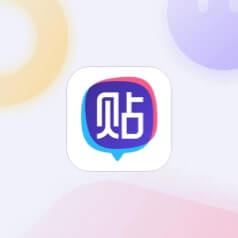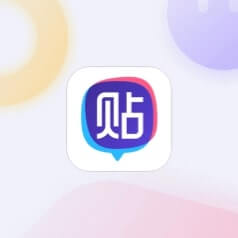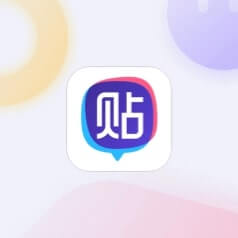不断上升的威胁:
战争贩子The Warmonger
渔民与牧民之间的现代争斗,是由牧民对诺普人的明显剥削而产生的。实际上,他们的道德差距被过分夸大了。早期的白日梦者会无差别屠杀所有的智慧海豚雀,而今天,牧民几乎完全依赖他们的牲畜,善待它们,尽量保护他们并且仁慈地处死诺普人,甚至与野生小海豚也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通常根本不捕猎野生动物。如今,诺普人大多成了渔民与牧民争斗的接口和替罪羊,因为历史在无数代人的口头重复中被扭曲了。这两种文化实际上比看起来的要相似得多。那么真正的威胁到底指什么呢?
我们之前提到,白日梦者有很多种族,不仅仅只有渔民和牧民。实际上,牧民并不是海洋中唯一专门捕猎大型猎物的白日梦文化。由于其他文化具有更相似的外貌,都属于同一生态型,渔民历来将它们归为一类,称为这种罪恶的“他者”。
因此,渔民对牧民的假设是错误的,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海洋中还有一些更大、更危险的白日梦者民族,他们依然会杀死其他近智生物来获取食物。另一个子集和渔民几乎同时间从共同祖先中分化,他们也不再饲养牲畜,但他们是更加强壮的猎人,追逐和杀死各种野生动物,尤其是其他海豚雀。这些捕鲸人是最大的白日梦者亚种,他们体格强健,可以捕食大型动物猎物。
在过去,捕鲸人和牧民之间经常有一条畅通的贸易和交流渠道,渔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也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归为一类。但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千年里发生了变化,气候变化使海水变浅,除了离海岸最远的水域,捕鲸人也远离了植被茂密的浅水区。长期以来,渔民和牧民一直是他们活动范围内唯一经常相遇的其他种族,但渔民们仍然把牧民定型为滥杀无辜的杀手,因为他们的喙结构和捕鲸人很相似。渔民和牧民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对方的文化,但他们的战争是冷战,冷嘲热讽比血腥冲突要多得多。牧民作为一个整体,只想独处,完全拒绝渔民文化,但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被认为是无聊的,最近出现了一种趋势,年轻的牧民偶尔会在青春期脱离自己的族群,融入渔民文化。尽管渔民们态度高人一等,但他们通常都能接受不同的人,并愿意与他们建立联系,只要他们相应地调整饮食(然而,因为这些“叛逃者”长着大牙齿的脸,对他们的偏见依然存在。)
最近,即使是如此小规模的牧民与渔民融合也开始在两者之间古老的鸿沟上架起最小的桥梁。通过这些年轻、叛逆的新成员加入他们的文化,渔民们了解到,牧民也相信从根本上讲相同的创世故事。一些渔民现在认识到相似之处可能大于差异,甚至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比对手更道德。然而,牧民文化仍然抵制任何外界影响,长者们坚决地与那些背叛他们与敌人交往的少年人断绝关系。因此,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任何团结的迹象似乎都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如果没有双方共同的努力,渔民和牧民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稳定联系。
但现在,无论是渔民还是农民,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两个新的变量几乎同时出现:
第一个因素是渔民声称找到了预言中的造物主的“手”,即两个失踪的造物主精华之一……甚至一些牧民也对这个想法感到好奇。面对那些传递信息的叛徒,那些保守的牧民可能会说:“渔民的脑袋里充满了热水,他们说的话太多了,以至于什么都不说。”但叛徒们已经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坚持这一次他们说的是实话。尽管他们不确定,但风险太大,他们不能不冒险……因为第二个因素出现了,这场古老竞争中的两个派系都必须应对一个新的种族带来的的致命威胁:失踪的捕鲸者突然返回沿海浅滩。自从他们离开后,他们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变化。
好战者Warmonger是捕鲸者中一个极端孤立的分支,他们通过数千年的故意近亲繁殖而形成,以支持新的隐性模式特征和缺乏黄色皮肤色素。他们的语言是所有种族中从起源点开始差异最大的。他们的语言深沉、缓慢、令人难以忘怀,对渔民来说,他们的语言比掘墓人的语言更难懂,而且他们很少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所有捕鲸者都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以免被发现。
他们与其他文化的历史交流仍然构成了好战者宗教的基础,但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好战者不再相信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古代造物主还有其他部分精华。他们相信他们的人民是神的唯一正统后代(太典了),他们认为自己比所有其他生命更加高贵。他们的巨大体型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优势地位,平均比牧民或渔民大 20%,头部和下颚明显更大,适合杀死大型海洋猎物。好战者进化为成群结队地捕猎,协调性极强。自然而然,白日梦者常见的那种松散群体让位于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而牧民或渔民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这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致命威胁,因为这个不断扩张的极端主义团体密谋通过消灭较弱的对手来展示他们对世界的终极权力……吃掉并灭绝其他的种族——这是终极的统治行为(豚特勒是吧)。
好战者是一个具有唯一领导者的统一战线,他们杀戮所有海豚雀,也不区分渔民和牧民。在他们看来,除自己种族之外的所有海豚雀都是红肉。
如今,为了抵抗不断增加的针对其他白日梦者的猎杀行动,牧民本不愿意和渔民联合。他们知道自己人数比渔民多,他们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自卫。但是叛逃者带来了充满诱惑力的条件:如果牧民期待已久的造物主之手真的已经回归并召集他们……那他们就不会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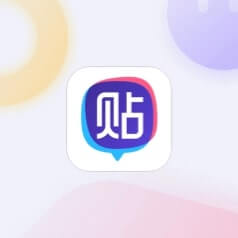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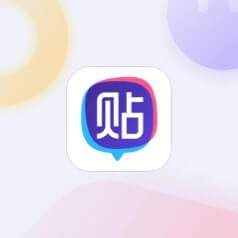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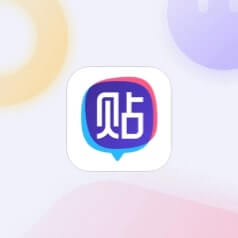

战争贩子The Warmonger
渔民与牧民之间的现代争斗,是由牧民对诺普人的明显剥削而产生的。实际上,他们的道德差距被过分夸大了。早期的白日梦者会无差别屠杀所有的智慧海豚雀,而今天,牧民几乎完全依赖他们的牲畜,善待它们,尽量保护他们并且仁慈地处死诺普人,甚至与野生小海豚也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通常根本不捕猎野生动物。如今,诺普人大多成了渔民与牧民争斗的接口和替罪羊,因为历史在无数代人的口头重复中被扭曲了。这两种文化实际上比看起来的要相似得多。那么真正的威胁到底指什么呢?
我们之前提到,白日梦者有很多种族,不仅仅只有渔民和牧民。实际上,牧民并不是海洋中唯一专门捕猎大型猎物的白日梦文化。由于其他文化具有更相似的外貌,都属于同一生态型,渔民历来将它们归为一类,称为这种罪恶的“他者”。
因此,渔民对牧民的假设是错误的,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海洋中还有一些更大、更危险的白日梦者民族,他们依然会杀死其他近智生物来获取食物。另一个子集和渔民几乎同时间从共同祖先中分化,他们也不再饲养牲畜,但他们是更加强壮的猎人,追逐和杀死各种野生动物,尤其是其他海豚雀。这些捕鲸人是最大的白日梦者亚种,他们体格强健,可以捕食大型动物猎物。
在过去,捕鲸人和牧民之间经常有一条畅通的贸易和交流渠道,渔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也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归为一类。但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千年里发生了变化,气候变化使海水变浅,除了离海岸最远的水域,捕鲸人也远离了植被茂密的浅水区。长期以来,渔民和牧民一直是他们活动范围内唯一经常相遇的其他种族,但渔民们仍然把牧民定型为滥杀无辜的杀手,因为他们的喙结构和捕鲸人很相似。渔民和牧民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对方的文化,但他们的战争是冷战,冷嘲热讽比血腥冲突要多得多。牧民作为一个整体,只想独处,完全拒绝渔民文化,但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被认为是无聊的,最近出现了一种趋势,年轻的牧民偶尔会在青春期脱离自己的族群,融入渔民文化。尽管渔民们态度高人一等,但他们通常都能接受不同的人,并愿意与他们建立联系,只要他们相应地调整饮食(然而,因为这些“叛逃者”长着大牙齿的脸,对他们的偏见依然存在。)
最近,即使是如此小规模的牧民与渔民融合也开始在两者之间古老的鸿沟上架起最小的桥梁。通过这些年轻、叛逆的新成员加入他们的文化,渔民们了解到,牧民也相信从根本上讲相同的创世故事。一些渔民现在认识到相似之处可能大于差异,甚至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比对手更道德。然而,牧民文化仍然抵制任何外界影响,长者们坚决地与那些背叛他们与敌人交往的少年人断绝关系。因此,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任何团结的迹象似乎都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如果没有双方共同的努力,渔民和牧民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稳定联系。
但现在,无论是渔民还是农民,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两个新的变量几乎同时出现:
第一个因素是渔民声称找到了预言中的造物主的“手”,即两个失踪的造物主精华之一……甚至一些牧民也对这个想法感到好奇。面对那些传递信息的叛徒,那些保守的牧民可能会说:“渔民的脑袋里充满了热水,他们说的话太多了,以至于什么都不说。”但叛徒们已经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坚持这一次他们说的是实话。尽管他们不确定,但风险太大,他们不能不冒险……因为第二个因素出现了,这场古老竞争中的两个派系都必须应对一个新的种族带来的的致命威胁:失踪的捕鲸者突然返回沿海浅滩。自从他们离开后,他们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变化。
好战者Warmonger是捕鲸者中一个极端孤立的分支,他们通过数千年的故意近亲繁殖而形成,以支持新的隐性模式特征和缺乏黄色皮肤色素。他们的语言是所有种族中从起源点开始差异最大的。他们的语言深沉、缓慢、令人难以忘怀,对渔民来说,他们的语言比掘墓人的语言更难懂,而且他们很少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所有捕鲸者都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以免被发现。
他们与其他文化的历史交流仍然构成了好战者宗教的基础,但与其他文化不同的是,好战者不再相信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古代造物主还有其他部分精华。他们相信他们的人民是神的唯一正统后代(太典了),他们认为自己比所有其他生命更加高贵。他们的巨大体型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优势地位,平均比牧民或渔民大 20%,头部和下颚明显更大,适合杀死大型海洋猎物。好战者进化为成群结队地捕猎,协调性极强。自然而然,白日梦者常见的那种松散群体让位于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而牧民或渔民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这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致命威胁,因为这个不断扩张的极端主义团体密谋通过消灭较弱的对手来展示他们对世界的终极权力……吃掉并灭绝其他的种族——这是终极的统治行为(豚特勒是吧)。
好战者是一个具有唯一领导者的统一战线,他们杀戮所有海豚雀,也不区分渔民和牧民。在他们看来,除自己种族之外的所有海豚雀都是红肉。
如今,为了抵抗不断增加的针对其他白日梦者的猎杀行动,牧民本不愿意和渔民联合。他们知道自己人数比渔民多,他们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自卫。但是叛逃者带来了充满诱惑力的条件:如果牧民期待已久的造物主之手真的已经回归并召集他们……那他们就不会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