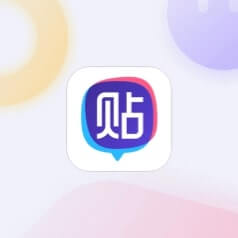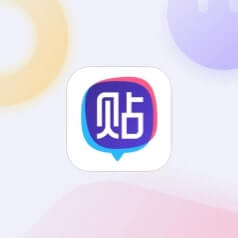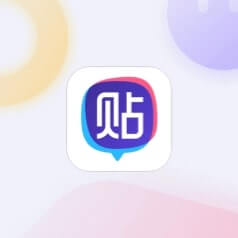暴风雨把我的电力系统切断为辅助系统,只留下足够的能量发出求救信号。我的VAP是盲目的,没有我的信号就无法返回。我再也没有找回它。
暴风越发猛烈,风速超过每小时四百三十公里。果冻状的“海洋”表面荡漾起伏。在暴风雨过去之前,我一直处于黑暗中。幸运的是,事实证明这对我很有利,一个小时后,我看到了达尔文四号上最难忘的景色之一。
先是一阵沉闷的咆哮。幸运的是,我的音响系统完好无损,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低噪音,一开始我以为是雷声。然而,它似乎太连续了,不像是大气,我又一次对我丢失的电脑数据发誓。我的可扩展地震干扰指示器和音频一样,在同一条辅助电源线上运行,它也能正常工作,它突然开始记录有节奏的振动。我把座位转向震源,但发现我的视线被一大块露出地面的岩石挡住了。我对这些地震读数很熟悉,因为我过去对巨大的树背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这些数字表明,这是一种更大的生物。我确信我很快就会遇到来自S. I. 848的著名生物。在我的大部分系统都关闭的情况下,我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工作。
其中包括从我的个人装备中准备好手掌大小的Vidisc旅游相机。我关掉了应急舱的灯,调暗了监视器,然后坐下来等待。“海”是黑暗而光滑的,被风吹动的涟漪偶尔会显示出嵌入微型动物的发光斑块。SDI,现在在背景中不断地哔哔作响,表明我和多年前引发了许多想象的不可思议的野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暴风越发猛烈,风速超过每小时四百三十公里。果冻状的“海洋”表面荡漾起伏。在暴风雨过去之前,我一直处于黑暗中。幸运的是,事实证明这对我很有利,一个小时后,我看到了达尔文四号上最难忘的景色之一。
先是一阵沉闷的咆哮。幸运的是,我的音响系统完好无损,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低噪音,一开始我以为是雷声。然而,它似乎太连续了,不像是大气,我又一次对我丢失的电脑数据发誓。我的可扩展地震干扰指示器和音频一样,在同一条辅助电源线上运行,它也能正常工作,它突然开始记录有节奏的振动。我把座位转向震源,但发现我的视线被一大块露出地面的岩石挡住了。我对这些地震读数很熟悉,因为我过去对巨大的树背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这些数字表明,这是一种更大的生物。我确信我很快就会遇到来自S. I. 848的著名生物。在我的大部分系统都关闭的情况下,我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工作。
其中包括从我的个人装备中准备好手掌大小的Vidisc旅游相机。我关掉了应急舱的灯,调暗了监视器,然后坐下来等待。“海”是黑暗而光滑的,被风吹动的涟漪偶尔会显示出嵌入微型动物的发光斑块。SDI,现在在背景中不断地哔哔作响,表明我和多年前引发了许多想象的不可思议的野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