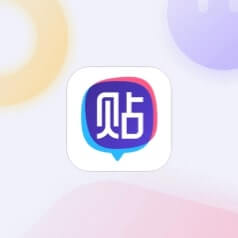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遇到了另外两个山上的居民,大山弹簧翼兽和峭壁跳兽(Crag springer),它们分别在这个生物群落中占据着独立但相似的生态位。前者比它的小表亲大一半,有一个颅顶,在一些标本中,颅顶几乎弯曲到脊椎。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这种巨大的翼冠被用来展示飞行中的优势,经常导致严重的翅膀撕裂——一个几乎总是致命的伤口,因为它在下面的岩石上造成了撞击。
峭壁跳兽没有它的远亲弹簧翼兽的翅膀。它非常敏捷,跳跃的能力让我无法呼吸。我记录了很多次20米以上的鸿沟跳跃,几乎无一受伤。它似乎在不停地寻找食物,选择覆盖在垂直岩石表面的碎石草作为主要食物。就像悬崖水螅一样,碎石草也会释放出自己有气味的孢子,有时其数量足以在山腰上产生一大片阴霾。
我在山里的第一天,快到傍晚的时候,我跟着一群峭壁跳兽进入了一片孢子云,看它们进食。孢子云层一定是触发了一种本能的进食反射,因为兽群开始上下摆动它们的大脑袋。当它们靠近墙壁时,它们继续这样的动作,当它们用角质的面部外壳摩擦石头时,发出响亮的声音。在我的屏幕上用更大的放大镜,我可以看到这些生物实际上是在用它们的进食槽把碎石草剃成长条。早些时候,我对悬崖上的多处磨损痕迹感到奇怪;观察这些进食习惯给了我一个答案。
(峭壁跳兽的背部有互锁的鳞甲。然而,尽管有这样的保护,达尔文四号的年轻且仍然不稳定的赤道山脉频繁的震动所引发的岩石滑坡和雪崩使许多个体失去了生命。)

峭壁跳兽没有它的远亲弹簧翼兽的翅膀。它非常敏捷,跳跃的能力让我无法呼吸。我记录了很多次20米以上的鸿沟跳跃,几乎无一受伤。它似乎在不停地寻找食物,选择覆盖在垂直岩石表面的碎石草作为主要食物。就像悬崖水螅一样,碎石草也会释放出自己有气味的孢子,有时其数量足以在山腰上产生一大片阴霾。
我在山里的第一天,快到傍晚的时候,我跟着一群峭壁跳兽进入了一片孢子云,看它们进食。孢子云层一定是触发了一种本能的进食反射,因为兽群开始上下摆动它们的大脑袋。当它们靠近墙壁时,它们继续这样的动作,当它们用角质的面部外壳摩擦石头时,发出响亮的声音。在我的屏幕上用更大的放大镜,我可以看到这些生物实际上是在用它们的进食槽把碎石草剃成长条。早些时候,我对悬崖上的多处磨损痕迹感到奇怪;观察这些进食习惯给了我一个答案。
(峭壁跳兽的背部有互锁的鳞甲。然而,尽管有这样的保护,达尔文四号的年轻且仍然不稳定的赤道山脉频繁的震动所引发的岩石滑坡和雪崩使许多个体失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