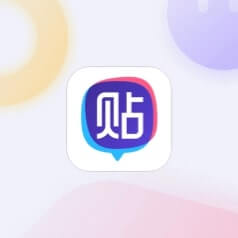
【原创】古风‖权臣大人饶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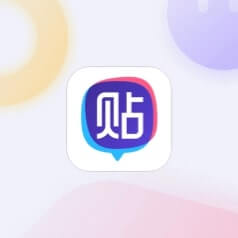
(53.4)解漪见状又将汤壶往二哥怀中送了送,来时路上听阿夙说解栖今日不太好,好不容易熬到母后离开,卸下裹腹时腹中胎儿闹个不停,折腾了他好一会。
“身上的小伤养养倒好,就是脸上的伤颇为严重,若是留疤破相……唉。”解漪说着语气低落下来,她还是后悔今日为何没护着四弟,明明这些事都是可以避免的。
解栖抚了抚对方发顶,语气微弱却有力量:“不必自责,事情已然发生时我们便想办法解决,何况作为姐姐你也第一时间将启星带了回来。”言下之意是解漪已经到做了她力所能及的最好。
“……所以,可查出幕后主使?”
解漪心头一软,搬着凳子向榻上倚着的那人又凑了凑,“我那时一心都在星弟身上,后来便直奔行宫来。中途隐约听说此事与柳昭仪有关,眼下父皇已下旨将她押入诏狱了。”
感受到对方僵硬了须臾,解漪微微诧异:“二哥?”
“所以,是柳昭仪算计启星?”
解栖盖在被中的手不自觉抓起下腹衣料,诏狱这两个字还在脑中回旋。
“二哥认识柳昭仪?”
解漪歪头不解,刚刚二哥神情中少见的闪过一丝慌乱,虽然极快极轻,但她还是敏锐捕捉到了。
解栖别开目光点点头:“入宫给母后请安时见过几次。”
“身上的小伤养养倒好,就是脸上的伤颇为严重,若是留疤破相……唉。”解漪说着语气低落下来,她还是后悔今日为何没护着四弟,明明这些事都是可以避免的。
解栖抚了抚对方发顶,语气微弱却有力量:“不必自责,事情已然发生时我们便想办法解决,何况作为姐姐你也第一时间将启星带了回来。”言下之意是解漪已经到做了她力所能及的最好。
“……所以,可查出幕后主使?”
解漪心头一软,搬着凳子向榻上倚着的那人又凑了凑,“我那时一心都在星弟身上,后来便直奔行宫来。中途隐约听说此事与柳昭仪有关,眼下父皇已下旨将她押入诏狱了。”
感受到对方僵硬了须臾,解漪微微诧异:“二哥?”
“所以,是柳昭仪算计启星?”
解栖盖在被中的手不自觉抓起下腹衣料,诏狱这两个字还在脑中回旋。
“二哥认识柳昭仪?”
解漪歪头不解,刚刚二哥神情中少见的闪过一丝慌乱,虽然极快极轻,但她还是敏锐捕捉到了。
解栖别开目光点点头:“入宫给母后请安时见过几次。”
(54.1)入目是幽不见底的黑。
解栖徘徊了许久,期间也试图找寻出口,只是所处之地除却蚀骨寒冷便余无边凝寂。
冥暗角落中倏忽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他屏吸收敛脚步,凝神聆听起来。只闻那声音愈发嘶哑凄厉,呜咽到最后好似严冬里哭啼的朔风。
喉头控制不住滚动了一下,解栖摇摇头试图驱散眩晕,同时强压下抵在喉管处的心脏。不知为何,眼前的场景让他既熟悉又陌生。
漆黑中悄然冒出丝暗红幽亮,悬起的心猛然跌落,解栖发疯般朝着那个方向狂奔而去。眼前的那条路却像没有尽头,他越是追逐,那抹幽红便越发明亮。
直到最后的最后,他眼睁睁看着那方暗红一点点转为醒目的橙红。
不要——!
脑中全然被这一个念头占据,他拼了命地想阻拦,然而下一瞬,女子凄惨尖厉的哭喊声伴随着滋滋作响的糊焦味充塞在各个感官。
全身血液顷刻充斥在头颅、发顶,解栖双目湿润,终是没能压住一直顶在喉头的反胃之感,俯身撑着膝盖呕了起来。
这一吐,腹中的不适骤然减半,只是腹内始终翻滚地难受,还未等他缓过劲,耳畔又森森传来一女声:
“解云柯,你可知烙刑是何滋味?”
解栖徘徊了许久,期间也试图找寻出口,只是所处之地除却蚀骨寒冷便余无边凝寂。
冥暗角落中倏忽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他屏吸收敛脚步,凝神聆听起来。只闻那声音愈发嘶哑凄厉,呜咽到最后好似严冬里哭啼的朔风。
喉头控制不住滚动了一下,解栖摇摇头试图驱散眩晕,同时强压下抵在喉管处的心脏。不知为何,眼前的场景让他既熟悉又陌生。
漆黑中悄然冒出丝暗红幽亮,悬起的心猛然跌落,解栖发疯般朝着那个方向狂奔而去。眼前的那条路却像没有尽头,他越是追逐,那抹幽红便越发明亮。
直到最后的最后,他眼睁睁看着那方暗红一点点转为醒目的橙红。
不要——!
脑中全然被这一个念头占据,他拼了命地想阻拦,然而下一瞬,女子凄惨尖厉的哭喊声伴随着滋滋作响的糊焦味充塞在各个感官。
全身血液顷刻充斥在头颅、发顶,解栖双目湿润,终是没能压住一直顶在喉头的反胃之感,俯身撑着膝盖呕了起来。
这一吐,腹中的不适骤然减半,只是腹内始终翻滚地难受,还未等他缓过劲,耳畔又森森传来一女声:
“解云柯,你可知烙刑是何滋味?”
(54.2)解栖撑在膝头的手一滞,应声抬起头,一双通红的眼正凝睇着自己。女子长发散乱,双目似要滴出鲜血,眼神却澄澈至极,仿佛是在问询今日午膳吃什么。
心脏猛然紧缩如锥刺入,解栖捂住心口用尽全身力气动了动唇瓣,开口后几度语气颤抖:“他们……对你…用刑了?”
“殿下?殿下!——殿下醒醒!”
光影交叠几番转幻,女子满盛恨意的眼神逐渐化为明显担忧,解栖眨眨眼,挣扎着撑起身子剧烈咳喘起来,待看清眼前人后眸光黯淡,几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阿夙……咳咳…可是时辰到了?”
阿夙见状忙替对方抚着背:“是,您和邝大人前几日约好的,只是今日……”说着又将目光转向解栖身前,眉头深深绞在了一起,“殿下身体抱恙,要不还是改日吧?”
“无碍,只是…咳……近日有些多梦。”
回忆起方才的梦境,解栖只觉背后还冒着冷气,心脏剧烈跳个不停,连带着腹中亦开始若有若无的抽痛起来。
他闭目缓了缓,终是囫囵在侧腹打圈安抚着:“同辉现在到何处了?先替我梳洗更衣吧。”
“邝大人此时应该已到山下。”阿夙心细如发,自然注意到了对方的动作,一时也没了主意。
彼时听到解栖的呼喊声后他便急忙闯进来,榻上那人又是面色发白又是冷汗频频,地上呕出的秽物还发着苦味。好不容易将人从梦魇里叫醒,醒来第一件事竟是记挂着与邝大人议事。
阿夙犹豫盯着对方身前的隆起,小声试探道:“殿下……是梦到晏姑娘了吗?”
从他进来时算起,殿下共唤了九声那个人的名字。
心脏猛然紧缩如锥刺入,解栖捂住心口用尽全身力气动了动唇瓣,开口后几度语气颤抖:“他们……对你…用刑了?”
“殿下?殿下!——殿下醒醒!”
光影交叠几番转幻,女子满盛恨意的眼神逐渐化为明显担忧,解栖眨眨眼,挣扎着撑起身子剧烈咳喘起来,待看清眼前人后眸光黯淡,几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阿夙……咳咳…可是时辰到了?”
阿夙见状忙替对方抚着背:“是,您和邝大人前几日约好的,只是今日……”说着又将目光转向解栖身前,眉头深深绞在了一起,“殿下身体抱恙,要不还是改日吧?”
“无碍,只是…咳……近日有些多梦。”
回忆起方才的梦境,解栖只觉背后还冒着冷气,心脏剧烈跳个不停,连带着腹中亦开始若有若无的抽痛起来。
他闭目缓了缓,终是囫囵在侧腹打圈安抚着:“同辉现在到何处了?先替我梳洗更衣吧。”
“邝大人此时应该已到山下。”阿夙心细如发,自然注意到了对方的动作,一时也没了主意。
彼时听到解栖的呼喊声后他便急忙闯进来,榻上那人又是面色发白又是冷汗频频,地上呕出的秽物还发着苦味。好不容易将人从梦魇里叫醒,醒来第一件事竟是记挂着与邝大人议事。
阿夙犹豫盯着对方身前的隆起,小声试探道:“殿下……是梦到晏姑娘了吗?”
从他进来时算起,殿下共唤了九声那个人的名字。
(54.3)腹中律动复起,解栖紧了紧指尖,侧腹衣料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又添了数道皱痕,掌心沁出的湿黏亦紧紧嵌入其中。
在听到阿夙的话后,他先是沉默了须臾。再开口时声音已平静如潭水听不出任何情绪,只淡淡道:“梦到,又如何?”
何况只是梦而已。
解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纵使他此刻忧心如捣,或是这些年念着她魂劳梦断。他此生与她也再无可能。
寥天爽气,霜枫点染。冬初的冷气随北风匀到了京畿南端的浵州。端坐在窗前专注提笔书写着什么的男子身姿颀秀,手中的黑檀笔杆也不停歇,便是偶尔凝眉沉思一番后又接着笔翰如流,除了窗外女子的嬉笑声偶尔会让他分神片刻。
书本哗哗翻过数页,本想找寻信中所用支撑,谁知一深红叶片竟出乎意料地掉落出来。那人怔愣一瞬拾起红叶,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岑修云』,“云”字后还紧跟着一爱心图样的线条。
指尖轻触上干涸的墨迹,叶脉的纹路同时摩挲着指腹。岑修云几乎已想象到对方在写这片红叶时是什么表情,他会心一笑,小心将那枚书签收藏起来。
在听到阿夙的话后,他先是沉默了须臾。再开口时声音已平静如潭水听不出任何情绪,只淡淡道:“梦到,又如何?”
何况只是梦而已。
解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纵使他此刻忧心如捣,或是这些年念着她魂劳梦断。他此生与她也再无可能。
寥天爽气,霜枫点染。冬初的冷气随北风匀到了京畿南端的浵州。端坐在窗前专注提笔书写着什么的男子身姿颀秀,手中的黑檀笔杆也不停歇,便是偶尔凝眉沉思一番后又接着笔翰如流,除了窗外女子的嬉笑声偶尔会让他分神片刻。
书本哗哗翻过数页,本想找寻信中所用支撑,谁知一深红叶片竟出乎意料地掉落出来。那人怔愣一瞬拾起红叶,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岑修云』,“云”字后还紧跟着一爱心图样的线条。
指尖轻触上干涸的墨迹,叶脉的纹路同时摩挲着指腹。岑修云几乎已想象到对方在写这片红叶时是什么表情,他会心一笑,小心将那枚书签收藏起来。
(54.4)
“修云,写好了没?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窗边忽的斜斜探出一颗脑袋,女子发间垂下的流苏晃动,珠玉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
岑修云顿时心情大好,拿起信封轻刮了一下对方的鼻尖笑道:“写好了,随时出发。”
“咦?你不生气了?”姜乐颜虽是歪着脑袋,可全程都关注着岑修云的表情,见他嘴角上扬明显还有些意外。
对方无奈摇摇头,一脸看傻瓜的表情:“哪有那么多气可生?我在乐乐眼里这样小气么?”
“没有没有,修云最大度了。我不是……怕你吃醋嘛……”姜乐颜越说越小声,说到最后只有两片唇瓣在动,眼睛却始终直勾勾盯着岑修云看,生怕错过他任何一个表情。
岑修云别开目光,侧过姜乐颜偷笑道:“为何吃醋?吃谁的醋?”
“元问玉呀,你刚刚来书房面无表情还一脸严肃,可不就是生气了吗?”
垂在身旁的手臂突然被对方紧紧抱住,岑修云长舒口气叹道:“我那是忽然想到信中要补充的内容,故走得急了些。至于元问玉——”
这恰到好处的停顿又让姜乐颜心里一紧。从前这厮就跟元问玉不对付,还暗搓搓算计人家,现在要他跟元问玉当面谈话……
嘶——姜乐颜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还是想象不出来。
“乐乐,你喜欢他么?”
岑修云的声音如平地一声雷,轰地在姜乐颜耳畔炸开,方才还在神游的她瞬间炸了毛高声道:“怎么可能?”
姜乐颜除了震惊还是震惊,恨不得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和元问玉撇清关系。
毕竟她可记得某人之前因为元问玉跟自己吵架,大着肚子被气得够呛,自己是又气又心疼。那件事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妥协不了了之,再后来两人出逃,在封县养身体,此事也就一直没有说开。
岑修云没想到姜乐颜的反应这么大,笑着抬起被对方紧抱的手臂示意道:“所以,我又为何要吃醋?”
“修云,写好了没?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窗边忽的斜斜探出一颗脑袋,女子发间垂下的流苏晃动,珠玉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
岑修云顿时心情大好,拿起信封轻刮了一下对方的鼻尖笑道:“写好了,随时出发。”
“咦?你不生气了?”姜乐颜虽是歪着脑袋,可全程都关注着岑修云的表情,见他嘴角上扬明显还有些意外。
对方无奈摇摇头,一脸看傻瓜的表情:“哪有那么多气可生?我在乐乐眼里这样小气么?”
“没有没有,修云最大度了。我不是……怕你吃醋嘛……”姜乐颜越说越小声,说到最后只有两片唇瓣在动,眼睛却始终直勾勾盯着岑修云看,生怕错过他任何一个表情。
岑修云别开目光,侧过姜乐颜偷笑道:“为何吃醋?吃谁的醋?”
“元问玉呀,你刚刚来书房面无表情还一脸严肃,可不就是生气了吗?”
垂在身旁的手臂突然被对方紧紧抱住,岑修云长舒口气叹道:“我那是忽然想到信中要补充的内容,故走得急了些。至于元问玉——”
这恰到好处的停顿又让姜乐颜心里一紧。从前这厮就跟元问玉不对付,还暗搓搓算计人家,现在要他跟元问玉当面谈话……
嘶——姜乐颜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还是想象不出来。
“乐乐,你喜欢他么?”
岑修云的声音如平地一声雷,轰地在姜乐颜耳畔炸开,方才还在神游的她瞬间炸了毛高声道:“怎么可能?”
姜乐颜除了震惊还是震惊,恨不得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和元问玉撇清关系。
毕竟她可记得某人之前因为元问玉跟自己吵架,大着肚子被气得够呛,自己是又气又心疼。那件事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妥协不了了之,再后来两人出逃,在封县养身体,此事也就一直没有说开。
岑修云没想到姜乐颜的反应这么大,笑着抬起被对方紧抱的手臂示意道:“所以,我又为何要吃醋?”
(55.1)
“那你之前还……”打量着眼前人确实不像生气的样子,姜乐颜嗔怪地甩开那人衣袖,又被对方自然而然反握住手腕。
岑修云的手指凉凉的,声音却格外柔和:“我与他先前有些恩怨,但与你无关。且并非是我嫉妒,只是怕你对他动了恻隐之心。”
他这番言辞说得恳切,姜乐颜尚有些懵然,又听他顿了顿补充道:“如同对我那般的……恻隐之心。”
什么意思?自己是同情元问玉不假,但对岑修云除了同情更多的是其他情感,所以他这是又误会了?
两人的心跳经由相贴的肌肤传导,姜乐颜轻轻扭动手腕,不确定地试探道:“所以,你是怕我像喜欢你一样喜欢他?”
“嗯。”
被戳中要害,他倒是坦诚。姜乐颜悄悄抿了抿唇,回看那人时发觉他的目光游移到了自己胸口,眉心亦微微蹙起:“可你那日,真叫我怕了。也不曾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明确你的心意。”
每每想起生产那夜她为自己挡箭时岑修云都觉背后发凉,他总觉得那次自己差点就要失去她了。
“那也算因祸得福了不是?”
姜乐颜的心软成一片,半个身子探进窗内,张开双臂将对方抱了个满满当当,后又将脸埋入岑修云颈边,用前所未有的认真语气承诺着:“以后不会再留你一个人胡思乱想了,我也会……尽我所能填补你的不安。”
感到怀中身躯僵硬了片刻,姜乐颜侧过脸飞快地吻了吻对方耳畔,扬起脸找寻他的眼睛:“听好了哦,我只说一次。”
“姜乐颜满心满眼都是岑修云,也只有岑修云,再容不下其他。”
窗外的风有那么一刻好像真的静止下来。很多年后,当岑修云回忆起那天时,脑中浮现的皆是她彼时坚定的眼神及誓言般的话语。
他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觉喉头哽得厉害,眼眶控制不住地发酸。短短二十载人生如萍飘蓬转,他在无数个日夜中被迫习惯着这种孤独。
眼前人的出现好比从天而降的一方栖岸,温暖、安定的同时又向他毫无保留地敞开怀抱。曾经他时常犹豫自己配不配得上,常常患得患失,现如今她亲口告诉自己,她的心只属于自己。
她在说也在这样做着,尽管自己一次又一次试探,偶尔还会因不当的试探伤害到她,可她却始终满怀爱意义无反顾地奔向自己。这一切的一切……叫他如何不动容?
相顾无言,惟四目相对两心相栖。他张开双臂将眼前人紧紧拥入怀中——她是他求生的浮木。
“修云此心亦同。”
“那你之前还……”打量着眼前人确实不像生气的样子,姜乐颜嗔怪地甩开那人衣袖,又被对方自然而然反握住手腕。
岑修云的手指凉凉的,声音却格外柔和:“我与他先前有些恩怨,但与你无关。且并非是我嫉妒,只是怕你对他动了恻隐之心。”
他这番言辞说得恳切,姜乐颜尚有些懵然,又听他顿了顿补充道:“如同对我那般的……恻隐之心。”
什么意思?自己是同情元问玉不假,但对岑修云除了同情更多的是其他情感,所以他这是又误会了?
两人的心跳经由相贴的肌肤传导,姜乐颜轻轻扭动手腕,不确定地试探道:“所以,你是怕我像喜欢你一样喜欢他?”
“嗯。”
被戳中要害,他倒是坦诚。姜乐颜悄悄抿了抿唇,回看那人时发觉他的目光游移到了自己胸口,眉心亦微微蹙起:“可你那日,真叫我怕了。也不曾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明确你的心意。”
每每想起生产那夜她为自己挡箭时岑修云都觉背后发凉,他总觉得那次自己差点就要失去她了。
“那也算因祸得福了不是?”
姜乐颜的心软成一片,半个身子探进窗内,张开双臂将对方抱了个满满当当,后又将脸埋入岑修云颈边,用前所未有的认真语气承诺着:“以后不会再留你一个人胡思乱想了,我也会……尽我所能填补你的不安。”
感到怀中身躯僵硬了片刻,姜乐颜侧过脸飞快地吻了吻对方耳畔,扬起脸找寻他的眼睛:“听好了哦,我只说一次。”
“姜乐颜满心满眼都是岑修云,也只有岑修云,再容不下其他。”
窗外的风有那么一刻好像真的静止下来。很多年后,当岑修云回忆起那天时,脑中浮现的皆是她彼时坚定的眼神及誓言般的话语。
他不知该如何回应,只觉喉头哽得厉害,眼眶控制不住地发酸。短短二十载人生如萍飘蓬转,他在无数个日夜中被迫习惯着这种孤独。
眼前人的出现好比从天而降的一方栖岸,温暖、安定的同时又向他毫无保留地敞开怀抱。曾经他时常犹豫自己配不配得上,常常患得患失,现如今她亲口告诉自己,她的心只属于自己。
她在说也在这样做着,尽管自己一次又一次试探,偶尔还会因不当的试探伤害到她,可她却始终满怀爱意义无反顾地奔向自己。这一切的一切……叫他如何不动容?
相顾无言,惟四目相对两心相栖。他张开双臂将眼前人紧紧拥入怀中——她是他求生的浮木。
“修云此心亦同。”
(55.2)
牢狱走廊中隐约响起脚步声,干草堆上的人影警觉地动了动,随着那串脚步声越来越近,柳氏起身拍了拍骑装上的尘土。两天时间,也不知刑部那帮废物查得怎么样了。
“传陛下口谕——”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柳氏如言恭敬跪下,极标准地行着后妃礼,目光始终注视地面。领头那人是贴身侍奉皇帝的内务总管,前朝后宫皆尊称一声陆中官。
“昭仪柳氏与皇四子受伤一案无干,务必尽快开释,将人护送回宫,切勿耽延。钦此。”
“叩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眼看着脚下平日里柔心弱骨的美人在听闻旨意后战战兢兢又行了三次大礼,陆中官满意地笑了笑,在对方施完礼后指挥侍从将人扶起。
“柳昭仪终于守得云开月明,回去后好好侍奉陛下才是。”
“多谢中官提点,妾能多问一句幕后主使可查出么?”
只见陆中官闻言一脸讳莫如深,柳氏亦识趣地闭了口。不管是谁背了这口黑锅,总之这锅现在是甩出去了。
再次回到宫苑已是傍晚,刚踏进宫门侍女竹萌就小跑着迎了上来。
“主子您可算回来了,奴婢想您想得好苦,诏狱那帮家伙没有欺负您吧?”小丫头边哭边胡乱拿柚子叶朝自家主人身上拍打,边拍还边嚷嚷着些去晦气之类的话。
柳氏不动声色打量了一番四周,见并无异常才稍稍放下心来:“我没事,别担心了。有陛下在,而且并无定论,诏狱的人不敢造次。”
“那,那奴婢去烧水伺候您沐浴更衣。”竹萌抖了抖自家主人衣袍扬起的灰,一张小脸皱得像包子,说话之余又眨了眨眼。柳氏瞬间心领神会,随她一同向屋内走去。
牢狱走廊中隐约响起脚步声,干草堆上的人影警觉地动了动,随着那串脚步声越来越近,柳氏起身拍了拍骑装上的尘土。两天时间,也不知刑部那帮废物查得怎么样了。
“传陛下口谕——”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柳氏如言恭敬跪下,极标准地行着后妃礼,目光始终注视地面。领头那人是贴身侍奉皇帝的内务总管,前朝后宫皆尊称一声陆中官。
“昭仪柳氏与皇四子受伤一案无干,务必尽快开释,将人护送回宫,切勿耽延。钦此。”
“叩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眼看着脚下平日里柔心弱骨的美人在听闻旨意后战战兢兢又行了三次大礼,陆中官满意地笑了笑,在对方施完礼后指挥侍从将人扶起。
“柳昭仪终于守得云开月明,回去后好好侍奉陛下才是。”
“多谢中官提点,妾能多问一句幕后主使可查出么?”
只见陆中官闻言一脸讳莫如深,柳氏亦识趣地闭了口。不管是谁背了这口黑锅,总之这锅现在是甩出去了。
再次回到宫苑已是傍晚,刚踏进宫门侍女竹萌就小跑着迎了上来。
“主子您可算回来了,奴婢想您想得好苦,诏狱那帮家伙没有欺负您吧?”小丫头边哭边胡乱拿柚子叶朝自家主人身上拍打,边拍还边嚷嚷着些去晦气之类的话。
柳氏不动声色打量了一番四周,见并无异常才稍稍放下心来:“我没事,别担心了。有陛下在,而且并无定论,诏狱的人不敢造次。”
“那,那奴婢去烧水伺候您沐浴更衣。”竹萌抖了抖自家主人衣袍扬起的灰,一张小脸皱得像包子,说话之余又眨了眨眼。柳氏瞬间心领神会,随她一同向屋内走去。
(55.3)
灯火幽微,空白的纸张在火焰中逐渐显现出一行字迹。被快速浏览后,那片纸张又以极快的速度化为灰烬。
“除此之外可还有其他消息?”柳氏吹了吹桌上残存的余烬,凝眉远眺不知在想什么。
“没了,邝公子还叮嘱您保护好自己,这个时期万不可大意,四皇子一案则已有确凿证据指向赵美人。”
柳氏沉默片刻,目光始终望着远处,良久后怔怔道:“只是可惜了美人,年纪轻轻便香消玉殒。”
封县地处浵州西,相比一州府衙格外偏僻,即便是在县城中心,街上也只是零落走过几个行人,客栈商铺等亦是门可罗雀。
“宁知州又给你寄信了么?这样一直找借口拖着也不是办法呀,我们什么时候回去?”马车内,姜乐颜盯着眼前街景忽觉有些惆怅。
刚出逃时自己与修云还有季大夫一干人都觉得宁知州有很大问题,毕竟一州府衙怎能轻易让敌人单刀直入,定是有人授意且大开门户。故为了安全一行人在封县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听说宁鹤慈得知原委后即刻派人调查,还数次写信请岑修云回去,只是皆被他以修养身体为由暂时搁置了。即便如此,宁鹤慈也非常尊重几人,派人又是请大夫又是赠送药物。
姜乐颜觉得她这样做也可以理解,毕竟下属在自己管辖内出了事,肯定会想办法息事宁人,只是岑修云还是迟迟不愿回去,又或许宁鹤慈真的不是什么好人?之前对他们的好也全是装出来的?
唉,好麻烦,弯弯绕绕想得人脑壳痛。
“先晾她一晾,而且,还没带你去封县走走。”不知她想到什么了,方才还高高兴兴的,突然就低落下来,岑修云捏捏姜乐颜的脸颊,食指与中指撑在她唇角试图挤出个笑容。
“小葡萄的名字想好了吗?”
“不是你来起我来挑嘛。”姜乐颜抓住对方的手指作势要咬,那人也只是笑着盯着自己,她顿觉无聊,又玩起对方的手指来。
见姜乐颜被成功转移注意力,岑修云垂目回忆了一番,其实他这几日倒是真想到了个名字,灵感来源于那枚书中掉落的红叶。
“叫『霜序』如何?。”他一边说一边在姜乐颜手心书写。
霜序?姜乐颜琢磨了一下,好听是好听,但是霍扶姜已经一个“冬”娘了,听上去总感觉凉嗖嗖的。“会不会有些太冷了?嗯……和煦的煦怎么样?”这个煦听起来就比较热乎。
“岑煦?景,光之人,煦若射。煦字倒也不错,只是单字易重名,不如就叫『煦柔』吧?”
“柔和的柔吗?煦柔……岑煦柔。”姜乐颜反复念了几遍笑道:“这个比霜序听起来温暖多了,就这个吧。”
“嘿嘿,我们小葡萄有名字啦。”
灯火幽微,空白的纸张在火焰中逐渐显现出一行字迹。被快速浏览后,那片纸张又以极快的速度化为灰烬。
“除此之外可还有其他消息?”柳氏吹了吹桌上残存的余烬,凝眉远眺不知在想什么。
“没了,邝公子还叮嘱您保护好自己,这个时期万不可大意,四皇子一案则已有确凿证据指向赵美人。”
柳氏沉默片刻,目光始终望着远处,良久后怔怔道:“只是可惜了美人,年纪轻轻便香消玉殒。”
封县地处浵州西,相比一州府衙格外偏僻,即便是在县城中心,街上也只是零落走过几个行人,客栈商铺等亦是门可罗雀。
“宁知州又给你寄信了么?这样一直找借口拖着也不是办法呀,我们什么时候回去?”马车内,姜乐颜盯着眼前街景忽觉有些惆怅。
刚出逃时自己与修云还有季大夫一干人都觉得宁知州有很大问题,毕竟一州府衙怎能轻易让敌人单刀直入,定是有人授意且大开门户。故为了安全一行人在封县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听说宁鹤慈得知原委后即刻派人调查,还数次写信请岑修云回去,只是皆被他以修养身体为由暂时搁置了。即便如此,宁鹤慈也非常尊重几人,派人又是请大夫又是赠送药物。
姜乐颜觉得她这样做也可以理解,毕竟下属在自己管辖内出了事,肯定会想办法息事宁人,只是岑修云还是迟迟不愿回去,又或许宁鹤慈真的不是什么好人?之前对他们的好也全是装出来的?
唉,好麻烦,弯弯绕绕想得人脑壳痛。
“先晾她一晾,而且,还没带你去封县走走。”不知她想到什么了,方才还高高兴兴的,突然就低落下来,岑修云捏捏姜乐颜的脸颊,食指与中指撑在她唇角试图挤出个笑容。
“小葡萄的名字想好了吗?”
“不是你来起我来挑嘛。”姜乐颜抓住对方的手指作势要咬,那人也只是笑着盯着自己,她顿觉无聊,又玩起对方的手指来。
见姜乐颜被成功转移注意力,岑修云垂目回忆了一番,其实他这几日倒是真想到了个名字,灵感来源于那枚书中掉落的红叶。
“叫『霜序』如何?。”他一边说一边在姜乐颜手心书写。
霜序?姜乐颜琢磨了一下,好听是好听,但是霍扶姜已经一个“冬”娘了,听上去总感觉凉嗖嗖的。“会不会有些太冷了?嗯……和煦的煦怎么样?”这个煦听起来就比较热乎。
“岑煦?景,光之人,煦若射。煦字倒也不错,只是单字易重名,不如就叫『煦柔』吧?”
“柔和的柔吗?煦柔……岑煦柔。”姜乐颜反复念了几遍笑道:“这个比霜序听起来温暖多了,就这个吧。”
“嘿嘿,我们小葡萄有名字啦。”
(56.1)未几,两人进入客栈,元问玉早已等候多时。眼前一个是霍扶姜的旧情人,一个是霍扶姜的冤种老公。姜乐颜在进门前就已经开始脚趾扣地替人尴尬。
为免尴尬,她还是选择主动出击,故率先寒暄起来:“问玉,好久不见啊。”
元问玉先是一怔,盯着姜乐颜出神了片刻后点头示意二人入座。
岑修云亦微微颔首,随姜乐颜一同坐下。许久未见,元问玉倒是变了许多。若说从前的他还算有几分跋扈,而今却全然只剩温顺,无端令人唏嘘。
“宁知州的意思应该与寄给你们的信里差不多,说千道万,包括让我来劝说都是希望你们能尽快回去。”元问玉虽是注视着面前两人,目光却忍不住虚焦到两人身后,他还是有些不敢看。
昔日的爱人与情敌并肩相伴,自己此刻怕是活脱脱一个小丑吧?
“今日与元公子不只是商议此事,我夫妻二人还另有事相求。”岑修云自然看出了元问玉的失意,说话时又刻意压重『夫妻』二字,果然见对方神色愈发怅惘。
一旁摸鱼划水的姜乐颜顿觉不妙,疯狂眨眼示意着身旁人,谁知这屑男人扬了扬眉还一脸无谓。
好嘛,还记着仇呢。
“是这样的,问玉。”姜乐颜清清嗓语气认真道:“之前在浵州衙署遇刺,修云和我都受了些伤,坦白说……我们现在不是很信任宁知州,所以想向你打听打听我们离开后浵州署有哪些动作。”
元问玉是霍扶姜名义上的好友,先前姜乐颜也因他的事求助过宁鹤慈,所以在宁鹤慈看来,元问玉是霍扶姜身边的人。故岑修云在信中提出让元问玉赴封县当说客,其实意在借元问玉试探宁鹤慈的态度。
若她百般阻拦则说明她与那些刺客之间有隐情,反之则暂时可以相信。
“我在的乐坊距离衙署有段路程,所以当时是第二天才听说前天夜里走水的事……”元问玉眼眸低垂,仔细回忆起数日前。
对面姑娘安安静静地听自己娓娓道来,带着求知的一双眼始终注视着自己,时不时还点头回应着。元问玉有一瞬恍惚回到了从前,那时只有她和自己两人,她也是这么安安静静地听自己说话。
恍惚了许久,姑娘的眼神忽然转向她身旁那人,元问玉这才发觉自己失神,干咳两声接着叙说起来,只是此后她的眼神再不曾在自己身上停留。
……
“谢谢问玉,路上小心啊~”姜乐颜大力挥舞着手臂告别,元问玉能来她真的很感激,自己与修云一干人此举意在赌宁鹤慈的为人。若是赌输了,元问玉大概率会遭遇不测,可他还是来了。
为免尴尬,她还是选择主动出击,故率先寒暄起来:“问玉,好久不见啊。”
元问玉先是一怔,盯着姜乐颜出神了片刻后点头示意二人入座。
岑修云亦微微颔首,随姜乐颜一同坐下。许久未见,元问玉倒是变了许多。若说从前的他还算有几分跋扈,而今却全然只剩温顺,无端令人唏嘘。
“宁知州的意思应该与寄给你们的信里差不多,说千道万,包括让我来劝说都是希望你们能尽快回去。”元问玉虽是注视着面前两人,目光却忍不住虚焦到两人身后,他还是有些不敢看。
昔日的爱人与情敌并肩相伴,自己此刻怕是活脱脱一个小丑吧?
“今日与元公子不只是商议此事,我夫妻二人还另有事相求。”岑修云自然看出了元问玉的失意,说话时又刻意压重『夫妻』二字,果然见对方神色愈发怅惘。
一旁摸鱼划水的姜乐颜顿觉不妙,疯狂眨眼示意着身旁人,谁知这屑男人扬了扬眉还一脸无谓。
好嘛,还记着仇呢。
“是这样的,问玉。”姜乐颜清清嗓语气认真道:“之前在浵州衙署遇刺,修云和我都受了些伤,坦白说……我们现在不是很信任宁知州,所以想向你打听打听我们离开后浵州署有哪些动作。”
元问玉是霍扶姜名义上的好友,先前姜乐颜也因他的事求助过宁鹤慈,所以在宁鹤慈看来,元问玉是霍扶姜身边的人。故岑修云在信中提出让元问玉赴封县当说客,其实意在借元问玉试探宁鹤慈的态度。
若她百般阻拦则说明她与那些刺客之间有隐情,反之则暂时可以相信。
“我在的乐坊距离衙署有段路程,所以当时是第二天才听说前天夜里走水的事……”元问玉眼眸低垂,仔细回忆起数日前。
对面姑娘安安静静地听自己娓娓道来,带着求知的一双眼始终注视着自己,时不时还点头回应着。元问玉有一瞬恍惚回到了从前,那时只有她和自己两人,她也是这么安安静静地听自己说话。
恍惚了许久,姑娘的眼神忽然转向她身旁那人,元问玉这才发觉自己失神,干咳两声接着叙说起来,只是此后她的眼神再不曾在自己身上停留。
……
“谢谢问玉,路上小心啊~”姜乐颜大力挥舞着手臂告别,元问玉能来她真的很感激,自己与修云一干人此举意在赌宁鹤慈的为人。若是赌输了,元问玉大概率会遭遇不测,可他还是来了。
(56.2)只是自己终究不是他的冬娘,能给他的也只有亏欠了。
“等等——”马车上向姜乐颜招手的元问玉突然想起什么,忙唤车夫停下后匆匆奔向两人。姜乐颜有些不明所以,和身旁的岑修云面面相觑。
“冬娘——下月是你的生辰,这个我准备了很久,还望你……不要鄙弃。”元问玉跑得有些急,轻喘着气从怀中掏出一物托在掌心。
不远处的岑修云眉头微动,却还是立在原地等待。姜乐颜尴尬地站在元问玉面前,也不知这礼物该不该收。
而且……这生日过得太突然了吧?!
见面前人迟迟不动,元问玉喉头一涩,手指微动正要收回——
“欸?很漂亮的长命锁呀,谢谢问玉,我很喜欢。”姜乐颜适时拿起那枚璀璨的平安锁,下坠着的三颗铃铛因微风响动,那人释然的声音也随之拂过耳畔:
“愿冬娘福康绵绵,长乐无疆。”
姜乐颜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回望着元问玉扬声应道:“那也祝问玉开心快乐,一生顺遂!”
会君难,别君易。元问玉再次登上马车,这次并没有掀开轿帘。只余吱呀的木轮一路踏着斜阳向城外缓缓离去。
“还看呢?人都没影了。”
视线骤然被一只大掌全然覆住,姜乐颜顺势靠在来人身上,还不待未一秒又忽的惊起,忙与那人拉开距离,一脸担忧地盯着对方的小腹。
“还疼吗?”光顾着和元问玉告别,差点忘了身边还有个柔弱不能自理的夫君。刚刚在客栈时见他捂着小腹,姜乐颜还悄悄替他暖了暖,也是那时起她的心思就从元问玉身上全跑到眼前人这里了。
眼看着姜乐颜极其自然地将手探到自己身前,岑修云颇为不自在,瞥了瞥一旁难为情道:“我们……还在街上。”
姜乐颜回过神扯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连拉带扯地推搡着岑修云上了马车。
“是没按时吃药?还是最近太累了?”搓热双手,姜乐颜熟练地将掌心贴在对方下腹,隔着衣料依稀能摸到那处不再柔软,她掌根微动,在那处轻轻按揉着。
“没事,最近已经没有再出血了。”岑修云伸臂将人揽入怀中,身体不自觉向对方靠了靠。
“可别人哪有像这样都快出月子了还总疼的……”姜乐颜本以为生完孩子就没事了,谁知光是让自己撞见他肚子疼就有好几次,更别提自己看不见的时候。
他人岑修云的确不知,关于自己的话……他回忆了一下得出结论:“其实疼倒是其次,就是总觉得腹中冰凉。”
确切地来说就像是下腹破了个口子,且未被缝合,每每发作起来就如同冷风直直往里钻。
姜乐颜按揉对方小腹的手未停,长出口气颇为遗憾:“唉,要是有暖贴就好了。”
岑修云眉头一挑:“何为暖、贴?”
“等等——”马车上向姜乐颜招手的元问玉突然想起什么,忙唤车夫停下后匆匆奔向两人。姜乐颜有些不明所以,和身旁的岑修云面面相觑。
“冬娘——下月是你的生辰,这个我准备了很久,还望你……不要鄙弃。”元问玉跑得有些急,轻喘着气从怀中掏出一物托在掌心。
不远处的岑修云眉头微动,却还是立在原地等待。姜乐颜尴尬地站在元问玉面前,也不知这礼物该不该收。
而且……这生日过得太突然了吧?!
见面前人迟迟不动,元问玉喉头一涩,手指微动正要收回——
“欸?很漂亮的长命锁呀,谢谢问玉,我很喜欢。”姜乐颜适时拿起那枚璀璨的平安锁,下坠着的三颗铃铛因微风响动,那人释然的声音也随之拂过耳畔:
“愿冬娘福康绵绵,长乐无疆。”
姜乐颜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回望着元问玉扬声应道:“那也祝问玉开心快乐,一生顺遂!”
会君难,别君易。元问玉再次登上马车,这次并没有掀开轿帘。只余吱呀的木轮一路踏着斜阳向城外缓缓离去。
“还看呢?人都没影了。”
视线骤然被一只大掌全然覆住,姜乐颜顺势靠在来人身上,还不待未一秒又忽的惊起,忙与那人拉开距离,一脸担忧地盯着对方的小腹。
“还疼吗?”光顾着和元问玉告别,差点忘了身边还有个柔弱不能自理的夫君。刚刚在客栈时见他捂着小腹,姜乐颜还悄悄替他暖了暖,也是那时起她的心思就从元问玉身上全跑到眼前人这里了。
眼看着姜乐颜极其自然地将手探到自己身前,岑修云颇为不自在,瞥了瞥一旁难为情道:“我们……还在街上。”
姜乐颜回过神扯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连拉带扯地推搡着岑修云上了马车。
“是没按时吃药?还是最近太累了?”搓热双手,姜乐颜熟练地将掌心贴在对方下腹,隔着衣料依稀能摸到那处不再柔软,她掌根微动,在那处轻轻按揉着。
“没事,最近已经没有再出血了。”岑修云伸臂将人揽入怀中,身体不自觉向对方靠了靠。
“可别人哪有像这样都快出月子了还总疼的……”姜乐颜本以为生完孩子就没事了,谁知光是让自己撞见他肚子疼就有好几次,更别提自己看不见的时候。
他人岑修云的确不知,关于自己的话……他回忆了一下得出结论:“其实疼倒是其次,就是总觉得腹中冰凉。”
确切地来说就像是下腹破了个口子,且未被缝合,每每发作起来就如同冷风直直往里钻。
姜乐颜按揉对方小腹的手未停,长出口气颇为遗憾:“唉,要是有暖贴就好了。”
岑修云眉头一挑:“何为暖、贴?”
(56.3)
只见对方摊开掌心手舞足蹈比划着大小:“就是一个会自己发热的东西。嗯……大概这么大,薄薄的小小的,贴在衣服里能暖和一晚上呢。”
“听起来似乎对我颇为有用?”
“是啊……”何止是有用,简直比这里的汤壶好用一百倍!来这里之前姜乐颜还没有体会到什么叫『独在异乡为异客』,现在的她无比渴望躺在冬天家里的暖气房,但现实是除了暖炉就是汤壶,出趟门也没什么取暖工具,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每次见她说起家乡的东西时总是双目放光神采奕奕,几番下来岑修云也不由心生向往。从前她不愿打开心扉,当下或许是个好时机。想到此处,他放柔声音出言诱导:“乐乐的家乡总有许多未听过新奇玩意。这次,能……和我说说你的家乡么?”
夤夜,帝都御道内马蹄声阵阵,疾驰着的女子扬起一鞭后迅速抬腕再落下一鞭,束起的长发在风中肆意飞舞,衣袍翻飞间怒气乍现。
宫门骤然被踢开,熟睡中的竹萌一个颤栗被激醒,还未看清来人便感到自己的衣领被提起,再有意识时人已经落到了地下。
“柳氏何在?叫她滚出来见我!”
来人凶戾愤然,一双怒目圆睁,活像庙里吃人阎罗的画像。竹萌默默咽了咽口水连滚带爬地站起身,颤巍巍拾起一旁的灯笼仔细瞧了瞧。
看清来人后小丫头冷不丁被吓了一跳,顿时扑通跪下哭得梨花带雨:“小的…小的有眼不识公主殿下,但主子这个时辰已经睡了,您要不……”
“放肆!你也配与本宫虚与委蛇?叫你主子出来回话!”眼前这丫头看起来格外碍事,解漪控制不住怒意正要飞起一脚,殿门猝然被从内打开,柳氏冲出毅然护在竹萌身前。
“殿下息怒!婢子不会说话冒犯了殿下,望殿下宽恕。”
宽恕?她还敢提宽恕?解漪怒极反笑,恶狠狠将人推入殿内后大力将门一摔,宫苑内惊醒的侍人们皆噤若寒蝉,满苑人人自危更无一人敢上前。
“我二哥腹中的孩子可是你的?!”
衣襟骤然被对方死死拽住,柳氏倒有些同情刚刚被摔在地的小丫头。她料想过有一日解漪可能会来,却没想到她会因解栖的事如此盛怒。
“什么孩子?妾不知……”
面前女子依旧是一脸标致的无辜,解漪忽觉有些恶寒,咬牙噙着几分恨意低声愤然:“你竟然敢让他怀有身孕,他的身子如何禁得起?”
柳氏哂笑一声,面上依旧装着糊涂。解漪总归是少年人,还是沉不住气,“公主说什么?妾不明白。”说着暗暗反握住解漪的手,一点点将衣襟挣脱出来。
“晏闻柳!你到底为什么?”
她为什么总能做到对一切都不痛不痒?从来都是一副高高挂起的模样?解漪怒极生悲,吼出那人的名字的同时几乎是压着哭腔哑声质问:“你知不知道就在今日……他差点早产命悬一线!”
解漪努力透过黑暗中那点烛光观察着面前人的表情,那怕她有一丝动容,自己都觉得二哥至少没有错付——可惜那张脸上的表情淡漠到令人失望。
“公主既知我姓晏,为何还要问为什么?”柳氏掸了掸衣襟上不存在的灰,盯着解漪迟疑了片刻,忽而想到什么似的笑言:
“奇哉怪也,将死之人,也能孕育新生么?”
只见对方摊开掌心手舞足蹈比划着大小:“就是一个会自己发热的东西。嗯……大概这么大,薄薄的小小的,贴在衣服里能暖和一晚上呢。”
“听起来似乎对我颇为有用?”
“是啊……”何止是有用,简直比这里的汤壶好用一百倍!来这里之前姜乐颜还没有体会到什么叫『独在异乡为异客』,现在的她无比渴望躺在冬天家里的暖气房,但现实是除了暖炉就是汤壶,出趟门也没什么取暖工具,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每次见她说起家乡的东西时总是双目放光神采奕奕,几番下来岑修云也不由心生向往。从前她不愿打开心扉,当下或许是个好时机。想到此处,他放柔声音出言诱导:“乐乐的家乡总有许多未听过新奇玩意。这次,能……和我说说你的家乡么?”
夤夜,帝都御道内马蹄声阵阵,疾驰着的女子扬起一鞭后迅速抬腕再落下一鞭,束起的长发在风中肆意飞舞,衣袍翻飞间怒气乍现。
宫门骤然被踢开,熟睡中的竹萌一个颤栗被激醒,还未看清来人便感到自己的衣领被提起,再有意识时人已经落到了地下。
“柳氏何在?叫她滚出来见我!”
来人凶戾愤然,一双怒目圆睁,活像庙里吃人阎罗的画像。竹萌默默咽了咽口水连滚带爬地站起身,颤巍巍拾起一旁的灯笼仔细瞧了瞧。
看清来人后小丫头冷不丁被吓了一跳,顿时扑通跪下哭得梨花带雨:“小的…小的有眼不识公主殿下,但主子这个时辰已经睡了,您要不……”
“放肆!你也配与本宫虚与委蛇?叫你主子出来回话!”眼前这丫头看起来格外碍事,解漪控制不住怒意正要飞起一脚,殿门猝然被从内打开,柳氏冲出毅然护在竹萌身前。
“殿下息怒!婢子不会说话冒犯了殿下,望殿下宽恕。”
宽恕?她还敢提宽恕?解漪怒极反笑,恶狠狠将人推入殿内后大力将门一摔,宫苑内惊醒的侍人们皆噤若寒蝉,满苑人人自危更无一人敢上前。
“我二哥腹中的孩子可是你的?!”
衣襟骤然被对方死死拽住,柳氏倒有些同情刚刚被摔在地的小丫头。她料想过有一日解漪可能会来,却没想到她会因解栖的事如此盛怒。
“什么孩子?妾不知……”
面前女子依旧是一脸标致的无辜,解漪忽觉有些恶寒,咬牙噙着几分恨意低声愤然:“你竟然敢让他怀有身孕,他的身子如何禁得起?”
柳氏哂笑一声,面上依旧装着糊涂。解漪总归是少年人,还是沉不住气,“公主说什么?妾不明白。”说着暗暗反握住解漪的手,一点点将衣襟挣脱出来。
“晏闻柳!你到底为什么?”
她为什么总能做到对一切都不痛不痒?从来都是一副高高挂起的模样?解漪怒极生悲,吼出那人的名字的同时几乎是压着哭腔哑声质问:“你知不知道就在今日……他差点早产命悬一线!”
解漪努力透过黑暗中那点烛光观察着面前人的表情,那怕她有一丝动容,自己都觉得二哥至少没有错付——可惜那张脸上的表情淡漠到令人失望。
“公主既知我姓晏,为何还要问为什么?”柳氏掸了掸衣襟上不存在的灰,盯着解漪迟疑了片刻,忽而想到什么似的笑言:
“奇哉怪也,将死之人,也能孕育新生么?”